小孩没娘,说来话长。父亲生平可谓坎坷波折,饱经风霜。人生三大不幸他经历其二:幼年丧父,中午丧妻。爷爷突发急病去世不久,奶奶怀着父亲再醮他乡。为了血脉流传,二爷爷调集乡党村落众把刚满月的父亲抱回老家土山村落。从此,父亲便与年迈的太祖母相依为命,困难度日。
穷汉的孩子早当家。父亲七岁便冒着风险到村落北的围子(日本鬼子的据点)里去卖粽子、火纸等物品,赚点零钱补贴家用。其间常常碰着鬼子、汉奸买了东西不给钱,讨要急了还打人的事情。也正是这些坎坷不幸的磨炼,父亲十多岁就承担起身庭重担,早起晚眠,跟二爷爷等长辈一起磨爬滚打,练就了一身好营生,耕耩锄割无一不精。也正因于此,本村落的大姨才将善良俏丽却又体弱多病的母亲先容给了父亲。
母亲生下我第二年不幸去世了。父亲又当爹又当妈,拉扯着年幼的我和十二岁的哥哥,里里外外一把手,困难地度过那段饥寒交迫的峥嵘岁月。
凭着一身的好农活,父亲被保举为队长。那时的大小干部都是身先士卒,样样活都一马当先。特殊是锄地与割麦,父亲是村落里的里手里手。至今我仍难忘他专一耕耘、行云流水的洒脱姿式以及他教给我的“老虎剔牙\"大众、“猴子攀山\公众等锄地口诀。于是在父亲挥汗如雨的背影里,我写下内心深外的崇敬与颂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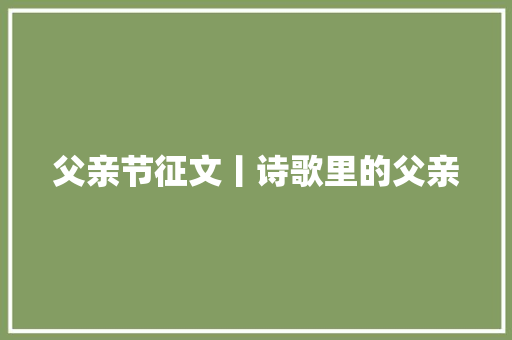
给父亲(1991年揭橥于《齐鲁》)
荷锄如笔
在生命的黄地皮里
深情地书写
生生不息的渴望
任岁月的的犁铧
在你信念隆起的额头上
刻出许多迢遥的风景线
凝聚力量的眉宇间
几抹苦涩的目光间
而你深奥深厚的目光里
依然流淌着淡淡的希冀
上世纪八十年代搞大包干,鼓励发展副业。我们这个沂蒙山区边缘的小山村落便因时制宜,靠山吃山,大力发展矿业,村落民们农闲时节便上白石山采石。那时村落里险些家家都拥有一个石坑,大家都会用硝酸铵炒制炸药,放炮采石。当时正读初中的我,每逢星期天或节假日便到上山帮父亲采石。我的紧张任务便是用一把木柄铁叉将那些碎小石屑装上哥哥赶的马车,拉到邻村落秦戈庄的石灰窑或石子机上卖几元钱。那时的钱很实,猪肉只卖几毛钱一斤,一毛钱能买十一颗水果味的糖块。那段影象里的父亲险些总是与汗水相伴,赤裸的上身被炎炎烈日晒得黝黑,在阳光下闪着古铜色的金属光芒。于是在泪眼朦胧中,便出身了我写给父亲的第二首诗歌:
给父亲(1992年揭橥于《黄河诗报》)
粗嗓子的开山炮
吼落那个青铜色的传说
四十岁的钢钎
通报山民久远的渴盼
你驾着生命的马车
亲吻冰冷的山风
然而棋木般的脊背
竟在斜阳里挺直了
噢 父亲
那时的我无以为报,只能用饱醮泪水与戴德的诗歌记录下父爱如山的轮廓。后来写的
野外(1992年揭橥于《潍坊日报》)
野外是一片最丰饶的版面
春夏秋冬是四位最虔诚的主编
农夫用鲜血和汗水费力耕耘
丰收的诗篇
庄稼是最生动的意境
粮食是最淳厚的措辞
麦收时节(1993年揭橥于《潍坊日报》)
麦收时节
满坡火辣辣的情绪
站成金黄的姿式
无数渴望的镰刀
划着俏丽的弧线
走进麦田
然后是许多苇笠
和许多汗水闪闪的笑脸
这些诗里,无不深深烙印着父亲那沧桑坚毅的身影。
这些年我一贯坚持业余文学创作,就象父亲终生耕耘脚下的地皮。也曾在全国几十家报刊揭橥诗文数百篇,但写给父亲的诗却只有这短短的几首。在许多难眠的夜晚,我常常会翻阅这些旧作,虽然越来越觉得写得青涩肤浅,但我却能从诗中看到父亲的日渐清晰伟大的轮廓:那瘦削的身躯,那坚毅的背影,那慈祥的笑颜,那老茧纵横的手掌以及那荷锄如笔,用鲜血与汗水在生命的黄地皮上写下的大爱与寂寞……
2024.6.13下午郑冠清写于山居斋
新闻线索报料通道:运用市场下载“齐鲁壹点”APP,或搜索微信小程序“齐鲁壹点”,全省800位在线等你来报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