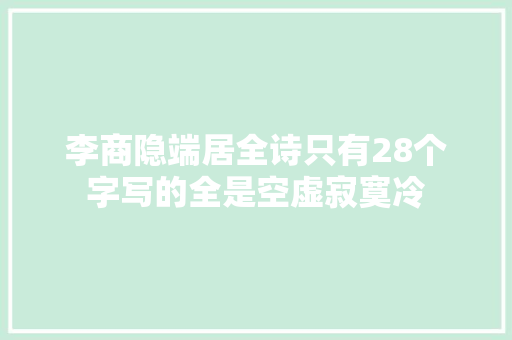提及李商隐,大家都会以为,这位老哥的诗,写得是绮丽残酷,读起来却是晦涩难懂。然后我们就会拿出《锦瑟》来证明,确实如此。但实在,李商隐也不是什么妖妖怪魅,他的很多诗还是很随意马虎读懂的,而且特殊能引起共鸣。比如这首《端居》:
远书归梦两悠悠,只有空床敌素秋。
阶下青苔与红树,雨中寥落月中愁。
我们知道,李商隐一辈子时运不济,只能在别人的幕府中当个小秘书什么的,没官没职赚不了钱,还被迫要阔别家乡,阔别妻子。以是他写这首诗,便是三分思念,三分愁绪,和四分无可奈何。诗题《端居》,便是我啥也不干,就在家里呆着,用现在话来说便是躺平,疫情之前可能还会倾慕这种生活,不用卷了嘛,疫情之后大家多多少少都被困在家里被迫“端居”,就知道那种闲得蛋疼的生活,也并不是那么好过。
那么,李商隐在端居的时候,又发生了什么,他又有什么感想呢?
他说“远书归梦两悠悠”。
古人一旦分离啊,那啥时候能再见就真是不好说,木心老师不是说过“从前的日色变得慢
车,马,邮件都慢”吗,你写一封安然家书,都不一定能安然投递,杜甫《述怀》诗就说:“寄书问三川,不知家在否?”就算书信送到了,都是良久往后了,“自寄一封书,今已十月后。”
还有“归梦”,啥叫“归梦”呢,便是你心中离去的愁绪,已经到了难以承受的地步,但你又无可奈何,你没有办法回家去团圆,人都有点魔怔了,末了的奢望便是,现实回不去,那我在梦中归家,享受短暂的团圆总行吧?
可是,白天盼着远书,夜里盼着归梦,结果只是“两悠悠”,李后主《清平乐》也有“雁来音信无凭,路条归梦难成”,你想远书归梦只管想,让你实现了算我输。
那怎么办,心中这孤独寂寞冷,怎么排解?没法排解,“只有空床敌素秋”,我只能静卧在这一张空床上,独自抵御外界和内心的孤独寂寞,一个“敌”字真是绝了。在寂寥清秋的夜里,得不到家人音信的虚无感,给人一种强烈的无法承受的悲惨感。如果把这个字换一下,比如换成“只有空床对素秋”,这种无法承受的感情就淡了。
然后从室内来到室外,“阶下青苔与红树”,家门前的石阶上都长满了青苔,这解释啥,解释李商隐独在异域,平日来往的朋友都很少,你每天熙熙攘攘不可能长出青苔嘛对不对。以青苔对红树,红树本来是很冶艳的色彩,但红树只在秋日,秋日是一个自带凄凉氛围的时令。
末了是“雨中寥落月中愁”,此时此刻,在我这有一个饱受离去之苦的人眼中,我面前所见的空床,窗外门前的红树,门前阶下的青苔,无论是在烟雨凄迷的雨夜,还是在月光朦胧的月夜,它们都和我一样,满心都是愁苦。
哎,李商隐这首《端居》,虽然只有短短28个字,小时候你可能只读到了笔墨之美,但是当你真正读懂的时候,已经不再是少年,独在异域的“客人”,心中的寂寥愁苦,又有何人能懂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