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世上有一种友情,彼此思念,情深似海,动听肺腑。
所谓日有所思,夜有所梦,白居易虽然比元稹还要年长7岁,可是元稹却走在了他前头。为此白居易痛楚万分,时常落泪,曾在梦里思念元稹,写下了这一句传颂千年的悼亡诗。
唐代元稹和白居易,本日,我们来聊聊这对同煲同捞的兄弟,为什么这二情面感如此深情。
首先他们两人都是河南人,属老乡,又是同一科的进士,属于共同发展的同门关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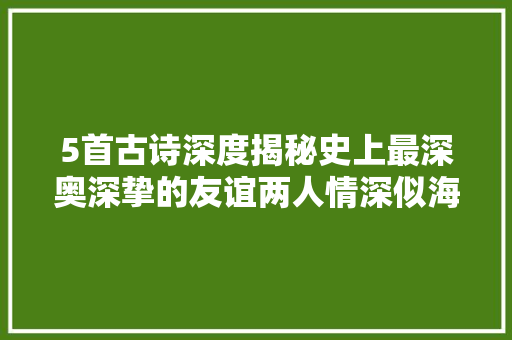
其次他们的诗歌创作造诣和政治主见也很附近。
末了,他们两人都有相同的远大抱负,可是两人都由于各自的抱负被贬谪在外。
太和年间,元稹被授以御史的官职,到梓潼(在今四川)审理案子,离开长安;白居易仍留在长安任职。元稹刚走,白居易与他弟弟及几位朋友曲江,游慈恩寺,之后又到李杓直家里饮酒。席间,白居易作了一首寄给元稹的诗:
花时同醉破春愁,醉折花枝作酒筹。
忽忆故人天涯去,计程今日到梁州。
——唐·白居易《同李十一醉忆元九》
一天,白居易与李十逐一路饮酒,在这花开时节,他们赏花饮酒,聊以肃清浓浓的春愁。醉酒后折下花枝当作饮酒行令筹子。忽然想起老友(元九便是指元稹)远在天涯,打算一下路程,他本日该当是到梁州了。
这是一首即景生情、因事起意之作。全诗无雕琢之迹,措辞朴素浅近,情深意真,表达了墨客和元稹深厚、朴拙的情意。
“忽忆故人天涯去,计程今日到梁州。”这两句表达了墨客和元稹的深厚感情。“计程”“忽忆”而来,是“忆”的深化。
故人相别,由于思念司帐算对方的行程,看看身在何处。墨客思念元稹,以是才司帐算对方的行程。墨客信手拈来这生平活中的真实景况,让人以为非常亲切、真实。墨客对元稹行程的打算是很准确的,可见他们交情深厚。
墨客在席间忆念元稹就写下了这首诗,看起来,像是墨客有时动念、随笔成篇,实在却有着朴拙深厚的感情根本。
这一天,元稹果真到了梁州的褒城(陕西汉中一带)。也差不多在同一天,元稹也写了一首给白居易的诗,诗中描述他梦见随着白居易一起绕着曲江头,一起去游慈恩寺:
梦君同绕曲江头,也向慈恩院院游。
亭吏呼人排去马,忽惊身在古梁州。
——唐·元稹《梁州梦》
晚上在汉川的驿站过夜,做了一个梦:与杓直(李建)、乐天(白居易)一起嬉戏曲江,同时去了慈恩寺的一些庭院,溘然醒了过来。换乘的马匹到了阶下,驿站的小官见告我天亮了。
后来溘然惊醒,换乘的马已牵到阶下,驿站小官奉告已天亮,这才知道自己身在古老的梁州。
如果不是由于有诗歌作为历史留存,乍一看还以为是故意编排的故事呢?我大略一点说:白居易在一座城市里嬉戏的情景,全都都涌如今另一座城市好友元稹的梦中。
两人相隔很远,在通讯不发达的古代不可能交流日程表,之以是能够这样梦魂千里地神交,是他们彼此十分理解、声息相通的缘故吧!
嘉陵江曲曲江池,明月虽同人别离。
一宵光景潜相忆,两地阴晴远不知。
谁料江边怀我夜,正当池畔望君时。
目前共语方同悔,不解多情先寄诗。
——唐·白居易《江楼月》
元和四年(809)春天,元稹以监察御史的身份出使东川,离开京都,也离去正在翰林院任职的石友白居易。
元稹独自寄居嘉陵江岸驿楼之中,圆月在天,清辉四射,江波粼粼,神思恍惚,浮想联翩,随即写下七律《江楼月》寄赠乐天,表达相思之情。
白居易接到元稹的七律之后,感同身受,产生共鸣,也情不自禁回应元稹,写下了一首同题诗《江楼月》。彼此唱和,传情达意,交相呼应。
一个在嘉陵江岸,一个在曲江池畔,一个在东川,一个在长安,相距迢遥,各在一方。嘉陵江和曲江的江水曲弯波折,你我共看一天明月人却各在一方。 在一起的各类往事仍影象犹新,如今却两地远隔,无从知晓彼此的。 没想到你在江边思念我的夜晚,我也正伫立在池畔想着你。 本日谈到此事才一起后悔,早知有这份情意真该当早点寄诗。
天上一轮圆月,地上一对离人,月圆人缺,月满人亏,不能相聚赏月,不能诗酒唱和,不能夸夸其言,不能管弦丝竹,不能游山玩水,不能寻幽览胜。
分开的两个人,各自孤独,各自忧伤。月光虽美,投下丝丝缕缕,搅乱一片心海。江水虽亮,散发道道光芒,刺痛迷离双眸。
是啊,恨天恨地恨月光,不能帮助离人排解忧闷,不能安慰失落落的心灵。怨山怨水怨分离,不能诗酒风骚快意人生,不能品茗赏月诗性飞扬。
昔我十年前,与君始相识。
曾将秋竹竿,比君孤且直。
中央一以合,外事纷无极。
共保秋竹心,风霜侵不得。
始嫌梧桐树,秋至先改色。
不爱杨柳枝,春来软无力。
怜君别我后,见竹长相忆。
长欲在面前,故栽庭户侧。
分首今何处,君南我在北。
吟我赠君诗,对之心恻恻。
——唐·白居易《酬元九对新栽竹有怀见寄》
实在元稹与白居易之间的诗作来往有很多,每篇都寄予满满的深情,比如本日要说的这首诗。在说这首诗之前,先捋一捋这诗中的关系。
白居易公元809年先是写过一篇《赠元稹》提到“无波古井水,有节秋竹竿。”元稹收到诗信之后在公元810年写了一篇《种竹》以竹自喻,回应白居易;白居易又收到元稹《种竹》复书之后,才写了本日的这一首诗《酬元九对新栽竹有怀见寄》
白居易《赠元稹》——元稹《种竹》——白居易《酬元九对新栽竹有怀见寄》
此时的元稹贬于江陵,白居易在长安,一南一北。
这首诗里表达了白居易对付受挫折、被贬官的好朋友的朴拙的惦记和深厚的友情,与此同时也显示出作者高尚的情操。
十年前,元稹中举时,作者把他比作“孤且直”的竹子;十年后,只管“外事纷无极,”作者仍以“共保秋心”相互勉励,也笃信“风霜侵不得”。
作者一方面赞颂秋竹,将它看作是孤直品性和高尚志趣的象征,另一方面借嫌弃梧桐及杨柳,对经受不住外界影响而随风飘浮之辈深表不满。
诗中可见元白二人对人生的态度,要学竹有节,不喜梧桐随季改颜色,不慕杨柳随风摇摆,要保持刚毅明净的气节。
蓝桥春雪君归日,秦岭秋风我去时。
每到驿亭先下马,循墙绕柱觅君诗。
——唐·白居易《蓝桥驿见元九诗》
元稹于元和五年(公元810)自监察御史贬为江陵士曹参军,经历了五年屈辱生涯。到元和十年(公元815)春奉召还京,他是满心喜悦、满怀希望。他经由蓝桥驿时写下“心知魏阙无多地,十二琼楼百里西。”那种得意的心情,切实其实呼之欲出。可是,昙花一现,他正月刚回长安,三月就再一次远谪通州。
元稹再度被贬,白居易自长安贬江州,满怀侘傺,经由这里,读到了元稹这首律诗。前后八个月,风云变幻如此诡谲,白居易感慨万千地写下这首绝句──《蓝桥驿见元九诗》。“蓝桥春雪君归日”。元稹西归长安,事在早春,小桃初放;
白居易东去江州,时为八月,满目秋风,白居易谪江州,自长安做生意州这一段,与元稹西归的道路是同等的。
白居易在蓝桥驿既然看到元诗,后此沿途驿亭很多,还可能留有元稹的题咏,以是三、四句接着说:“每到驿亭先下马,循墙绕柱觅君诗。”这首绝句,乍读只是平淡的征途纪事,顶多不过表现白于元交谊甚笃,爱其人而及其诗而已。实在,这貌似平淡的二十八字,却暗含着墨客心底下的万顷波涛。
“蓝桥春雪君归日”,显然在欢笑中含着眼泪。更尴尬的是:正当他为元稹再一次远谪而难过的时候,现在,自己又被贬江州。那么,被秦岭秋风吹得飘零摇落的,又岂只是白氏一人而已,实际上,这秋风吹撼的,正是两位墨客共同的命运。
春雪、秋风,西归、东去,道路往来,风尘仆仆,这道路,乃是一条悲剧的人生道路!
“每到驿亭先下马,循墙绕柱觅君诗”,墨客处处把稳,循墙绕柱寻觅的,岂只是元稹的诗句,切实其实是元稹的心,是两人共同的悲剧道路的轨迹!
一首诗统共才二十八个字,却容纳如许丰富的感情,墨客的形象和内心活动,淋漓尽致地展现在我们面前,使人深深为他怀友思故的真情挚意所冲动,激起我们对他遭逢贬谪、天涯沉沦腐化的无限同情。一个结句得到如此强烈的艺术效果,更是这首小诗的特色。
元稹与白居易这两位最深情的老友记,他们一起走过了人生的风风雨雨,一起分享了生活的甜甜蜜蜜。
他们以笔墨为纽带,以诗词为桥梁,相互扶持,相互鼓励。
他们的友情,就像那最坚韧的琴弦,虽然历经风雨,但仍旧能奏出最动人的乐章。
白居易的悼亡诗,“君埋泉下泥销骨,我寄人间雪满头。”如此痛彻心扉的句子,正是他对元稹深深的怀念和无尽的痛惜。而这样的句子,也让我们看到了他们之间那份过命的交情,那份刻在骨子里的友情。
他们的友情,不须要华美的辞藻去润色,也不须要繁复的情节去描述。他们的友情,只须要一句话,一个词,就能让我们感想熏染到那份深深的冲动。
图片来源于网络,如有欠妥,联系立即删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