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史》中记载:这一年终中大旱,朝廷拜张养浩为陕西行台中丞。五十九岁的张养浩奉命前往关中赈灾,结果“到官四月,忧劳以去世”、“关中之人,哀之如失父母”。
于是这首《山坡羊·潼关怀古》,遂成为一代爱国墨客张养浩的“绝笔”。在人们印象当中,元曲名家大多都是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
在声名显赫的元曲四大家里面,关汉卿、白朴二人长期流寓江湖;马致远当过浙江行省务官、郑光祖只做过杭州小吏。但是张养浩生前却官至元代“礼部尚书”,中书参知政事。
张养浩这个级别,相称于副丞相。作为一名权倾一时的著名政治家兼文学家,张养浩创作出的元曲小令,显然与“四大家”等名人是有所差异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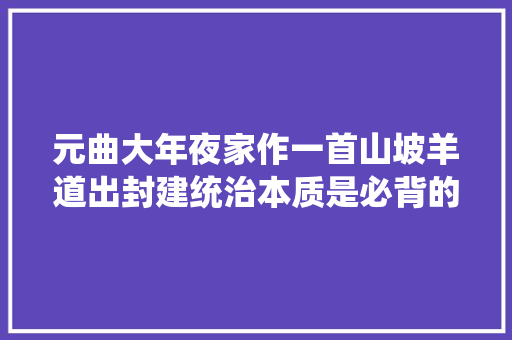
这种差异,就表示在张养浩这首代表作《潼关怀古》当中。下面我们就来欣赏一下,这首凝聚了一代爱国文人毕生心血,被后人传诵了千年,同时也是教材中必背的名曲。
《山坡羊·潼关怀古》赏析《山坡羊·潼关怀古》——元·张养浩
峰峦如聚,波涛如怒,山河表里潼关路。望西都,意犹豫。
伤心秦汉经行处,宫阙万间都做了土。兴,百姓苦;亡,百姓苦!
口语意译:
群山汇聚,层峦叠嶂;山外的黄河波涛滚滚,昼夜发出彭湃怒号的声音,这便是《左传》里面提到的“山河表里,必无害也”的潼关路了。
我站在这条路上,西望长安城。足下徘徊不定,心潮起伏。想到过往那些秦朝、汉朝的先民们,都曾经和我走过同样的一条路。
眼见着那些金碧辉煌、巍峨高耸的宫殿,化作了历史的尘土。但是一个王朝的兴替对普通的老百姓,又意味着什么呢?答案是:天下兴,百姓耐劳;天下亡,百姓依旧耐劳。
潼关是中国古代非常主要的军事关隘,是历代兵家的必争之地。它地处关中平原,南接群山之腰,北临黄河滨道,可谓是双重天险。
春秋期间,楚国曾驻扎在晋国的边陲附近。晋文公问子犯该当怎么办,子犯鼓励晋文公对楚国开战时,曾经说过:“山河表里,必无害也。”
意思便是说,如果晋国和楚国打仗,打得赢固然好,打不赢,晋国外有黄河,内有群山,居于关内,必定会安全无事,因此潼关自古便是兵家必争之地。
但是张养浩在这里提到的“潼关”,并不是现实中的“潼关”,而是统统被封建统治者认为可以依凭的“战役防线”。
统治者们以为,只要自己身处于这道防线之内,就可以肆无忌惮地震员战役。哪怕有再多的白骨盈野,腥风血雨,都浇不息那些称雄者的野心。
想到这里,张养浩的脚步踟蹰,心潮起伏。他望到西面的长安城,那里可是古代诸多王朝的故都。千百年来,一代一代的伟大王朝兴起又覆灭。
伴随着江山的倾颓,以公民血泪堆砌而成的黄金宫殿,也在转瞬间轰然倒塌。秦砖汉瓦,都成了粪土。这样的戏码,至今仍在一代又一代地重复。
这些封建帝王,之以是敢于任意发动战役,是由于他们在开战之前,已经替自己和自己的江山,想好了却局和退路。
但是在计较短长得失落的时候,这些封建帝王永久也不会把天下百姓的退路一并打算进去。由于他们争天下,为的就只是自己和家族的光彩。
一旦这些封建帝王登上至尊的宝座,得到的权力和财富,也只会与贵族阶层分享。可是民间的老百姓,却连残羹剩饭都吃不上。
国家灭亡了,百姓自然要被人奴役,过着贫苦的日子;国家壮大了,老百姓还是被贵族当成牛马使令,永无出头之日。
作为元代著名的政治家、文学家,张养浩写下的这首小令,和别的元曲作者的创作风格是大不相同的。
《山坡羊·潼关怀古》继屈、杜诗风,站在底层公民的视角核阅历史,对千百年以来,庶民百姓的不幸遭遇,表达了最深切的同情。
由于借古喻今,直接“为弱者发声”,让这首小令展现出了唐诗般的动人风采,因此能够从中脱颖而出,被人们称颂千年。
实在比起这首小令,更加让人肃然起敬的还是张养浩的为人。张养浩是山东济南历城人,少年时期就由于才学出众,被举荐为东平学正。
后来从太子文学、监察御史,一起做到了礼部侍郎、礼部尚书、中书省参知政事。在朝为官时,张养浩尽职尽责,曾经主持了元代第一次科举考试,为朝廷选拔人才。
元英宗期间,某一年天子准备学习古代习俗,趁元宵节在宫里办“鳌山灯会”。张养浩知道后就上奏反对:世祖(忽必烈)执政三十年,每到元宵,民间都禁止张灯,何况皇宫里面呢?
张养浩认为元英宗这样做不但摧残浪费蹂躏钱财,还是奢侈享乐的表现,结果弄得元英宗很生气。后来看了奏书,元英宗还是打消了办灯会的动机。不过不知道为什么,张养浩就告退归里了。
张养浩辞官归隐后,元英宗感到后悔,曾经七度聘请张养浩复出为官,都遭到他的谢绝。从这件事情中我们可以看出,张浩养一贯坚持天子与庶民,该当等量齐观。
公元1329年,也便是张养浩生命中的末了一年,关中地区涌现干旱,朝廷又聘请他去陕西赈灾。结果59岁高龄的他匆匆奔赴关中灾区,途中经由潼关一带,就写下了这首《山坡羊》。
谁料四个月后,张养浩就由于忧郁又劳累病去世了。我们从他的个人经历看来,他的确是一个言行同等,令人敬佩的好官。
以是张养浩的去世,让当地的百姓非常难过,“哀之如失父母”。由于他的文如其人,他的忧国忧民更是发自内心的,非常值得后人尊重。
结语民间有一句俗话叫做: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相传之以是有这句话,便是由于元代发生过朝廷不许民间擅自点灯的事情。
从张养浩与元英宗的对话来看,至少在忽必烈当政的那三十年中,的确涌现过元宵节不许百姓燃灯的规定。
至于缘故原由,不外乎这两种:一是当时元朝的江山未稳,夜晚实施宵禁,官府害怕百姓燃灯为号,搞出乱事;二是元代的统治者认为元宵燃灯是摧残浪费蹂躏灯油,以是一禁了之。
张养浩阻挡元英宗办“鳌山灯会”时说道:朝廷已经三十年不许百姓点灯,既然百姓们都不能点灯,宫廷里更不能例外。
这种对君民等量齐观的思想,一贯延伸了张养浩末了的绝命之作中。以是他这首小令真正想表达的是:当一个国家霸占“潼关”天险后,统治者们就可以不顾公民的去世活,为所欲为了。
如果说“潼关”是国家江山的“防线”,那么天下百姓生命安全的“防线”,又在哪里呢?可惜找不到这样的“防线”巩卫百姓,让他们不必忍饥受饿,遭受奴役剥削。
以是,“兴,百姓苦;亡,百姓苦”,而这也是封建统治的实质,无论兴亡,都与普通的老百姓无关,由于他们一贯都受着苦,从未发生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