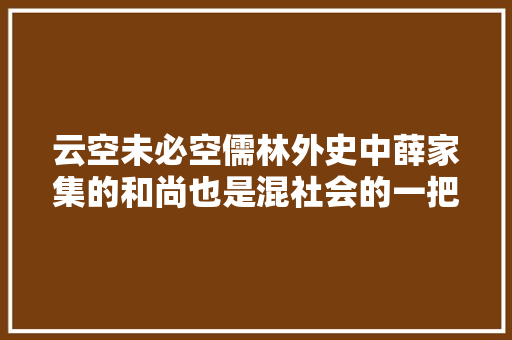在小说一开始,作者就用了寥寥数笔,为我们勾勒出了一个鲜活的小人物——一个连名号都没有的和尚。
薛家集,是山东衮州府汶上县的一个小村落庄,村落口有一个不雅观音庵,庙里有一个和尚。薛家集有什么事情,村落民们都是聚拢到这个庙里来商量的。
当时,村落里就有十来个人正走进不雅观音庵,准备切磋正月十五村落里闹龙灯的事情。和尚接着他们,问好时,想必嘴里少不得要念上几句佛号,但他却连珠炮般地挨了一顿数落:
“和尚!
你新年新岁,也该把菩萨面前喷鼻香烛点勤些!
阿弥陀佛!
受了十方的钞钱,也要消受。”
“诸位都来看看:这琉璃灯内,只得半琉璃油。”
“不论别人,只这一位荀老爷,三十晚里还送了五十斤油与你;白白给你炒菜吃,全不敬佛!
”数落和尚的人,叫申祥甫,是薛家集的一个普通田舍。别人都不怎么说话,他怎么就能够拉得下脸来,持续串地训斥和尚呢?
原来,他的亲家是夏总甲,那可是卖力村落里一百多户人家的赋税、徭役的大人物,这也让申祥甫在乡民中间,有了说话的底气。给和尚来上几句,那就更不在话下了。再说,明清期间,民间本来也有讥讽、挖苦出家人的风气。
和尚陪著小心。等他产生发火过了,拿一把铅壶,撮了一把苦丁茶叶,倒满了水,在火上烧得滚热,送与众位吃。
多么诚笃的一个和尚啊!
难道申祥甫是在曲解和尚不敬佛,暗地里扰乱么?再今后看,我们就能创造申祥甫的话,说得一点儿错都没有。在集会上,众人不但商定了闹花灯的事情,还为薛家集的孩子们找到了一位教书师长西席,便是周进了。教馆就设在了不雅观音庵里,由和尚卖力给周进供应一日三餐,每天的饭费是二分银子。
二分银子究竟是多少,在当时的购买力如何,这就不太好说了,但我们可以做一个明显的对照:在明朝大名鼎鼎的戚家军里,戚继光为士兵们每天发的军饷是三分银子。
士兵们不但得抛家舍业,逐日在军营里刻苦演习,还得时候准备着为国杀敌,做的都是把脑袋系在裤腰带上的生存,军饷自然不能是只够他们用饭的。由此可以看出,周进每天二分银子的炊事费,可是不少的了。
和尚为周进供应的食品是什么呢?“一碟老菜叶、一壶热水”。
要说和尚没有贪污周进的炊事费,那是谁都不会相信的。看来,一开始申祥甫训斥和尚的话,就该当一点儿都没说错。
和尚当时什么都没有说,由着申祥甫数落、讥讽,一副低头顺眉,老诚笃实的样子,现在看来,他那切实其实便是做贼心虚。
和尚打定了主张,对申祥甫的话既不肯定,也不否定,采纳了沉默主义,实在是高明之至。
既然会场设置在庙里,那就该当由和尚来供应一些吃食了,谁让这些人都是庙里喷鼻香火的檀越们呢?尤其是个中还包括着“权倾村落庄”的大人物——夏总甲。
“云片糕、红枣、和些瓜子、豆腐干、栗子、杂色糖”,满满摆了两桌。会后,和尚还为大家安排了一斤牛肉面,不但席面丰硕,连佛家的清规戒律都顾及不到了。
虽然教馆设在不雅观音庵里,尤其是为周进供应每天饭食的差事,让和尚又多了一项收益,但和尚是不必去奉承周进的。和尚是不会把一个穷教书师长西席放在眼里的,乃至有时候,和尚还可以陵暴一下周进。
途经的举人王惠,在不雅观音庵里暂住了一宿,临走时留下了一地的“鸡骨头、鸭翅膀、鱼刺、瓜子壳”,结果是周进第二天昏头昏脑地扫了一个早上。庙里的卫生,难道不应该是由和尚来卖力么?
王惠来的时候,和尚极力地奉承他,过后,却把这给王惠扫尾的活儿交给周进去做,可见和尚很会陵暴诚笃人。不过,当周进发达了往后,和尚就又变了一副嘴脸。
周进的学生荀玫考中了秀才,和梅玖一起回到不雅观音庵里时,和尚激情亲切地接待了他们,不但夸赞了荀玫,说他考中的秀才,是他父亲荀老爹“生平虔诚,做多少佛面上的事,广积阴德”挣来的,还描述了荀玫小时候在这里上学的情景,并且把他的老师——周进的永生牌位指给他们看:
二人看时,一张供桌,喷鼻香炉、烛台,供着个金字牌位,上写道:“赐进上出身广东提学御史,今升国子监司业周大老爷永生禄位。”
立牌位的人,写的是“薛家集里人、不雅观音庵僧人同供奉。”这个和尚在撰文的时候,居然还没有忘却自己。万一将来周进能够见到,或者是听到的话,这也是自己在感情上的一份小投资了,再加上两人旧日的“交情”,切实其实是有百利而无一害,何乐而不为呢。
只是和尚所供奉的人,不是西席周进,而是官员周司业。
不雅观音庵里的这个和尚,只是小说中的一个小人物而已,小到作者连他的法号都没有先容。作者为他所花费的笔墨也很吝啬,但仅仅是这寥寥几笔,就为我们刻画出了一个爱慕钱财,贪恋权势的出家人的形象。
出家人该当是四大皆空的,但是这个和尚,却是云空未必空,浑身充满着世俗的味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