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早之前,他还由于把孟浩然在《宿建德江》中的名句——“野旷天低树”,阐明成“天比树还要低,树反而到天上去了”而受到网友讨伐。
一些网友认为:康震教授不但把“天低树”中的“低”读成了“去声”,并且还质疑他到底是否懂得“低”字在古汉语中的用法。
“去声”,是指当代汉语的第四声。为此,我专门去看了那一期的节目,康震教授只是把“低”字的音发得有点重,但是并没见有发成了“帝”音,发的还是“一声”。
康震教授对付“野旷天低树”这一句的阐明,猛然一听,仿佛和“标准答案”有所不同,但是事实上,他的阐明和诗意实在并不相违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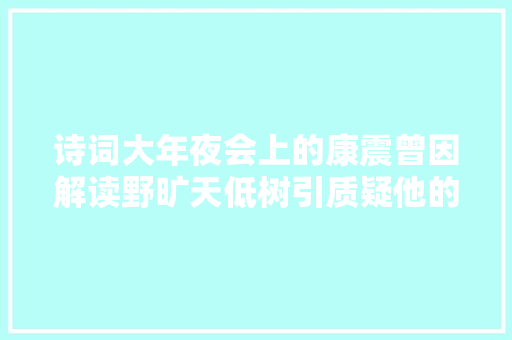
诗词重视“兴发冲动”,写诗的人因有觉得而付诸笔端,通过笔墨引发读诗的人产生共鸣。阅读是一个再创作的过程,因此诗歌不应该只有“标准答案”和“固定阐明”。
一、《宿建德江》原文干系阐明《宿建德江》——唐·孟浩然
移舟泊烟渚,日暮客愁新。
野旷天低树,江清月近人。
孟浩然的这一首诗,前几天我已经详细写过一次了,这里就不再重复啰嗦了。这首诗我查了一下,现在是被放在小学六年级的教材里。
低年级的语文课,不会深入地解读它,只是会对一些字词进行注释。最近我把稳到,有网友在网络上质疑书中的注释有一些问题。
比如第一句,“移舟泊烟渚”中的“烟渚”,真的是指江中的小岛吗?有的人狐疑,烟渚实在只是阁下的一个灌木丛而已。
还有的人认为,如果那“烟渚”是江心小岛的话,那后面怎么来的“野旷天低树”呢?那是一个巨大而广阔的空间啊。可见,前面的“烟渚”绝对不是小岛,而是一个炊烟袅袅的船码头。
对此,我不得不佩服他们强大的想象力。不过很遗憾的是,“渚”字在《新华字典》第12版中清清楚楚地写着,“指水中间的小块儿陆地”。
可是如此一来,这首诗后面的“野旷天低树”,的确是很“玄幻”了。不知道何故,关于这句诗的争议,影响力并不如杜牧《山行》中那几句的争议来得大。
康震教授作为中文专业的博士生导师,自然不会在“渚”字的理解上犯缺点。但是他却在“低”字的阐明上,受到了很多网友的质疑。
“野旷天低树”这一句,按照上辞版《唐诗鉴赏辞典》的阐明,是指的傍晚时分,旷野无边无垠,远远地望去,天空显得比近处的树木还要低。
这一句话如果你不仔细地看,或许就会感到很难明得。实在它的意思是,当你身处空旷的平原地带,前方的视线没有遮挡物的时候,你会看到远方的天空和地平线连接成了一片。
这个时候的天(与地平线交卸的地方),就会显得比树木的位置还要低。有野外旅行或者户外露营履历的朋友,对此就会深有体会。
但是,康震教授却把这句诗阐明成了“树反而到天上去了”。那么,他的这种阐明,算不算错呢?实在我认为也不算错。
前面已经说过了,这一首诗的“画风”事实上是非常“玄幻”的。它在“美妙”的同时,又有一些不讲究逻辑。由于按照正常的逻辑,水中这一小块的陆地,哪来的“旷野”呢?
我们先假设“旷野”是存在的,那么远远地看过去,树实在便是比天高。天本来不是活物,既然“天可以低树”,那么“树自然也就可以上天了”。
这么一来,康震教授就只是对这首诗做了“诗意化的理解”,以是完备是没有问题的。既然阐明完备没有问题,又哪里来的缺点呢?
二、古诗争议何其多唐诗宋词从写下到流传至今,已经靠近千年或者上千年的韶光了。我们如今看到的诗词,大多都是通过古人以“手抄”的办法传承下来的。
个中有相称大的一部分诗词,都不是原来的样子容貌了。以是如果中间有个别字词不一样时,请不要轻易地用“对错”二字去下结论。
比如李白《将进酒》的敦煌版,好几个版本都不一样。再加上古人没有版权意识,编写集子的人,又喜好去主动“修订”原文。以是,光是李白的《静夜思》,就有八个版本之多。
在杜牧的《山行》这首诗中,里面“白云生处有人家”的“生”或者是“深”的不合,实在也是因版天职歧而来。不过,前不久人教社已经确定是“生”了。
以上的这些情形,是古诗词随意马虎引发争议的第一类,这一类紧张是流传过程中涌现了一些变革而造成的。而古诗词随意马虎引发争议的第二类,则是由古今汉语发音的不同而引起的。
比如杜牧的《山行》中“远上寒山石径斜”的“斜”字,是不是该发“峡”的音,还有他的《过华清宫·其一》中“一骑尘凡妃子笑”的“骑”字怎么发音等等。不过,最近听说这些字都被统一弄成了现行普通话的发音了。
由于字词的古代汉语发音和当代汉语发音已经涌现了很大的不同,以是今人读古诗,有时候会以为有一点拗口。实在,以前这个问题是有办法办理的。
原来的办法是根据“叶韵”,然后弄出一个古音,只管即便让它读起来富有音律的节奏美(这个是格律诗重视的内容),而现在则是都选择了一刀切。
实在,押不押韵实在也不主要了,反正大家都只是看内容而已。这忽然让我想起了最近很红的“作二代”,大作家贾平凹的女儿贾浅浅写的诗。
连“顺口溜”都要押韵,而“当代诗”本来就缺少笔墨上的美感,现在竟然连韵都不押了!
不押韵,又没有音律起伏和美感的东西,这还能叫诗吗?古诗词随意马虎引发争议的第三类,便是由于字词的古今涵义不一样。而且这些字词在古汉语中的意思,在当代汉语中已经不用,或者是极少用了。
如杜牧的《山行》中“停车坐爱枫林晚”的“坐”,意思是“由于”;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中“可怜楼上月徘徊”的“可怜”是指“可爱”的意思等等。
古诗词随意马虎引发争议的末了一类,则是由类似“野旷天低树”这样的理解不合引起的争议。古代汉语中“低”和“近”都是“使……低,使……近”的意思。
“野旷”、“天”和“树”,都是自然界中的东西,按理说他们是不可能自己动的。不过在诗中,“野旷”作了主动,使“天”比“树”低,这是一种拟人手腕。
以是康震教授在诗词大会上对孟浩然这首《宿建德江》进行阐明的时候也采取了“拟人”化的阐明,因此他说“天比树还要低,树反而到天上去了”是完备没有问题。
结语叶嘉莹师长西席在其著作《迦陵论诗丛稿〈题记〉》中说:诗歌便是墨客的心灵与自然界相通得到的感想熏染,诉诸于笔墨,借助于词采、意象,引发阅读者“丰融之遐想”。而这种想象不必局限于一人一事,它是“通古今而不雅观之”的。
换句话说,你的想象力越强大,你阅读到的天下也就越广大。因此“野旷天低树”,不但可以是指“树反而到天上去了”,也可以是指天穹太低,压弯了树。
以是,在阅读或者解读古诗词的时候,千万不要自我设限,用书本上的“标准答案”去限定自己的想象,由于这样只会让自己被困于一个很狭小的空间的里。
同时,所有爱好古诗词的人,都该当大胆地放飞自己的想象,用自己的心去聆听古诗词。自然也可以把真实的感想熏染写出来,求同存异,让我们彼此得以进行审美上的互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