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读蒋士铨的《鸣机夜课图记》,你是不是会受到更多启示呢?
好多年前,我向一位忘年交的苑姓朋友,请教如何写年夜大好人物散文。他给我讲了两篇散文,一篇是鲁迅的《藤野师长西席》,另一篇是清朝文学家蒋士铨的《鸣机夜课图记》。题目里话,就出自后一篇文章。里面的情节和细节,到现在还影象犹新。
蒋士铨,生于1725年,卒于1784年,清代戏曲家、文学家,江西铅隐士。乾隆22年(公元1757年)进士,官至翰林院编修。乾隆29年辞官后,任书院讲席。有《忠雅堂诗集》和《江雪楼九种曲》传世。和袁枚、赵翼合称江右三大家。
他的母亲钟令嘉,生于南昌名门,女作家,有《柴车倦游集》存世。18岁嫁到蒋家,相夫教子,勤恳持家。虽然他也描写了封建社会的母范:孝敬父母,夫唱妇随,教子成名,但是,她并不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三从四德的女性。在丈夫做的不对的时候,她也敢于几次再三规劝批评,直到丈夫接管为止。她也不接管“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封建意识,从小随着父亲读书,有很高的文学成绩。他父亲诗词中的瑕疵,她能很快创造并示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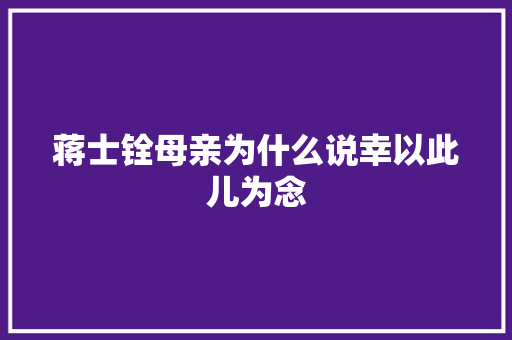
蒋士铨在10岁前,由于父亲在外地做幕僚,一贯由母亲教诲培养。寒冬夜半,虽然很不忍心,母亲还是把她叫起来读书。纵然在病中,也不忘儿子的学习。由于教诲得法,儿子进步很快,很早就考中了秀才。后来,父亲又让他跟随名师学习,学业大进。22岁中举,32岁中进士,后来成为一代大家。这都和母亲的早期教诲是分不开的。
最让我忘不了的情节,是这样一段:先府君每决大狱(审理主要案件,指有关人命的案件),母辄携儿立席前,曰:“幸以此儿为念。”(千万为孩子着想。意思是不要冤枉人,做缺德的事情。)府君数颌之。
在蒋父审理人命大案的时候,蒋母常常带着儿子站在公案前面,悄声提醒丈夫:幸以此儿为念。让他不要冤枉人,做缺德的事情。言外之意,如果那样做,会报应在儿子身上。这几同谩骂的提醒,蒋父也不生气,频频点头表示赞许。
实在,对蒋士铨来说,这也是一种现场传授教化,身教更胜于言教。父母作为人生第一老师的凭着良知为人处世的方法,蒋士铨全受益良多,终生难忘。
古代的这样一种现场传授教化方法,恐怕大家是闻所未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