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家客厅的墙壁上,挂着老舍师长西席为外公写的墨宝:“学知不敷,文如其人。”打仗了外公的作品后,再遐想到他的为人,我加倍觉得到用老舍师长西席这八个字来形容外公真是再贴切不过了。
“学知不敷”,代表着外公一贯秉持着谦逊的态度,不断地从不同的人和事物中汲取知识。
幼时的外公颇受古典文学熏陶,后来纵然在创作描摹现实生活的新诗时,也总带有水墨的意境,抒怀的手腕也带有古诗的韵味。比如“薄暮还没溶尽归鸦的翅膀”,比如“静波上把冷梦泊下”。而外公晚年时创作的旧体诗,像“老牛亦解韶光贵,不待扬鞭自奋蹄”,更是深得古典文学的精髓。
青年期间的外公师从闻一多师长西席,从闻师长西席处不仅学到了爱国情怀,还学到了许多写作的技巧和态度。外公回顾说:“他见告我这篇诗的好处,缺陷。哪个想象很聪明,哪个字下得太嫩。”这种细致到每个字的考虑精神,在外公日后的诗文中也有着充分的表示。比如《兵车向前方开》一诗第一句“耕破黑夜”中的“耕”字,不仅描述出了兵车浩浩荡荡开拔抗日前哨的壮不雅观景象,还表现了中国军队不怕捐躯、勇往直前的宏伟气势。试想如果换成“划”字,便少了颇多意蕴。《老马》中“眼里飘来一道鞭影”,这里的“飘来”二字更是神来之笔,是“闪来”“掠过”一类的形容所无法比拟的。在创作它们之时,可以想象外公多少次为诗文中的用字“一个人踱尽一个薄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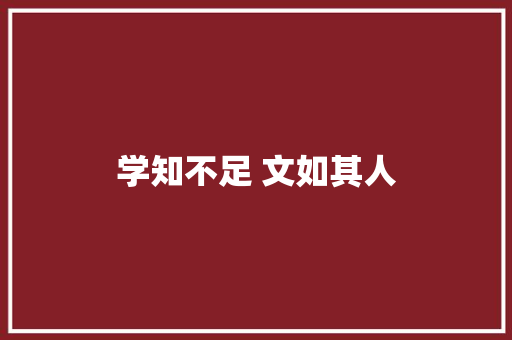
步入老年,本该颐养天年的外公,仍旧没有停下学习的步伐。在我们的小四合院中,三间南房装的全是外公的书。随机从中抽取一些,都能看到外公在上面做的条记,有评论,有感悟,也有自我反思。他在《读书学习的零散感想》一文中说:“论古人,评今人,要有创见,这就得有教化。”多读书、不妄语、与专家朋友畅谈、在生活中不断积累履历,都是提高教化的路子,而外公道生都在身体力行,是我们子弟的榜样。
“文如其人”,则代表着外公的真实情绪和高尚人格,都完完备全体现在他的笔墨中了。
外公是个有大爱的人。
外公颇爱闲步,让当时幼小的我感到非常惊奇的是,险些胡同里所有的人都和外公认识,走到哪里都有邻居同他闲聊几句。终年夜后才知道,外公的文学创作总是从现实出发,表示的都是普通老百姓的酸甜苦辣。他早期的诗文作品,充满着对劳苦公民深深的同情和对社会不公的愤慨,“老哥哥”“六机匠”是他笔下最鲜活的人物。解放战役期间,他还写下了《公民是什么》一诗,直抒胸臆表达了对忽略公民疾苦的愤怒之情。他最为著名的诗作《有的人》,虽是为纪念鲁迅师长西席所写,却为公民发出了振聋发聩的呼喊:“骑在公民头上的,/公民把他摔垮;/给公民做牛马的,/公民永久记住他!
”
外公好交友,且将交情放在了极高的位置。小时候的我有着模糊的印象——总是有不同的人,老的少的、高的矮的、胖的瘦的,相继而来地涌如今小院里。我家客厅里挂着许多文人墨宝,外公还特地写下散文《交情和墨喷鼻香》,记录了每一幅墨宝中动人的交情故事。外公待人的激情亲切、随和、谦善、诚挚,是他广交石友的窍门。
外公还是个童心未泯的老人。他非常喜好去胡同里的幼儿园看小孩子玩闹,听着孩子们一声声叫他“爷爷”,他总是极愉快的。他与孩子们分享糖果,安慰哭泣的孩子,在他们之中开怀大笑。我读他的文章《我和孩子》创造,与孩子们在一起的外公,是极其快活而有生命力的。
每每回顾起外公,我的心情都不是伤感,而是惦记和敬佩。我认识的外公,用他的一言一行在影响着我,要我乐不雅观待事、爱慕待人,永久抱着小儿百姓之心,纵然眼含热泪,也要用力地生活。
(作者:罗文雯,系臧克家外孙女,90后影视文学策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