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颋
春节刚过,京师的臣民还沉浸在节日的欢快之中。街市上时而锣鼓喧天,时而鞭炮炸响,那些跑旱船的、要龙灯的、踩高跷的、变魔术的,招引得围不雅观者人隐士海常常将道路壅塞。这几年,天下太平,国泰民安,人们也有了欢度佳节的兴致。尤其元宵前后这几日,儿童们忙着燃放烟火鞭炮,女人们忙着沿街不雅观灯看耍,而男人们则忙着串门饮酒。至晚间,确乎要家家扶得醉人归了。
这天,苏颋让中书舍人高仲舒和齐瀚二人前去把宋璟请到家中。他知道,宋璟正为禁恶钱而被罢职心烦着哪,在一起喝杯水酒,叙谈叙谈,兴许也能相互宽慰一下。
宋璟一见苏颋,便问道:“怎么,是不是想开酒戒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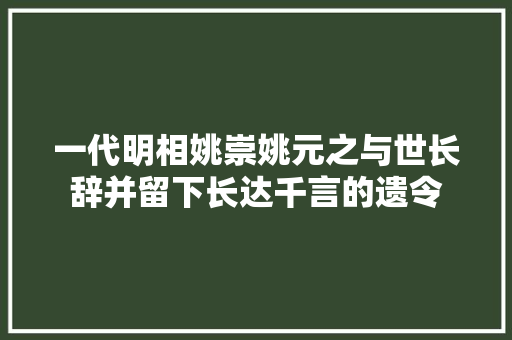
苏颋笑笑说:“对。你,开府仪同三司;我,荣任礼部尚书。还不该好好庆贺一番?尤其你宋大人,已经年近花甲,几十年来,从北国的并州、幽州,到南疆的睦州、广州,历任十多州的都督、刺史,何曾有一日消停?常言道,人生难得几时闲?若是再不让休歇一下,就太不公正了。今日,本来还想请姚(崇)老一起来,可是,他已经年迈力衰出不得门了。还是当年曹孟德说得好: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慨当以慷,幽思难忘。何以解苦恼惟有杜康……""
“不,你还年轻,绝不能就此屁滚尿流。”宋璟说,“便是礼部尚书,亦应勤谨为之。就你的才能,在官场升沉之中,今日沉,嫡还能升!”
苏颋苦笑着摇摇头,说:“侄儿虽愚,尚有自知之明。随宋大人为相三载,已不枉此生了。三年来,虽然日日克己惕厉、诚惶诚恐,但效忠心、除弊政、选贤良、斥奸恶,诸位同仇敌忾,为大唐再创盛世。尤其在别人眼里,你我乃是风云际会,如鱼在水。都快让人羡妒煞了。”
苏颋夸年夜诙谐的言谈,逗引得大家都笑了。
齐瀚却非常负责地说:“苏大人并未言过实在。而今四海安定,赋役宽平,刑罚清省,人寿年丰,大唐盛世再度涌现。人们常把姚大人、宋大人与贞不雅观年间的房玄龄、杜如晦相提并论,合称大唐四名相……"
宋璟听到这里。站起身来扭头想走。苏颋急忙上前拦住。
宋璟说:“宋某平生最烦阿谀奉迎!姚老曾说,欲知古,问高君,欲知今,问齐君。我今日是求二位破解困惑来了,可不是来听奉承的。”
齐瀚笑笑说:“此话差矣!齐某绝无奉迎之意,只是宋大人性急,尚未耐心听完后边的话语。”
“我宋璟能与前代明相比较吗?”宋璟又坐下来问道。
“不如前代明相。然而,姚、宋与房、杜合称四明相了,也就该到顶了,该到头了。"齐瀚从容答道。
"说呀!”“说完了。”四人都沉默了。
宋璟叹了口气,又说:“实在罢相,也无所谓,只是这恶钱禁不住,倒让我寝食不安。近些日子,镇静地想了一下,禁恶钱失落败的缘故原由可能有二:一是操之过急;二是用人不当……"
“三是皇上未曾武断支持。”齐瀚补充说。
一贯沉默的高仲舒开口了:“常言道,察看犹豫者清,当局者迷。三年前的姚大人罢相,绝不是由于儿子不肖;而今宋大人罢相,也绝不是由于禁恶钱不力。而是由于功绩太大了,太成功了。再连续下去,会功高盖主了。可以回忆一下,开元二年五月,魏知古便向皇上奏报了姚大人二子在东都的不法行为。但是,皇上不但没因此处治姚大人,却嫌魏知古薄情,有负姚大人,被罢黄门监,降为工部尚书。也便是说,此时姚大人正如日中天,儿子不肖,亦瑕不掩瑜。你魏知古如实奏报,也是别有用心。可是,两年半之后,到开元四年闰十仲春,皇上想罢黜姚大人了,便又提起儿子不肖作为情由了。对付你宋大人,亦可举一例证……”
“请讲。”宋璟心折了。
“开元四年闰十仲春,刚任命宋大人为吏部尚书兼黄门监。大武军将领郝灵荃出使突厥,得到了久为祸患的突厥默啜可汗首领,便以为建立了不世之功,定会得到厚奖。但是,宋大人封锁,拖延封赏,达一年之久。使郝录荃大失落所望,恸哭而去世……”
宋璟说:“确有此事。那时害怕皇上因此而喜好武功,把人力物力用于战事上。”
高仲舒笑笑说:“实在只这一件事,则足以罢相了。但是,对付刚刚任命的宰相,正高接远迎,礼遇有加。即便有瞒而不报之事,也以为是好心,不作计较了。至于比来禁恶钱之事,倘若有过失落,改正便是,何须正副宰相同时罢黜?”
齐瀚又接着说:“你们看,院子里那几棵树,假若中间那棵最高的是皇上,它两侧的树再长高了行吗?当然弗成。移栽之后,只让你长三年两载。如果韶光再长,就会树大根深。下边盘根错节,上边直指蓝天。与中间高树,又争肥、又争水、又争阳光。因此,成功了,也就到头了。请诸位拭目以待,随后再任命的宰相,兴许便是平庸之辈了。”
高仲舒又插话道:“还可以预见,越是平庸之辈,在位韶光越长,而越是才干轶群,处事果决者,在位韶光便会越短。”
果真不出齐擀和高仲舒所料,随之便敕命才干平庸、在姚崇生病期间曾主理过朝政的京兆尹源乾曜为黄门侍郎。同时,并州长史张嘉贞被擢升为中书侍郎,并同平章事。五月,又晋升源乾曜为侍中,张嘉贞为中书令(有些官名,明皇接管宋璟建议,又规复旧称。)平庸的源乾曜在二十九年的开元期间十三名宰相中(任期一年以上者)他是任期最长的,前后达十年之久。而与他同时任命的张嘉贞,因是军撤出身,处事敏捷决议确定,脾气浮躁,任相的韶光与姚崇、宋璟差不多,亦是三年旁边。
张嘉贞
在张嘉贞接到任命诏书之前,这位并州长史,兴许做梦也未曾想到自己会进京
去当宰相。 那是开元八年正月,大年纪后的某个夜里,明皇失落眠了。既已决定罢黜宋璟、
苏颋,而接替他们的人选还尚未考虑成熟。而今天下已经大治,宰相不需太冒尖了,当然也不能太无能。能够“守成”就可以。源乾曜算一个,此人的优点是能够严以律己,生活俭仆,不贪不占;与人共事,从不争权,皆能和蔼相处;最大的好处,是谦恭谨慎,事事请示奏报,从不自己做主。有了功绩,都说是皇上圣明;有了过失落,总是主动承担。朝廷大事,可由皇上亲自处理,至于盘根错节的庶务,有他这么个不急不躁、四平八稳、任劳任怨、处事严谨的宰相处理,也就可以了。但是,姚崇和宋璟,皆文武双全,统辖全国军队,安排边关将领,乃至直接决策边关战事,亦是得心应手,绝不陌生,文臣武将无不钦服。而他源乾曜却不谙军旅武事。也便是说,得配备一名将帅出身的人与他搭帮。这些封疆大吏他逐一数点着:薛讷,不成。他是名将薛仁贵之子,治军确乎有方。八年前在骊山讲武时,只有他与解琬的军队纪律严明。但是,后来让他兼了副宰相之职,与契丹作战时,差点儿全军覆没。此人只能任将领,但不足深奥深厚,尤其不懂朝廷政事。再便是朔方大总管王睃了。他在任桂州都督时,曾经救过刘幽求的命,使刘幽求没有落进广州都督周利贞之手。周利贞已经接到崔湜要他杀害刘幽求的指示。但王睃窝藏刘幽求,假说刘幽求已去广州。闹了个刘幽求失落踪,着落不明,谁也就难以查找了。足见此人有胆有识。开元后,先后任鸿胪少卿,朔方军(今宁夏)副大总管、安北大都护、并州都督,朔方大总管等职。有他统兵把守国门,皇上可以无忧无虑。若是将他调进京师,边关统帅就虚空无人了……
明皇溘然记起,去年,有一位边陲将领被人弹劾有贪赃收贿不法行为,经御史台调查核实,创造是无中生有的诬告。明皇很生气,便敕令深究和处治那个诬告者。但这位边陲守军的将领,却非常豁达宽容,他上疏奏道:“百官谏,庶人谤,是真是假由天子核实推敲。若反连坐弹劾者,则将堵塞言路。此后天下事便难以上达。望能赦免此人之罪,以开天下言路。”
这件事给明皇留下了很好的印象。便想往后找机会提拔一下这个人。这天夜里,思虑宰相人选的时候,便溘然想起了他。他是个将领,可以填补源乾曜不懂军事的短处。肯定待人宽厚仁义,对付诬告他的人都能不计较、不深究,对其他人则更加宽容了。常言道,宰相肚里能撑船。对,这便是个空想的人选。但是,这天夜里想来想去,便是记不起他的姓名来了。
兴许已经三更过后了,找谁问呢?宫内多数房间里灯烛已经熄灭了。今日召幸的武氏惠儿,她根本不留心什么军中将领。若是王皇后,她肯定能帮你思虑一下,乃至为你拿个主张。他不仅对朝中文武百官直呼姓名,说清出身脾气,便是十道封疆大吏、节度使、军队正副大总管等,亦能逐一悉数道来。她读书能过目不忘,对这些人事杂务,她则能过耳不忘。她听你讲一遍,便会永久铭刻在了心上。但是,她太像个男人。与她在一起,议论起军国大事,可以通宵达旦,让人忘了疲倦。但是,也会忘了她是个女人,忘了夫妻之间夜里做的那些事,隋。如今,场合排场安定了,与她也疏远了。她身体不好,变得面色干瘪黑黄。明皇每想起她,便有一种愧疚感,实在对不起她,但又有什么办法呢?
明皇强制自己不再想王皇后的事,但是,那位边陲大吏的名字还是记不起来。他让宦官把值夜班的中书侍郎韦抗叫来讯问。
韦抗便将北方的统帅将领、节度使等逐一讲了一遍。明皇只是摇头。末了,明皇又问了一句:“朔方的节度使。叫什么名字,你再讲一遍。”
“朔方现任节度使叫张齐邱。”
“莫非是他?”明皇还是记不准,“可能便是他吧,不错,彷佛姓张,名是两个字”
.明皇当即让韦抗起草了任命张齐邱为中书侍郎,并同平章事的诏书。
待韦抗走后,明皇随手拿起几份大臣的奏章翻阅。溘然,“张嘉贞"三个字跃人眼帘。对,他叫张嘉贞,一点儿不错。
明皇又派人将韦抗召来,将任命书上的张齐邱,改上了张嘉贞。
明皇一言九鼎。倘若这一夜明皇不翻奏章,不创造张嘉贞的名字,第二天任命张齐邱的诏书一公布,那么张嘉贞做宰相的机遇切实其实是天外飞来的机遇,便会人不知鬼不觉地悄然消逝了。难怪有些读史的人对此大发慨叹:“不知张嘉贞那辈子烧了高喷鼻香?侥幸、侥幸、侥幸之至!”
源乾曜与张嘉贞刚上任,明皇便很满意。
源乾曜向明皇奏报:“臣看到权贵之家的子弟,多任京官。但有德有才而门第低微的人,则多任外官。这是不公正的。臣有三子,皆任京官。臣恳请派二子去任外官。”
明皇就把他的宗子源弼派去任绛州(今山西新绛)司功参军。把他的次子源洁派去任郑县(今陕西华县)尉。并特殊敕令表彰源乾曜,号召百官向他学习。还规定家中父子兄弟三人担当京官的,至少一人下地方任官。而且京官和地方官根据表现,进行不断互换。结果有一百多名京官下到遍地所任职。空出来的位置,又选拔了一些有德有才的地方官进京补充。
几个月来,源乾曜为此忙得起早贪晚,废寝忘食。明皇亦不断地对他进行慰问。
源乾曜
源乾曜便淳厚地笑笑,说:“臣无大才能,只好勤恳做些小事,以报陛下知道之恩。”
张嘉贞走立时任之后,仍旧带着军旅生涯养成的那种处事敏捷果断,雷厉风行的作风。他首先向明皇提出对军役制进行改革。当时采取府兵制,军队平时为农,战时成军,男子21岁至60岁为服役期,险些是终生制。张嘉贞说服源乾曜,两人联名上奏,将服役期缩短为从25岁到50岁,并由百姓轮流参军从军。得到了明皇的批准,亦受到了全国军民的欢迎和推戴。
但源、张二人既不是思想家,也不是政治家,只能属于忙劳碌碌的干家。时过不久,明皇便开始皱眉头了。他们与姚、宋比较,切实其实有寰宇之别呀!
源乾曜事无年夜小,都得上奏请示,很少有个人见地,办事效率太低。老问题还没来得及办理。呈现出的新问题又堆积成山。但他仍旧不急不躁。明皇有时便又急又恨地说:“你呀,能不能快点办,切实其实像头老黄牛,半天挪不了一步!”而张嘉贞的刚愎自用、脾气暴躁的弱点,韶光一长,也逐渐显露了出来。他只信赖自己提拔的苗延嗣、吕太一、崔训、员嘉静四人,形成一个小团伙。被人讽刺为“令公四俊,苗吕崔员”。与其他官吏的关系,则越来越紧张,大有怨声四起的势头。
开元八年的仲秋八月,某夜月明星稀,明皇召幸杨氏侍寝。杨氏于景云年间身怀皇上三子嗣升之时,因受太平公主攻讦,皇上无奈,求张说觅药坠胎。后张说劝皇上另谋良计,生下皇子。自此杨氏永念张说大恩,侍寝之时便相机讯问张说,并哀求皇上善待张说。也便是在这天夜里,明皇梦见了张说……
张说自开元元年年末,被贬为相州刺史、河北道按察使,而后又贬为岳州刺史。谪居岳州的张说,空隙无聊、游山玩水,抚今追昔,触景生情,念及已经故世的五位老友,写成了《五君咏》组诗,分别伤悼魏元忠、苏瑰、李峤、郭元振、赵彦昭。张说与苏颋二人皆为当时诗界泰斗、文坛领袖,被誉为“燕许大手笔”(张说曾被封爵为燕国公、苏颋袭父爵为许国公)。张说与苏瑰、苏颋父子两代具有厚交,平素时有书函往来,诗词唱合亦相互传送。开元四年十一月,适逢苏瑰故世六周年,张说便将《五君咏》中《苏许公瑰》诗托人捎给此时任紫微侍郎的苏颋。苏颋见诗,哀痛难禁,竟放声大哭。同年闰十仲春,苏颋升任宰相,找了个适当机会,便将张说的几首诗作,呈给皇上。明皇阅后,很受冲动。个中一首《岳州作》是这么写的:
夜梦云阙间,从容簪履列。朝游洞庭上,缅望京华绝。潦收江未清,火退山更热。重郗视欲醉,懵满气如噎。器留鱼鳖腥,衣点蚊虻血。发白思益壮,心玄用弥拙。冠剑日苔藓,琴书坐废撤。唯有报恩字,刻意长不灭。
苏颋见皇上为诗中张说之忠心痴情所冲动,便乘机奏道:“张大人虽然屡被左迁,颠沛北国江南,然而,报国之心,思君之情,仍诚笃不移。”明皇缄默良久,虽未曾表态,却已深深记于心底。
不久,张说被迁荆州长史。数月之后,又封以右羽林将军检校幽州都督。后因并州长史张嘉贞晋升宰相被召进京,经由一番推敲,又授张说为检校并州长史兼天兵军大使。张说身着戎装回京谢恩,明皇大喜,又责成他带书稿于军中兼修国史。
武周末年,张说为魏元忠辩白,曾被流放钦州。中宗登基,魏元忠任兵部尚书时,张说曾任兵部侍郎。张说睿智超迈,数年间熟读兵书,研讨韬略,又时常巡边,参与战事,因此,对付调兵遣将,已不陌生。接替张嘉贞去并州之后,将军兵加以整顿改编,短短数月之间,便涌现了一个崭新局势。信息不断传到明皇耳边,明皇十分满意。但原任并州长史张嘉贞却有点儿撇嘴了。也不全是心怀妒意,而是鄙视张说对皇上的吹捧和献媚。
魏元忠
就在李隆基夜梦张说的第二天,收到了张说的密折奏报:散居于大同、横野周围的拔曳固族部落和同罗族部落,数年来一贯与北方汉族相安杂处,较为友好。然而,比来他们闻听散居河曲一带的突厥族降户全部被杀,便惊惧不安。乃至有人说,如其等去世,毋宁早反。臣以为急需安抚,相安无事,大唐圣朝,绝不滥杀无辜。然而,臣已收到兵部命令,指示立即讨伐。全部诛灭,不遗后患。臣以为欠妥,又不敢违反。只得如实急报,恭候圣上卓裁……
实在,兵部呈奏的王睃诛灭河曲突厥匪众的捷报,早就摆在了明皇披阅章疏的案桌上,却一贯没有在意思虑。经张说提醒,李隆基也以为如此不论黑白、鸡犬不留,大为欠妥了。他不愿看到张嘉贞(中书令兼兵部尚书)那倔犟横耿的表情,便密派心腹王毛仲直接去并州,与张说相机而行。
张嘉贞被蒙在鼓里,他还上奏张说,是文人带兵,临战畏缩不前。明皇只是含笑不语。他要等王毛仲归来之后,再作计较。
及至王毛仲赶到并州,想不到张说已经客岁夜同以北的少数民族部落了。副使李宪见告王毛仲,张说只带轻骑二十,叮嘱若旬日不还,即带兵讨伐。刚走那天,副使溘然想起,夜晚无论如何不能宿于他们的帐篷内,拔曳固族人反复无常,不堪信赖。便立即写了封书信,遣飞骑追赶送去。傍晚,送信的骑兵回来了,并带回了张说的复函。副使说着,将张说的复函交给了王毛仲。王毛仲展开看时,见文辞仍如先前那么俳谐,但字里行间,却蕴涵悲壮。个中有几句话,切实其实令人终生难忘。
那段话是:“吾肉非黄羊,必不畏食(不畏惧他们会吃);血非野马,必不畏刺(不畏惧他们来刺。他们有刺出野马血喝的习气)。士见危致命,此吾效去世之秋也“他们去了已经三天了,音信全无……”副使双眼含泪了。“当时我就要求前去,他哪里答应?还说,你笨嘴拙舌的……"
王毛仲鼻子一酸,眼泪便涌了出来。
当初张说是李隆基的侍读,他王毛仲是李隆基的家奴,张说虽为帝师,但从不鄙视他们这些下人。就像父辈、兄长那样关心爱护他们,每次外出归来,张说总爱带回一些小古董、小礼物,哪一次也少不了他王毛仲的。如今他亵服拴的玉坠,那便是张说从岳州带来送给他的。张说一点儿也不像姚崇、宋璟那样傲慢、摆架子。不过,张说命苦,颠沛流离多年,末了,竟然这样……
大家都认为张说回不来了。
王晙
朔方大使王睃诛杀突厥降户仆固都督勺磨,不便是诱人宴会高下的手吗?你能杀他们,他们为何不能杀你呢?
王毛仲越想越怕。
第四天过去了,张说没有回来。
第五天又过去了,张说还没有回来。
王毛仲沉不住气了。他让副使李宪带兵严阵以待,准备作战。然后,他率百余轻骑从太原赶往大同。
但是,他们在路途相遇了。张说与二十轻骑凯旋归来了。
夜晚,在大同张说宴请王毛仲。谈及这次与拔曳固、同罗诸部落酋长的会见,便有些后怕了。他说:“也算是九去世生平。刚到的时候,便被他们包围了。我再三申明来意,他们哪儿肯信?我只好让同去的二十人交出武器。但进入会谈的帐篷里时,二十人全部隔在了外边,而他们的刀斧手却埋伏在帐篷的四周。真没想到还能囫囫囵囵返回来……”
王毛仲很受冲动。他再三表明,回朝后一定如实向皇上奏报。
这天夜里,张说喝得大醉。当宴会结束,众人辞职之后,张说执着王毛仲的手痛哭流涕。他说:“真正出生人去世的,不是这一次,而是屡遭贬谪。在相州,我曾数次拔出匕首,想剖出自己的赤胆忠心,让人送给皇上。在岳州,我曾多少次想跳进长江、或跳进洞庭湖,像当年屈原那样……自己不断地与自己会谈,说服自己,不能轻生,要相信皇上是圣明的,终有一天,皇上会明白……”
王毛仲再次表示回朝后一定向皇上如实奏报。张说竟一下子跪倒在王毛仲的面前,感谢他了……
这便是此后人们传说的,张说为了东山再起,求王毛仲在皇上面前美言,竟跪下给王毛仲磕头,吻王毛仲靴子的丑闻。当然,越说越离奇,个中添油加醋的身分则越传越多了。
然而,王毛仲回京奏报之后,李隆基便决定重新起用张说了。
第二年五月,调张说参与了对西北叛胡的围剿之后,待秋日战事结束,玄月十九日,授张说为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这是张说第三次拜相。诏书中赞赏他说:“张说挺其公才,生我王国,体文武之道,则出将人相,效忠贞之节……”
张说这个文坛领袖,近年来,无论是率轻骑驰骋疆场,利用政治手段办理军事问题,还是直接统辖数万人马参与大的战役,都表现了一位儒将的超凡胆识和卓越才能。为皇上所看重的则是他的文武之道。有人说,李隆基对张说的再次起用,是开元初期拨乱反正、皇权巩固的任务由姚崇、宋璟两人帮助完成之后,进人歌功颂德、粉饰盛世的中期的分边界。也便是说,起用张说。是明皇看到“大治”的实现,盛世的来临,亟待颂扬皇上文治武功的须要。明皇在《命张说兼中书令制》中,称张说“道合忠孝,文成仪式,当朝师表,一代词宗。”便是要这“当朝师表”出来制订仪式,要这“一代词宗”出来粉饰升平了。
当然,张说接到委任宰相的诏书时,也曾故意推辞过,说什么“臣早已是诗人射策,载笔圣朝;晚以军志典兵,秉旄乘塞。”也便是说,晚年能在边防效忠就足意了。实在,张说企盼再出的欲望是相称强烈的。人活一口气,佛活一炷喷鼻香。他要让姚崇看看,他张说又堂而皇之地回朝当宰相了。气去世他!不过为了争做宰相,他乃至引起了许多清高人士的厌薄。当然,他自己也明白,这次回京任职,与许多人将是非常难处的。原来,明皇调张嘉贞任宰相,目的在于让他兼任兵部尚书,填补源乾曜不懂军事的不敷。但如今兵部尚书由张说兼任了,张嘉贞立即便感到张说对他的地位已构成严重的威胁。也便是说,这次张说入京,从开始便与张嘉贞形成了势不两立的阵势。况且,在中宗时,张说为兵部侍郎,那时张嘉贞不过是个小小的兵部员外郎,是张说的属下。而现在,只管同为宰相,但张说位在张嘉贞之下,只是个副宰相。张说不买张嘉贞的账,张嘉贞又刚愎自用、鄙视张说。这么两人共事,岂能久长?
让张说所光彩并且遗憾的是,在他这次受命的半月之前,即玄月初三日,那位博识莫测、容不下他张说,却又退而不休,仍旧顾问朝政的姚崇,与世长辞了。享年七十二岁。去世后赠扬州大都督,谥日文献。这位书写过中国历史上最为辉煌一页的名相。实在不同凡响。他在即将告别人间的病笃之际,还留下了两则盛传千古而不朽的佳话:一,他写了一篇长达千言,以戒子孙的《遗令》二、还留下一则《去世姚崇算计了活张说》的传奇故事。大概是姚崇临去世又想起了开元元年。他酒醉之后对魏知古讲下的大话如今真的要自作掩饰了。只可惜魏知古已经作古。
遗令,不同于遗嘱。嘱,是叮嘱,让子孙记住,令,则是命令,不管你是否乐意,必须得实行照办。姚崇最退却撤退下政治舞台,是为儿子不肖所累,以是,临终仍不放心,口气自然较为严厉。《遗令》很长,紧张有如下几方面的内容:
一、不能梦想富贵而见利忘义。开篇则说:“古人云,富贵者,人之怨也。贵则神忌其满,人恶其上,富则鬼瞰其室,虏利其财。自开辟以来,书本所载,德薄任重而能寿考无咎者,未之有也。”他列举了一些古代事例之后,又说"吾才不逮古人而久窃荣宠,位逾高而益惧,恩弥厚而增忧…王逸少(王羲之)云:‘俯仰之间,已为陈迹。’诚哉此言!比见诸达官身亡往后,子孙既失落覆荫,多至贫寒。斗尺之间,参商是竞。岂唯自玷,乃更辱先,无论曲直,具受嗤毁……”
二、他去世后不准儿子为他大办丧事,进行厚葬。他说:“孔丘亚圣,母墓毁而不修;梁鸿至贤,父亡席卷而葬。昔杨震、赵咨、卢植、张奂,皆当代英达,通识今古,成有遗言,嘱以薄葬。或濯衣时服,或单帛幅巾,知真魂去,身贵速朽。子孙皆遵成命,迄今以为嘉话。凡厚葬之家,例非明哲。或溺于流俗,不察幽明,咸以奢厚为忠孝,以俭薄为悭惜。至今亡者致戮尸暴骸之酷,存者陷不忠不孝之诮。可为痛哉,可为痛哉!去世者无知,自同粪土,何烦厚葬,使伤素业?若也有知,神不在柩,复何用违君父之命,破衣食之资?吾身亡后,可殓以常服。四季之衣,各一副而已。吾性甚不爱冠衣,必不得将入棺木。紫衣玉带,足便于身,念尔等勿复违之……”
三、姚崇生平不信佛教和玄门,以是不许儿子为他请和尚羽士念经作法。他认为,根本没有什么天国地狱,不要枉费钱为去世者乞求什么阴间福分。他只希望能把自己数年任宰相的业绩和这期间的言行,写人墓志铭,立于坟前。
这个《遗令》是从二十五史的《旧唐书·姚崇列传》中摘录下来的,没有丝毫改动和夸年夜。这位在距今1200多年前的大唐名相,值去世前病笃之际,头脑之复苏、见地之精辟、论述之深刻,无不让人叹为不雅观止!只管这是一个临去世的人,向自己子孙的嘱托和训教,口气既亲切又严明,通篇谈古论今、娓娓道来,但对付梦想富贵、虚荣奢华、愚蠢迷信、宠佛信道等,却是一声声捧喝;而那真理的光芒,却能普照千秋万代!姚崇写好《遗令》之后,他又对儿子说:“我过去曾对人讲过,我的墓志铭必请张说撰写。”
儿子姚奕说:“父亲与张说早有嫌隙,这是人所共知的。请他撰写,彷佛欠妥。”“不,正由于有嫌隙,他所写出的功德,人们才更以为真实可信。若请亲朋好友撰写,文中褒奖赞誉,人们则会以为那不过是浮语虚辞的奉承罢了。张说是当今文章年夜师,最近明皇又想重新起用他为宰相,恰好召他回京。值此春风得意之时,他不但不会抑低于我,肯定还会只管即便歌功颂德,以避免皇上和群臣对他非议,说他胸襟狭窄,太小家子气……"
“不过,他要推辞谢毫不写,怎么办?”
“张说一向酷爱字画古玩。我没之后,张说必定前来吊祭。你们可挑几件最宝贵的字画和古董玩器,放在我的灵座前边。张说来吊祭时,若是看一眼便拜别,这解释他还牢记前仇,便很可忧虑,你们得赶紧回家乡种地去,躲得越远越好。如果他瞥见这些字画古玩很感兴趣,你们赶紧呈上让他品赏。他若爱不释手时,你们就可乘机对他说:先父有遗言,让把这些字画古玩全部赠予给张叔。先父说,只有张叔才识得这些珍品。'张说如能接管,则可立即求他写墓志铭。碑石要早准备好,张说一旦写出来,便立时送皇上审阅,连夜安排刻石。我预见,数日后张说必定反悔。他派人前来索稿修正时,可见告他,皇上已经批阅了,再领他看一看刻好的碑石,便无话可说了。”
事情果不出姚崇所料,张说来吊祭时,一见这些稀世珍宝,便品赏起来爱不释手了。接管了赠送之后,求写墓志铭则无法推托了。张说手快,当天便将墓志铭写好。明皇阅后,亦大加夸赞:“开元贤相,理应如此称颂赞赏。张说的碑文也写得好呀,将会传之千古的。”
果真,数日后张说派人到姚家取文稿来了。谎说文章写得仓皇,须要修正。姚崇的儿子见告来人,皇上已经批阅,墓碑已经刻好,并领来人看了石碑。当张说听到派去的人回来申报请示之后,才知道是上了姚崇确当。他恨得跺着脚说:“我一个活张说,反被去世姚崇算计了。今日方知,我张说之才智,远不及姚崇呀!”
而张嘉贞之才智,却又远不及张说。时过不久,张嘉贞便败在张说部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