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23日,巴金故居、巴金研究会、华东师大中国当代文学资料与研究中央在上海作协共同举办了《寒夜》出版七十周年暨四十年代长篇小说创作研讨会,学者陈子善、李怡、杨联芬等三十余位中外学者出席研讨会。
研讨会现场
不同于巴金的《家》、《雾雨电》等前期的作品,巴金在《寒夜》中用笔极为镇静,创作风格由激情亲切倾泻转入深蕴细腻,是他艺术上最为成熟的一部作品,为那些在阴郁中挣扎的小人物喊出了痛楚的呼声:青春的消逝,空想的破灭,人性的扭曲,中年景熟背后的悲哀……
《寒夜》经历了若何的文本天生过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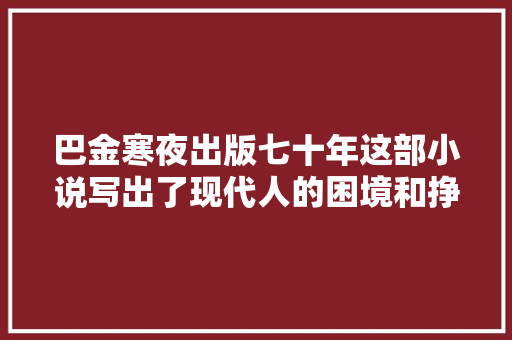
《寒夜》写于一九四五年抗日胜利前夕,完成于胜利之后,一九四七年出版,与小说故事发生韶光大抵相同。
《寒夜》的情节很大略。小说主人公汪文宣和曾树生是一对大学教诲系毕业的夫妇。年轻时曾经编织过许多俏丽的空想,希望能用自己的知识和力量办一所“村落庄化、家庭化”的学堂。但抗战爆发后,他们逃难到重庆,汪文宣在一家半官半商的图书文具公司当校正,曾树生在大川银行当“花瓶”。汪文宣的母亲为了减轻儿子的生活包袱,赶来操持家务,但汪母与曾树生婆媳关系反面,汪文宣夹在中间两头受气,且又患上肺病,家庭经济非常窘迫。末了曾树生跟随银行年轻的经理乘飞机去了兰州,汪文宣在抗降服利的鞭炮声中病去世,汪母带着孙子小宣回了昆明老家。两个月后,曾树生从兰州回到重庆,但已物是人非,伤感不已。
作为巴金生平最为圆熟的作品,《寒夜》在当代文学史上霸占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写作《寒夜》时背景如何,这本小说又经历了若何的文本天生过程?
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使国民经济受到了重创,出版业也受到了极大的影响,前五年仅出版长篇小说35部。六年抗战往后,中国的战区局势相对稳定下来,从而1943年到1949年景为中国长篇小说的复兴期。在这段复兴期中,国统区的作家不断以当代思想深入生活,通报当代人的代价不雅观念。出版于1947年的《寒夜》正是个中的范例之作。然而,《寒夜》的刊载发行亦有着颇多弯曲。
巴金故居的常务副馆长周立民先容:“《寒夜》第一次揭橥在一本画报上,连载了三次后这个杂志停刊了,但幸好巴老连续写下来了。而1947年3月出版这部作品的时候,恰好是国共两党关系紧张之时,民气不安定,通货膨胀加剧,买书的人大大减少。《寒夜》初版的出版,也只得到一篇像样的书评。进入新时期往后,《寒夜》这种风格要么被大家批驳,要么被大家忽略。”
周立民承认,此后因时期等诸多缘故原由,《寒夜》经历了一个经典化的过程。然而,经典除了是外部成分的天生之外,作品本身也要有相应的特质,才能超出前辈,形本钱身的特点。“《寒夜》里面有很多明确的特点,是值得我们把稳的。首先,三个人物的关系设定,是一个去世局,但也是一个说不完的局。三个人可以都是无辜的,但同时又能感到三个人身上的罪。其次,《寒夜》的开放性和阐释性超过了巴金其他的任何一部作品,它的冲突是内在声音和外部环境的交织。再次,《寒夜》里面没有英雄,由于没有反抗。这部作品写出了当代人的自我困境和挣扎,我们现在面对的很多境遇都是我们无法反抗,乃至无从躲避的。”
“末了,巴金师长西席对日常生活的阐述贡献是突出的,他长于将日常生活的阐述把握在虚和实之间,不完备掉进现实的境遇里面,又生发出梦魇、幻觉、变态生理等各种阐述手段。这样富于变革性的探索对巴金这一代作家来说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巴金的长篇小说《寒夜》
如何处理传统和当代的关系?
《寒夜》是对《家》的反思,家庭问题是中国人面临的诸多难题之一。巴金的《寒夜》从传统和当代的关系上欢迎了这一寻衅。
《寒夜》当中,汪文宣、曾树生和汪母之间的抵牾是家庭当中的经典问题。两个女人都爱着同一个男人,而且都是被同一个男人深爱。但两个女人之间的抵牾,又使得男人始终处在抵牾的状态下,他无从摆脱自己的困境。惟有男人处在身体不好的情形下,两个女人表现出和平的状态,但过后还是方枘圆凿。
辽宁师范大学的乔世华认为,“巴金的《家》与《寒夜》,在主题、情节设置、故事情节、命运走向等方面,实在都是相联系的。《家》中主人公的出走是离开家就可以得到新生,否则只能像其他人一样去世在家里。但《寒夜》当中,曾树生对付离开小家长久犹豫着,巴金彷佛不愿意再去重复先前离开家就可以得到幸福的模式,反而涉及到知识女性的心灵困境等诸多心灵上的思考。在写作《寒夜》时的巴金比写《家》时的更理性、成熟,他对家的文化有了重新的创造。”
相对付《家》,《寒夜》的进步有目共睹。然而,进步之下的深层缘故原由如何?中国公民大学杨联芬教授表示,“巴金的《家》和《寒夜》,代表了中国新文学关于家族叙事两个阶段的典范。《家》是离家出走反抗家族,而《寒夜》则是出走往后。《家》具有典范性,它对付新文化是一种意识形态的表达,比如它的反封建,当代和传统之间的对立等等。而《寒夜》的阐述超越了新旧二元论。巴金在《家》里写的大家庭是中国传统大家族的标准,而他在《寒夜》当中则供应了五四往后夫妻小家庭的情形。《寒夜》已经开始关注家庭问题的繁芜性,并非说年轻人反抗家长统统问题都可以办理,反抗之后出走之后会怎么样,巴金通过《寒夜》对《家》进行反思。”
“在传统和当代上,巴金肯定对‘旧’是不满的。在《寒夜》里面,汪母是一个贤妻良母,有很多令人酸楚冲动的描写,但巴金不完备赞许汪母。巴金在后来的修正版里,写了一个场景,汪文宣的妻子曾树生走了,汪母问儿子‘她还没有回来吗’?巴金有一句,‘实在她心里暗暗高兴’。可以看得出巴金对付汪母的否定性。但巴金对付‘新’也存在反思,显然曾树生在母亲这个角色上是很不合格的,把儿子交给学校,以为拿钱就可以办理统统问题。汪母和曾树生的形象,实在是一种象征,不但显示了传统文化和当代文化无法兼容,而且象征了文化的断裂。”
“传统和当代,既不能兼容,但必须相处在现实里头,怎么办?当然巴金在《寒夜》没有给出答案。新文化及至之后的革命期间,对付传统和当代,所选择的是激进,以至于末了夫妻可以反目,妻子戳穿丈夫,儿女戳穿父母。但本日父母对付儿女婚姻的干涉,则又是回到了五四之前。巴金的《寒夜》所引出的思路正是新文化不可避免取代传统的时候,当代文明和传统伦理若何才能较好的整。我想这是《寒夜》对我们最大的启示,我们该当通过重读《寒夜》做出更多思考。”
巴金 东方IC 图
巴金小说的抗战清醒
一贯以来,对付《寒夜》中汪家悲剧的紧张缘故原由,大多从社会阴郁、制度腐败,抑或汪家内部的文化冲突来阐明。然而,上海交通大学张中良教授指出,“它更深层的缘故原由是抗日战役。如果不是抗争,汪家不太会跑到重庆去,而三人的很多抵牾都是由于战役环境下家庭经济的窘迫引起的。”
从“九一八事变”之后,抗战书写是巴金小说或明或暗恒以贯穿的一条线。巴金在很长的一段韶光都是怀着开阔和激情亲切关注着革命。“巴金是敏感的作家,具有时期的良心。巴金心中始终有抗战的,他的许多作品从‘九一八事变’之后,都流露出对抗战的热切关心。小说《海的梦》由于‘九一八’爆发,将两个月前刚写了头七页的短篇小说改写为中篇,不再写他所爱的奇异的海上之梦,更要写陆地上残酷的现实。此后,巴金还写了短篇《发的故事》与长篇《火》第一部,反响日本统治下朝鲜公民的被压迫情形以及艰巨的解放斗争,表达对朝鲜公民甚大的同情。《第四病室》更以日记体的形式戳穿1944年的紧张场合排场,写出了抗战背景下中国社会的缩影。”
对抗战的关注背后,实在所蕴含的是对付正在展开着的革命的思考。专研巴金的学者黄长华认为,“从1927年到1942年,用写作来描述反军阀斗争的场景以及塑造青年革命者的形象,表明了巴金对付革命这个重大问题做了深入持久的思考。他借助于青年革命者的决议以及他们的结局,思考了革命的意义,青年与革命的关系,也磋商了革命的道路、策略、办法、出息问题。1927年到1942年可以说是巴金的革命期间。”
《寒夜》的家庭纠葛与革命有何关联?黄长华剖析:“从五四到上世纪四十年代,中国当代文学中人的内涵是在不断深化和发展的。当代作品中对付人的表现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从最初重视人及人的自然存在;第二个阶段从社会分解以及阶级层面表现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第三个阶段则是从人的主体存在来塑造个性化的人。巴金的《寒夜》正是在关注人的主体性的层面上,蕴藉地将政治进行隐喻,用沉着写实的语调刻画了个体生命的独特体验,展现了当代文学直面人生,探索灵魂的意义。”
“对巴金来说,在四十年代,一个活的人的全部思想感情是巴金写作的重点。《寒夜》是一部看不见英雄的小人小事作品,也是一个当代小家庭的思想冲突、个性冲突的交响曲。从家的意义上,《寒夜》展现了上世纪四十年代抗战前期一个小职员汪文宣一家的困境,事情不顺生活压力大,家庭内部婆媳抵牾以及亲情的疏离。此外,两个知识分子生活在同一个屋檐之下,有着诸多的不顺。它也是另一种类型的生活急流,表面上沉着,但深处翻滚着波浪。从女性评价的方面,在巴金的小说当中,女性大致可分为三类:传统女性、革命女性以及当代女性。《寒夜》中曾树生形象的涌现,意味着巴金对付当代女性的自我意识,还有她们的自由意志做了更多思考和表现。巴金一方面写出了当代小家庭里知识分子变革的过程,家庭的成员只管受到当代教诲,有学识,也有对平等自由原则切实其实定,但在当代家庭里面,他们缺少原谅,仍旧存在着各类抵牾,家庭成为亲人间相互侵害的沙场。另一方面也包含着某种隐喻。如果说《家》紧张写的是革命者的活动,以及他们对封建家族的批驳,那么《寒夜》则是挖掘出革命中的人性。《寒夜》夫妻二人也曾想凭借知识和力量办学堂,但后来空想被生活折磨之后,只能归于无。我想个中一个隐喻便是,如果知识分子失落去了空想,后果便是相互灭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