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源于:古诗文赏析gswsx.cn
君子于役(《诗经·国风·王风·君子于役》)
朝代:先秦
作者:佚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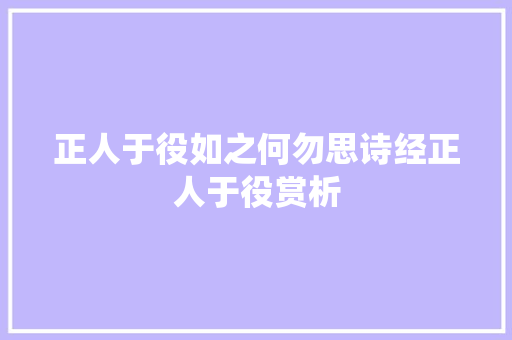
原文:
君子于役,不知其期。曷其至哉?鸡栖于埘。日之夕矣,羊牛下来。君子于役,如之何勿思!
君子于役,不日不月。曷其有佸?鸡栖于桀。日之夕矣,羊牛下括。君子于役,苟无饥渴?
译文及注释
译文
君子远出服役,不知它的限期。何时才能归里?鸡儿回窠栖止,日头垂挂天西,牛羊下山歇息。君子远出服役,如何能不相思?
君子远出服役,不知日月程期。何时才能重聚?鸡儿回栏栖止,日头垂挂天西,牛羊缓缓归至。君子远出服役,该是没捱渴饥?
注释
⑴役:服劳役。
⑵曷:何时。至:归家。
⑶埘(shí 时):鸡舍。墙壁上挖洞做成。
⑷如之何勿思:如何不思。
⑸不日不月:没法用日月来打算韶光。
⑹有佸(yòu huó 又活):相会,来到。
⑺桀:鸡栖木。
⑻括:来到。
⑼苟:表推测的语气词,大概,大概。
鉴赏一
这是一首写妻子怀念远出服役的丈夫的诗。所谓“君子于役”的“役”,不知其确指,大多数情形下,应是指去边地戍防。又“君子”在当时统指贵族阶层的人物,但诗中“君子”的家中养着鸡和牛羊之类,地位又不会很高,大概他只是一位武士。提及“贵族”,给现在读者的觉得彷佛是很了不得的。实在先秦时期生产水平低下,下层贵族的生活,并不比后世普通农人好到哪里去。便是在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西南少族民族中的小贵族,实际生活情形还不如江南一带的农人。
这是一首很朴素的诗。两章相重,只有很少的变革。每章开头,是女主人公用大略的措辞说出的内心独白。稍可把稳的是“不知其期”这一句(第二章的“不日不月”也是同样意思,有不少人将它阐明为韶光漫长,是不确切的)。等待亲人归来,最令民气烦的便是这种归期不定的环境,彷佛每天都有希望,结果每天都是失落望。如果只是外出韶光长但归期是确定的,反而不是这样烦人。正是在这样的生理中,女主人公带着嗟叹地问出了“曷至哉”:到底什么时候才能回来呢?
这下面的一节有一种天然的妙趣。诗中不再正面写妻子思念丈夫的哀愁乃至愤怨,而是淡淡地描述出一幅村落庄晚景的画面:在夕阳余晖下,鸡儿归了窠,牛羊从村落外的山坡上缓缓地走下来。这里的笔触彷佛完备是不用力的,乃至连一个形容词都没有,不像后代的文人辞章总是想刻画得深入、警觉,恐怕读者不把稳。然而这画面却很冲动人,由于它是有感情的。读者彷佛能看到那瞩目着鸡儿、牛儿、羊儿,瞩目着村落外蜿蜒沿伸、通向远方的道路的妇人,是她在冲动读者。这之后再接上“君子于役,如之何勿思”,读者分明地感想熏染到女主人公的愁思浓重了许多。倘试把中间“鸡栖于埘,日之夕矣,羊牛下来”三句抽掉,将末了两句直接接继在“曷至哉”之后,觉得会完备不同。这里有抒怀表达的节奏问题——节奏太快,没有起伏,抒怀效果出不来;同时,这画面本身有其特殊的情味。
熟习屯子生活的人常常看到这样的晚景。农作的日子是费力的,但到了薄暮来临之际,统统即归于平和、安谧和恬美。牛羊家禽回到圈栏,炊烟袅袅地升起,灯火温暖地跳动起来,农夫和他的妻儿们聊着闲散的话题。薄暮,在大地上涌现白天未有的和顺,农夫以生命保重着的东西向他们身边归聚,这便是古老的农耕社会中最平常也是最富于生活情趣的时候。可是在这诗里,那位妻子的丈夫却犹在远方,她的生活的缺损在这一刻也就显得最为强烈了,以是她如此怅惘地期待着。
这诗的两章险些完备是重复的,这是歌谣最常用的手段——以重叠的章句来推进抒怀的冲动。但第二章的末句也是全诗的末句,却是完备变革了的。它把妻子的盼待转变为对丈夫的顾虑和祝愿:不归来也就罢了,但愿他在外不要忍饥受渴吧。这也是最平常的话,但个中包含的感情却又是那样善良和深厚。
这是古老的歌谣,它以不加润色的措辞直接地触动了民气中最易感的地方。它的天然之妙,在后世已是难以重复的了。
鉴赏二
没有天马行空的想象,惟有低徊反复的小叙;没有夸年夜浪漫的铺陈,惟有直截真实的浅唱;没有云谲波诡的咏叹,惟有无痕无迹的自吟……这便是《君子于役》的笔墨特色,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君子于役》里的那位思妇……流露出的感情特色。
按理说,《君子于役》应属于一首思妇诗,但我以为这与女主人公(确切地讲应是男女主人公。天各一方,在天的那一边的男主人公又何尝无此感想熏染,痛哉!
)的分外经历和纷杂情绪大为干系。《君子于役》绝不是唐朝的秋闺怨诗,这里没有可予寄思的明月,也没有缠意绵绵的柳带,更没有满载悲秋的游丝;有的只是一斜抹不去的落日残曙,一群洁无渍的暮归羊牛,还有一位意难平的平凡村落妇,仅此,而已……
这不是一副“明月——阑干——美人”式的动人画卷,而正是一副“薄暮——薄暮——村落妇”式的残破画面——这才是真正的情思呵!
是真悲彻,不是假矫情!
《君子于役》共有两章,虽然两章的笔墨大体相同,表达的意思也无甚出入。但是表达的情绪却截然不同。我以为大体可以将女主人公的内心活动的形态表示成倒S型。其九曲回环不说,单单是倒S型中间的那一段向上升的部分,也是极其繁芜的啊!
其间的徘徊彷徨,千次万次的抵牾,又岂是几个句式几个笔墨所能表达?!
倒S型前一段低落的部分(实在说“低落”也不是太好,只因思妇之情太浓太重,谁能知晓在这之前她的内心是细浪柔沙还是波涛澎湃?哀哉!
姑且暂明“低落”吧!
),是表现在“君子于役,不知其期”这句。君子?呵,未必如《诗经》其他诗里的“君子”所指“贵族公子”相同吧?妻子是一位极其平常的“田家贤内助”,想必此“君子”也崇高不到哪儿去吧?只是在这位妻子的心中,她的丈夫是高大光辉的,光辉得能和上层“君子”同居!
可以大胆地推测,她的丈夫便是一位平凡男丁,他的活动范围一样平常不出“农田——房舍”,只是由于统治阶级的征兵徭役,他才去了边陲,去防守那一弯时盈时亏的冷月!
在这之前,他们的关系正是“牛郎织女”般的关系,当然,现在也是,或许将来的某一天,他们还是!
之后便是那平滑的一段。“鸡栖于埘,日之夕矣,羊牛下来。”然而这看似平平地描写家畜的一笔,却也是包含着各类离恨和声声嗟叹的啊!
就连畜生都有归期,都有“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报酬,为何一个活生生的“人”,竟是一去不归,遥遥无期?等待并不痛楚,痛楚的是漫漫无期的等待!
堕泪并不迷离,迷离的是泪已流尽,而你却不再来!
可痛楚,堕泪又有何用?她只能悄悄地等待……
可再倔强的女子,也抵挡不住去叩舒怀念之门的诱惑——她想逃出这思念的老屋,可奈人单力薄,只能倚着门框逐步地坐到地上,她真的无能为力了。可那炽热的心瞬间又升腾起依依绵思的觉得,于是她喊出:“君子于役,如之何勿思?”是啊!
我的丈夫在外服役,作为妻子的我怎么能不思念他呢?此时的她,感情比开始的“我的丈夫怎么还不回来呢?”时的低吟细语,是要炽热得多的。因此,此处即是那倒S型中间上升部分的前半段。
“君子于役,不日不月,曷其有佸?”我的丈夫在外服役,那日子极为漫长。什么时候可以终得一聚?“不日不月”,那是什么?是“年”啊!
人生苦短,能有几番循环几次年?何况是在那个奴隶社会!
她的感情,她的思念之情,不仅没有冷却,反而更加升温。“天若有情天作福,如何灰灰在今暮?”这句诗是我以前有感而作,如今拿来放在这位思妇身上,我以为也是很得当的。
此层的语调,感情不仅没有降落,减缓,反而更加升高,增速,像阳春三月的花瓣,红遍枝头的同时,零飞落地后更能艳煞整片绿野!
这是每一位能身临其境,感其所感的读者所能达成的共识。以是,此层即为倒S型中间上升部分的后半段。
叹叹叹——又到了该死的薄暮了——整片整片的羊牛又要归圈了,当然也少不了鸡的“戏份”。“鸡栖于桀,日之夕矣,羊牛下括。”这几句险些与第一章的“鸡栖于埘,日之夕矣,羊牛下来。”千篇一律,只是将“埘”更换成“桀”,将“来”更换成“括”。两层的意思也一样,借家畜的归圈侧面陪衬丈夫的归期茫茫,不如畜生。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煎熬苟活不得,魂归故乡亦不得——抵牾啊!
此层的感情虽然较之“君子于役,不日不月,曷其有佸?”平缓些,但比之同层的“鸡栖于埘,日之夕矣,羊牛下来。”还是更为“高调”点。由于至少,对付一位昼夜思君的妇人来说,每过一天,就要多看这些鸡,羊,牛一眼,她的“妒恨心”怎能不随之多添一分呢?当然,无论如何,此层还是倒S型后半段那平缓的部分,这是毫无疑问的。
接下来便是倒S型那末了的一段了。“君子于役,苟无饥渴?”我的丈夫在外征役,大概,希望他不后悔饿着,渴着吧?此时的思妇,彷佛已经有了一些妥协之意。切切关怀更进一步,绵绵待归之情,却是令人感到可惜,不仅扼腕唏嘘地更退一步了!
这是她的放弃吗?显然不是,这是言之平,思之切啊!
整天在村落口翘首等着夫君归来或许真的是一个稚子得让那夫君都不禁抿嘴苦笑的想法,但我现在就只希望他能吃饱喝足,边陲的景象很冷,在天的这一边的奴妾只希望你能多加一件衣服——难道就这点哀求都不能如愿吗?总之,她不是什么大人物,她便是一位在生活上别无他求的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女子。
以上便是这自谓之倒S型的女主人公感情颠簸的大略评介。
或许从文本自身看,《君子于役》险些无任何“艺术性”可言。措辞上既无华美的词华,有无多变的句式;内容上也只是倾述女主人公的苦思,彷佛也没有多少吸引人之处;选材上也只是重复地讲了两次鸡,羊,牛的活动。让人总以为这首诗歌并不是很“美”。的确,不仅不“美”,而且很“粗糙”。然而虽然没有唐诗那样的意境幽然,“美”得都想让我们普通读者跳入那个意境了,但我却以为它很“实”——“实”不也是一种不是“美”的“美”吗?
正如鲁迅评《红楼梦》时所说的,《红楼梦》与巴尔扎克笔下的许多著作一样,是可以由说话看出人来的。我认为《君子于役》这篇诗歌,当我们将自己的灵魂与情绪注入个中去欣赏它时,确也可以从中看出一个鲜活的奴隶社会下层女子这一形象来的。
对付《君子于役》,我彷佛有说不尽道不完的话,囿于篇幅,就此打住吧!
大抵我的灵魂也已嵌入个中了?!
言不尽意,赋诗续之,以作内心之余响。诗曰:
稀疏泪点湿昙花,何日一步跨天涯?
古来离恨多春秋,今到征思几冬夏。
羊牛更有牧人催,夫君竟无归声达。
一怨不经千怨出,依依绵思泣烟霞!
鉴赏三
《君子于役》出自《诗经·王风》。《诗经》是我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反响了我国西周初至春秋中叶的社会生活。个中有一部分诗歌反响的内容是丈夫去服那遥无归期的兵役或徭役后,妻子在家默默地痛楚思念。《君子于役》正是这样内容的一首诗,不仅深刻地戳穿了当时重役之下公民生活的巨大痛楚,而且以统治者无休无止的重役给公民婚姻造成的危害,间接地反射出公民对自由幸福生活的神往和追求。
这首诗在中国诗歌史上有着极为主要的地位:“鸡栖于桀下牛羊,饥渴萦怀对夕阳。已启唐人闺怨句,最难消遣是昏黄。”(许瑶光《雪门诗抄》卷一《再读〈诗经〉四十二首》)个中“已启唐人闺怨句”一句,高度评价了此诗在中国诗史上的首创性地位。可以说,从此诗开始,便逐渐形成了“早晚闺思”的原型和母题。钱钟书师长西席在《管锥篇》里引白居易、司马相如、吕温、潘岳、韩、赵德麟等人的诗赋文句后的评价——“取景造境,亦《君子于役》之遗意。”(钱钟书《管锥编》卷一《毛诗正义六十则·君子于役》)——便是对此极有见地的解释。
《君子于役》以其内容的深刻性和主题的首创性使其传之后世,在技巧上也给此后文人和后世的读者诸多的可资借鉴的地方:
在写法上,这首诗最大的特点是“赋”与“兴”的利用。
“赋”便是“敷陈其事而直言之”,普通地说,便是平铺直叙。这首诗的两节都利用了这种技巧,对鸡回巢栖,夕阳西沉,羊牛归栏的田舍生活平铺直叙,作了极为生动而细腻的描述。与此同时,这首诗还利用“兴”的手腕,即“先言他物引起所咏之辞”。“鸡栖于埘,日之夕矣,羊牛下来”, 鸡栖于桀,日之夕矣,羊牛下括”。 不仅是直接写景,是“赋”的利用,更主要的是,诗歌通过这几句刻画的日常生活细节,点染着思妇家庭生活的情景与妻子思念的气氛。试想一下,夕阳西照之时,鸡儿、羊儿、牛儿正在归圈,而思妇却形单影只,目睹此景,不能不令人触景伤情,思念起“于役”在外不能归家的丈夫。这正是“兴”的奥妙利用,诗中用鸡、羊、牛的晚归“兴”“于役”的丈夫不能归家的事实,从而淋漓尽致地写出了女主人公倚门望归人的形象和希望“于役”的丈夫早日归家的生理。然而,女主人公深深地明白她那种美好的希冀只不过是不现实的抱负。因而墨客的笔锋随着女主人公心情陡然一转,从“君子于役,如之何勿思!
”到“君子于役,苟无饥渴?”这样,就把她无奈的思念化为难刁难丈夫深情的祝愿,祝愿离家在外的丈夫不要受饥挨渴,一颗妻子的心温顺得令人为之深深冲动。总之,这首诗以“赋”的手腕对鸡回巢栖,羊牛归栏的田舍日常生活细节浓墨铺排,既描绘出思妇家庭生活的环境与氛围,又“兴”丈夫“于役”不归的事实,从而真切动人地表达了思妇的愿望丈夫安然归来的心情。
同时,在构造上采取重章叠句的艺术形式,也是本诗的特点。
这首诗的两节在句式的利用上基本同等,采取了重章叠句的艺术手腕,使诗的构造更为谨严。整首诗高下两节只有三句有较大不同:首节第二句是“不知其期”,第二节为“不日不月”;首节第三句是“曷至哉?”第二节为“曷其有?”首节末句为“如之何勿思! 第二节是“苟无饥渴? 其它句子不是完备一样便是仅改一字。 这种复沓叠唱不仅使整首诗富于音乐性和节奏感,而且使诗歌蕴含的感情更显深厚。由于重章叠句的艺术构造每每对诗歌的艺术气围和意境起着极强的营造作用。诗歌就在反复地吟咏中把思妇内心无奈思念的悲苦和深情祝愿的泪水延伸得绵绵涟涟,极为浓郁,使读者的心仿佛与深情款款的妻子一同黯然欲泣。
此外,这首诗采取当时的口语,朴素简炼,描述了一个朴拙动人的生活画卷,状景言情,真实纯朴,成功地刻画出思妇倚门怀人那柔肠寸断,悲哀凄婉的艺术氛围。正如明人谢榛所言:“统统景语皆情语。”这首诗正是以简洁朴质的措辞描述融情的晚景,表现思妇悲哀的心境,动听至深,的确达到了诗歌所哀求的情景交融,意与境谐的至高境界。
本号长期征稿,稿酬从优,哀求原创,QQ 917293188(微信同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