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日是第三十五西席节,静下心来,写了篇关于教诲与西席的短文,以此祝愿老师祈福教诲。
——谨以为记。
大家都知道,“尊师重道”是中国人的传统美德。孟子的学生乐正克在《礼记·学记》中就曾说过:“凡学之道,严师难堪。师严然后道尊,道尊然后民知敬学。是故君之所不臣于其臣者二:当其为尸,则弗臣也;当其为师,则弗臣也。大学之礼,虽诏于天子无北面,以是尊师也。”
但是,在历史的不同期间,老师们的地位与荣誉是曾跌入谷底的。曾几何时,老师们就有个非常有“味道”的别称,叫“臭老九”。臭则臭矣,还行九,看来,这地位是低得没治了。当时,老师们(知识分子)是排在“地、富、反、坏、右、叛徒、特务、走资派”之后的,因其位居第九,以是才得到了“臭老九”的美号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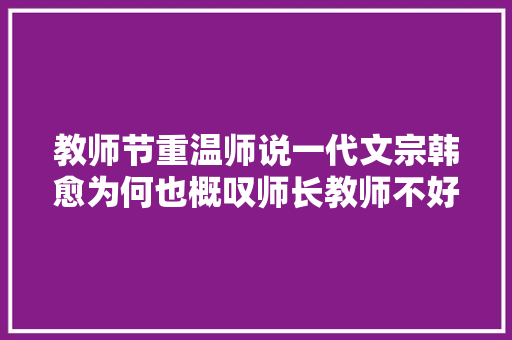
实在,“臭老九”一词并不是当代才有,它是源于蒙元,“元制,一官(政府官员)、二吏(不能擢升为官员确当局雇员)、三僧(佛教僧侣)、四道(玄门羽士)、五医(年夜夫)、六工(高等工程技能职员)、七匠(低级手工技能职员)、八娼(歌舞姬或妓女)、九儒(知识分子)、十丐(托钵人)(《陔余丛考》)。”儒者的身份排在娼之后,仅仅高于托钵人。由于元朝存在韶光较短,这样的排名鲜为人所识,以是,流传不广。
直20世纪60年代中期,“臭老九”其名才臭名远扬。当时,“臭老九”并非专指老师,而是指统统有文化、有学识的知识分子。当时,一大批知识分子被批斗劳动改造,有的乃至命丧黄泉。当时有人就曾说过,“秦始皇算什么?他只坑了四百六十个儒,我们坑了四万六千个儒。”
这种征象,直到1978年才有所改不雅观。1978年往后,“臭老九”大多规复名誉,重新走上新的岗位,为社会奉献余热。但是,由于轻视或敌视知识的不雅观念延习已久,以是,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又涌现了“研究导弹的,不如卖茶蛋的”这一脑体倒挂的奇异征象。
高考制度的规复,一度曾让老师们又成为神圣讲坛的主导,并为国为家培养了一代又一代精彩人才。但是,因受金钱至上不雅观念的影响,如今的老师,无论是其权柄还是地位,又受到责怪与寻衅,俨然成为社会的弱世群体。实在,在社会代价多元的时期,不管盛世、衰世,有如此征象是非常正常的。比如,我们引以为傲的大唐,也就有过不尊师重教、斯文扫地的时候,为此,有着一代文宗之誉的韩愈老师曾经愤而著《师说》。
韩愈的《师说》因入选择中小学教材而广为人知。但是,韩愈因何而著《师说》却鲜为人知。韩愈是是唐代精彩的文学家、思想家、哲学家、政治家,被尊为“唐宋八大家”之首,与柳宗元、欧阳修和苏轼合称“千古文章四大家”,有“文章巨公”和“百代文宗”之名。
虽然韩愈如此精彩,但是,由于他生活的时期正是安史之乱后的分外期间,曾经的盛唐正日趋没落,这给他的人生带来许多困惑与纠结。韩愈虽出身世家(韩愈系西汉韩王信之后,其父亲韩仲卿官居秘书郎,去世后赠尚书右仆射),但是,3岁即遭丧父之痛,其后,他由兄长韩会抚养。韩愈11岁那年,哥哥韩会因受元载牵连,贬韶州刺史,到任未久便病逝于韶州任上。是年,韩愈年仅12岁,嫂嫂就成了他唯一的依赖。
韩愈好学,也会学,成绩更是杠杠的。以是,韩愈19岁那年,便信心十足地进京赶考,“我年十八九,壮气起胸中”。可惜的是,韩愈第一次科考名落孙山,心情沮丧至极。实在,韩愈没能考上,未必是文章写得不好抑或是临场发挥失落常,可能也跟他为人低调、不爱混圈有关。
韩愈“在京八九年矣,足不迹公卿之门,名不誉于士大夫之口”。比较而言,其他墨客整天带着干谒诗和行卷混迹于王公大臣之间。而唐朝科举考试并不糊名,换言之,试卷上没有装订线,不会密封。阅卷老师可以看到考生的名字,一旦以为哪个名字眼熟,自然而然会优先录取。为人低调、不爱混圈的韩愈,难免亏损。之后,韩愈接连又考了两次,均不中。
公元792年,25岁的韩愈第四次参加科考,终于考中进士。这一年,金榜题名的还有李绛、崔群、武元衡、裴度,都是将来赫赫有名的大人物。以是,那一届科举史称“龙虎榜”。韩愈25岁中进士,说实话不算晚。想当年,白居易27岁中进士,喜滋滋地写下“慈恩塔着落款处,十七人中最少年”。
在唐朝,考中进士并不一定有会捧上金饭碗,还得经由各种考察、培训才能入朝为官的。个中,最紧张的路子,便是要通过吏部的博学宏词科考试。博学宏词科考试,韩愈连考了3次,都未通过。眼看,从正经路子步入仕途,是难上加难了,本来不屑逢迎的韩愈,也疑惑起自己的人生了,于是,韩愈也同其他许多一样,选择了“曲线就仕”,他跑去找宣武军节度使董晋。贞元十二年(796年)七月,韩愈受到董晋推举,得试任秘书省校书郎,并出任宣武节度使不雅观察推官。
董晋对韩愈有知遇之恩,在任不雅观察推官三年间,尽心赞助董晋。但是,好景不长,贞元十五年(799年)仲春,董晋逝世,韩愈随董晋灵柩离境。。同年秋,韩愈应徐泗濠节度使张建封之聘,出任节度推官,试协律郎。贞元十六年(800年)春,韩愈回到徐州,于夏季离开徐州,回到洛阳。同年冬,韩愈前往长安,第四次参吏部考试。这次考试,韩愈得以通过铨选。次年春,韩愈被任命为国子监四门博士。
韩愈的“四门博士”,实在就一教职,其职责便是管教七品以上侯伯子男的子弟以及有才干的庶人子弟。普通点说,韩愈的四门博士便是国子监里重点班的班主任兼国学老师吧。韩愈本来是靠学习成绩精良,才混到现在这个教职的,但是,他进入国子监后,却创造了让贰心寒的征象——由于科场阴郁,朝政腐败,吏制弊端重重,致使不少学子对科举入仕失落去信心,因而放松学业;当时的上层社会,看不起教书之人。
在士大夫阶层中存在着既不愿求师,又“羞于为师”的不雅观念,直接影响到国子监的传授教化和管理。韩愈对此咬牙切齿,便愤而写下一篇流传后世的《师说》,以澄清人们在“求师”和“为师”上的模糊认识。
古之学者必有师。师者,以是传道受业解惑也。人非生而知之者,孰能无惑?惑而不从师,其为惑也,终不解矣。生乎吾前,其闻道也固先乎吾,吾从而师之;生乎吾后,其闻道也亦先乎吾,吾从而师之。吾师道也,夫庸知其年之先后生于吾乎?是故无贵无贱,无长无少,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也。
古代求学的人一定有老师。老师,是可以依赖来传授道理、教授学业、解答疑难问题的。人不是生下来就懂得道理的,谁能没有迷惑?有了迷惑,如果不跟从老师学习,那些成为疑难问题的,就终极不能理解了。生在我前面,他懂得道理本来就早于我,我该当跟从他把他当作老师;生在我后面,如果他懂得的道理也早于我,我也该当跟从他把他当作老师。我是向他学习道理啊,哪管他的生年比我早还是比我晚呢?因此,无论地位高低贵贱,无论年纪大小,道理存在的地方,便是老师存在的地方。
由于当世轻师寡,韩愈又发出浩叹:
嗟乎!
师道之不传也久矣!
欲人之无惑也难矣!
古之贤人,其出人也远矣,犹且从师而问焉;今之众人,其下贤人也亦远矣,而耻学于师。是故圣益圣,愚益愚。贤人之所以为圣,愚人之所以为愚,其皆出于此乎?
韩老师说的是啥意思呢?用当代措辞来表述便是,古代从师学习的风尚不流传已经良久了,想要人没有迷惑难啊!
古代的贤人,他们超出一样平常人很远,尚且跟从老师而请教;现在的一样平常人,他们的才智低于贤人很远,却以向老师学习为耻。因此贤人就更加圣明,愚人就更加愚蠢。贤人之以是能成为贤人,愚人之以是能成为愚人,大概都出于这吧?
实在,韩愈的《师说》之以是能终极成文,还得益于他的一个名叫李蟠的学生:“李氏子蟠,年十七,好古文, 六艺 经传皆通习之,不拘于时,学于余。余嘉其能行古道,作师说以贻之。”
说的是有个叫李蟠的孩子,只有十七,喜好古文,六经的经文和传文都普遍地学习了,不受时俗的拘束,向我学习。我赞许他能够遵行古人从师的路子,写这篇《师说》来赠予他。
韩愈喜好的这个学生李蟠,李蟠也确实没负恩师所望,第二年(唐德宗贞元十九年),年仅18岁的李蟠便考上了进士,并且还有第一名,18岁得中状元,这在两千多年的科举史上,也属罕见。
实在,教诲的发展与改进,是须要时日的,不论古今中外,都是有过弯路与改变的。以是,我们要相信韶光,相信人类的聪慧,社会以及众人会再对付教诲事情及广大老师们给出一个精确选择的。
本日,是第三十五个西席节,老黄在此唯愿天下为师者都能秉行“不以物喜、不以己悲”之心态,励己树人,只管耕耘,别问收成,相信,韶光会让社会及众人再给教诲与西席一个再认知与再认同的选择。末了,老黄在此谨祝各位老师身心康健、节日快乐!
(图片来自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