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黄霸刀
当年的知青生活,相去已50多个春秋了。应了一句老话,光阴似箭,岁月如梭。然而光阴流逝,影象犹存,就像一棵迢遥的树,时时时会从树上飘落一两片叶子,在面前晃动,在心中幽鸣,让人既伤感又怀念。一个年过古稀的老人回顾年轻时的往事,有点靠不住。由于韶光让统统都变了味。我下乡的那个地方,是个比较封闭的山村落,从漳州坐两个多小时汽车到枋洋镇(当时叫公社),再走五里路才到内枋村落,也便是我生活了一年多的内枋大队。我先在第一小队,往后调到第三小队。都在溪边。
那是一条宽阔而浅近的小溪,满溪的鹅卵石,溪水就在卵石间穿行,发出欢畅的脚步声。岸边有许多翠竹,一丛连一丛,延绵出山。溪上没有桥,过溪走跳桥。跳桥便是一块块大卵石间隔排列,跨石而过,水在脚下走,人在石上行。空身,走起来很有味道,特殊是女知青过跳桥,身轻如燕,让人想到惊鸿什么的,有点诗意。
用现在的话来说,是山村落里一道亮丽的风景。如果带点东西,或挑着担子,女知青就要让位当地的村落姑了。她们挑担子过跳桥的身姿,旁边摆动,前后搭配,节奏分明,更是山村落的一道亮丽的风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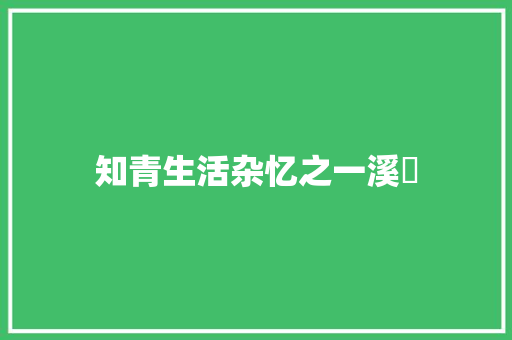
每当这个时候,我的脑筋里便会浮出这样的诗句,“小楼一夜听春雨,深巷明朝卖杏花。”年轻时爱好文学,背了许多古诗词。可是跳出来的诗句却有点莫名其妙。现在细想陆游全诗的境意,联系当时的处境,彷佛也有一点点道理。所谓潜意识使然。
这溪最让人流连的还不是跳桥和跳桥上的风景,而是溪里的一种鱼,叫溪鳁。我不知道溪鳁的学名怎么叫,彷佛是喷鼻香鱼。这鱼不大,约两只母指长,在滚水里一烫,用筷子夹起来,抖一抖,肉便掉了下来,极清甜。用漳州话说,连舌头都想卷进去吃。时隔几十年,现在想来,还会流口水。
听说这鱼不但味道鲜美适口,还极有营养代价。还听说,日本人想把整条溪买断,单为了这溪鳁。开价100万公民币。100万,在当时是个天文数字。听说县里已经赞许了,公社的章也盖了,就等大队的见地。大队支部布告说,莫说是100万,便是用一座金山再加一座银山也不换。
我问布告,有没有这回事?他笑了笑,又摇了摇头,什么也没说。我想这是群众性的创作,有如现在的段子,以表达一种感情,一种对自家溪鳁的自满感。不必当真。这种创作遵照当时革命样榜戏“三突出”的创作原则:在浩瀚的人物当中突出正面人物,在正面人物当中突出英雄人物,在英雄人物当中突出主人英雄人物。以是,大队布告就有点“高大全”,语出惊人,大义凛然了。
布告姓蔡,平时话很少,精明干练。他是大队知青领导小组组长,我是副组长,又常常在大队帮写一点总结和标语,打仗多,比较熟。
有一次,我正在大队部写标语,听到溪里敲石头的声音,出于好奇,便下楼去看。大队部在溪边,出了门过一条路便是。我看到一个人拿着一只大铁锤,在敲溪边的一块鹅卵石,敲两下,放下锤子,掀开石头,居然有一条溪鳁浮在水面。他得意地看了我一眼,把鱼涝起来,扔进背后的鱼笼里。
我从来没有看过这种抓鱼的办法,很新奇。我把这个创造见告布告,他淡淡一笑,说,石下有洞,洞里的鱼,他懂得看,一敲,把鱼震晕了,就浮上来了。又说,我带你去捉,另一种办法的。于是,在一个风和日丽的早上,我便和他一起,溯溪而上,挑一处溪面局促的地方,把网拉开,一人一边,绑在溪边的树干或石头上,然后,跑到上游赶水。所谓赶水,便是站在溪边往水里扔石头。赶了一下子,布告说,好了。
我们就收网,果真,有许多溪鳁挂在网上。我们一条条地捉起来,放到鱼笼里。鱼在手中甩尾巴,欠妥心,就又掉到水里去了。他便手把手地教我,如何抓得牢,不让鱼滑掉。这是我平身第一次在溪里捉鱼。不一会儿,我们捉了半笼子。他说,够了。
我们便回去,让大队妇女主任去煮鱼汤面,再把在大队部的几个干部,大队长,民兵营长,司帐等,叫来一起吃,吃得欢天喜地。我们那个大队穷,一个工分值二分七厘,一个强劳力一天记十个工分,也便是二角七分钱。知青一样平常与妇女同,记七个工分。
一天劳作,只赚一角八分九厘。还是照顾的,真较起真来,我们哪能与屯子的妇女比较。当时,人比较纯朴,记工分时,妇女们不与我们计较,知青们是毛主席让来的,有什么好说的,照顾便是了。
社员之间,就不那么大略了。每天晚上到队间(小队部)记工分,都要比,都要吵,有时,“吵得麦子都熟了”,说到底也只是一分半分的事情。出了队间,统统又都只当风吹去,该叫婶还叫婶,该叫姐还叫姐。
时的大队干部,大都比较清廉,吃鱼汤面,工是公家的(我和布告去捉鱼,用的便是队里的工),面是公家的,较起真来,便是多吃多占,我也有一分。就这事,布告还让司帐记上,算事情餐。司帐便负责地写上,面两斤二角三分钱,味精一包二角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