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粉骨碎身浑不怕,要留明净在人间”
于谦在青年时期写下著名的《石灰吟》“千锤万凿出深山,烈火点火若等闲。粉骨碎身浑不怕,要留明净在人间。”这首诗成为于谦命运的注脚、生平的写照,而“明净”也成为他最主要的精神底色。在明朝阴郁的官场中,于谦始终洁身自好、清廉自持,如一袭白袍,终生未曾熏染污迹,不仅“下不纳赂”,而且“上不贿要”。公元1444年前后,内阁三杨相继谢世,宦官王振弄权,把持朝政,可谓是“朝廷枢府,布列私人;阉党故旧,把持要津”。在这种情形下,很多官员对王振如蚁附膻、呼为翁父,而地方大员回京时也多拜见并贿以重礼。当时于谦正巡抚山西、河南,他的下属劝告他回京时也去拜见王振,哪怕带些地方土特产也好。于谦听罢,举起自己的袖子诙谐地回答:带有“两袖清风”。为此,他还专门作了一首《入京》:“手帕蘑菇与线喷鼻香,本资民用反为殃。清风两袖朝天去,免得闾阎话短长。”实在,历史不仅书写于浩瀚的史籍中,也存在于芸芸众生的评判中,“两袖清风”这个典故能够千古流传便是百姓对付谦高洁品质的最高褒奖。于谦自奉俭约,终生廉明,“及籍没,家无余资,独正室鐍钥甚固。启视,则上赐蟒衣、剑器也”,《明史·于谦传》中的这一段,仿佛是他在蒙冤受去世之后对大明王朝的无声告白,读来让人震荡、让人冲动。
寸心洁白,可以昭垂百代清芬。于谦行为上的廉明源于他精神上的高洁。他所看重的不是物欲,而是名节。他在诗中说:“名节重泰山,利欲轻鸿毛”,“但令名节不堕地,身外区区安用求”。有时,他也能感想熏染到在全球流俗中洁身自好的困难,但还是像柏树一样“节操棱棱”。其《北风吹》一诗就表达了内心的这种坚毅:“北风吹,吹我庭前柏树枝。树坚不怕风吹动,节操棱棱还自持。冰霜历尽心不移,况复阳和景渐宜。闲花野草尚葳蕤,风吹柏树将作甚!
北风吹,能几时?”只要心中坚守着对付暖春的崇奉,就不会畏惧隆冬的侵凌。于谦时时不忘敦品修德、雕琢节操,在他的诗作中,我们常常能看到明月清风、茂林修竹、秋菊冬梅这些经典意象。他笔下的夜空“明月扬素辉,修篁散疏影”,他笔下的山峰“幽崖树色经霜古,绝顶松涛入夜惊”,他笔下的秋菊“晚喷鼻香好在东篱菊,相伴秋霜入鬓华”,他笔下的梅花“明净可能陪雪月,孤高元不惹尘埃”,读来让人觉得表里澄澈、神骨俱清。于谦生活的时期,正是“恢张皇度,粉饰太平”的台阁体盛行之际,但是他的诗歌却别具一格、风致卓然,为当时寂寞的诗坛增长了一股清正浩然之气。
“但愿苍生俱饱暖,不辞辛劳出山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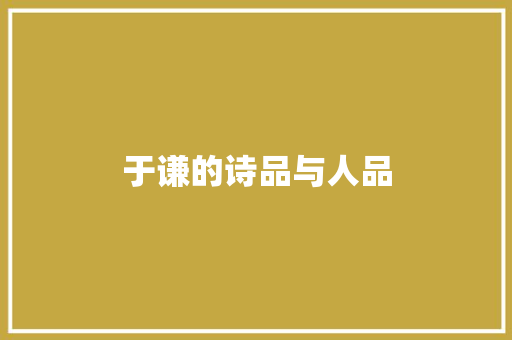
在于谦的诗歌中,有一首诗与《石灰吟》齐名,但其歌咏的工具与明净的石灰形成了强烈的反差,这便是《咏煤炭》:“凿开混沌得乌金,藏蓄阳和意最深。爝火燃回春浩浩,洪炉照破夜沉沉。鼎彝元赖天生力,铁石犹存去世后心。但愿苍生俱饱暖,不辞辛劳出山林。”“煤炭”这个意象在诗歌中很少涌现,于谦之以是歌咏它,是由于看中了它所独占的品质,它不仅能够带来“燃回春浩浩”的温暖,而且能够带来“照破夜沉沉”的光明。诗以言志,于谦所追求的便是为百姓苍生带来温暖和光明,其为民的情怀和深奥深厚的大爱是他生平勤政济世的原动力。从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到郑板桥的“些小吾曹州县吏,一枝一叶总关情”;从杜甫的“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到于谦的“但愿苍生俱饱暖,不辞辛劳出山林”,都充分解释心无百姓莫为“官”。
公元1430年(宣德五年),于谦擢为兵部右侍郎,巡抚河南、山西,从此在太行山脉度过了十数年的仕宦生涯。在此期间,他为了实践“苍生俱饱暖”的政治空想,在晋豫两省“不辞辛劳”地奔波。他刚刚上任,就“轻骑遍历所部,延访父老,察时势所宜兴革,即具疏言之”。为了把问题搞清楚,每每是“朝在太行南,暮在太行北”,乃至除夕之夜也忙于政务,“不是五更闻炮竹,那知今日是新年”。虽然离乡千里、政务繁忙,但于谦也是毫无怨言,“民安足遂中央愿,年壮何妨到处家”。作为地方官,于谦心系庶民,“贫者为宽征,饥者为发粟。善良加抚摸,豪强使慑服。闾里无横科,仓廪有馀谷”。此外,他还兴修水利,筑路铺道、植树挖井、贷粮济贫、施药救难,政绩卓著,境内大治。当地百姓感念于谦的恩德,直呼为“于龙图”,当地流传的歌谣中有“天遣恩官拯二方”之句,足见其民望之高。公元1446年(正统十一年),于谦被王振罗织罪名下狱,后虽获释,但由三品巡抚降为四品大理寺少卿。“山西、河南吏民伏阙上书,请留谦者以千数”,王振迫于压力只好让于谦官复原职。于谦在巡抚任上,心忧百姓、为民请命;当他蒙冤入狱,民众不惧压力为他声援,这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一幕动人的篇章。
“凛凛英风震百蛮,巍巍砥柱屹狂澜”
于谦在《和何知县交趾去世节韵》一诗中写道:“凛凛英风震百蛮,巍巍砥柱屹狂澜。自缘忠义存心正,不惜从容就去世难。”这“凛凛英风”的果敢刚毅,“巍巍砥柱”的无畏担当,正可以形容他在北京保卫战中的表现。公元1449年(正统十四年),蒙古瓦剌部的首领也先率军反攻袭击明朝边疆,王振鞭策英宗御驾亲征。于谦最初也在随军出征的名单中,但是他上书极力反对英宗亲征,结果王振一怒之下把他从名单中划掉了。这大概是王振生平中做得最精确的一件事,正是这一笔挽救了大明王朝的命运。“土木堡之变”中,英宗被俘,明朝精锐部队全军覆没,也先率50万大军乘胜而来,兵锋直指北京。传来,京师震撼,惶恐蔓延,乃至有官员发起将都城南迁至南京。国家真的到了危难存亡之际,而于谦便是力挽狂澜令金瓯无缺的国度栋梁。风雨飘摇中,于谦站出来了,他满怀悲愤地说:“言南迁者,可斩也!
京师天下根本,一动则大事去矣,独不见宋南渡事乎!
”众望所归,民气所向,于谦被任命为兵部尚书,全权卖力北京的防守以及对瓦剌的军事作战指挥。首先,他火速调动兵马保卫北京,包括“两京、河南备操军”“山东及南京沿海备倭军”以及“江北及北京诸府运粮军”,从而缓解兵力不敷的问题。然后,他联合众臣拥立郕王为帝,重修领导核心,摧毁了也先挟持英宗威逼大明的图谋。末了,他灵巧利用伏击战、阵地战、游击战等多种战术,取得了北京保卫战的胜利,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于将倾。
北京保卫战是于谦生平中的高光时候,个中最闪耀的光芒便是他的担当精神。在危难之际,调度兵马、重修领导核心、亲自指挥战斗,哪一步都充满风险,哪一步都容不得有闪失落,否则都是无法承受的代价。个中风险于谦岂能不知,但国难当头,惟有勠力向前,岂能明哲保身?在于谦的心中,国家民族、江山社稷、庶民百姓是最主要的,危难险重之际更要敢于任事、勇于担当。担当是一种信念和义务,而当面临死活决议的时候,担当又会化成一种无上的勇气和力量。这种精神在其诗歌中多有表示,如“孤臣不为一身惜,降将应怀万古羞”“等闲吸尽四海水,化作商霖拯旱乾”等都反应了他迎难而上、以身许国的抱负,浩然正气满盈天地。
关于于谦的诗品与人品,《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的一段评论则可谓全面而中肯:“谦遭逢恶运,独抱孤忠。忧国忘家,计安宗社。其大节炳垂竹帛,本不藉笔墨以传。然《集》所载奏疏,明白洞达,切中事机。较史传首尾完全,尤足觇其经世之略。至其诗风格遒上,兴象深远,虽志存开济,未尝于吟咏求工,而品质乃转出文士上,亦足见其才之无施不可矣。”于谦为人,品质高洁、肚量胸襟大爱、勇于担当;于谦为文,表里澄澈、风格遒劲、正气浩然,其人品与诗品交相照映,并垂不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