廉政瞭望
行到水穷处 坐看云起时
扫一扫看
更多文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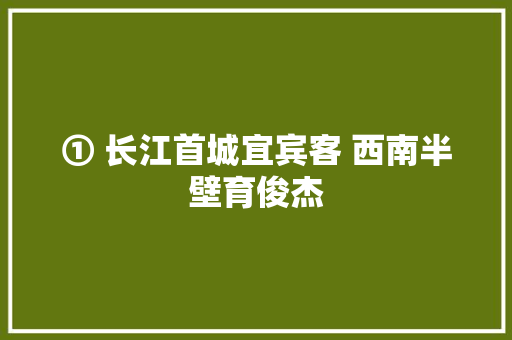
北宋元符二年(1098年)盛夏,长江上一叶扁舟载着54岁的黄庭坚垂垂前行。一代大墨客、书法家已过知命之年,身上落下一身病痛,当他沉浸在川南陌生而雄秀的山水中时,彷佛忘却了官宦生涯起伏的糟心,脸上是岁月刻下的笃定。
他的下一站是戎州(今宜宾)。5年前,宋哲宗修《神宗实录》,入朝任秘书省校书郎的黄庭坚参与。因年轻气盛,不识党争险恶,他秉笔直书,把宋神宗时期的朝政善恶皆加以记录,结果因“诬谤不实”而开罪,屡遭贬谪,颠沛流离。
就在此时,在戎州担当副职的行政主座苏时正忙着一件事——申请戎州改名的奏折,正从戎州向京城呈送。情由是,如今民族联络和蔼,车与中原同轨,书与中原同文,措辞教诲和中原相同,但州名还是叫“戎”,彷佛不太美观。
忙于搪塞西夏战事的宋廷哪有闲情顾及戎州改名之事,苏时的奏折一搁便是17年。直到政和四年(1114年),朝廷才以《尚书•禹贡》载有“西戎即叙”一句为依据,把西南方向的戎州改为叙州,作为州、县治所的僰道城也随之改为义宾县。又因避宋太宗赵光义“义”字之讳,取《中庸》“义者宜也”之意,义宾县更名为宜宾县。
金沙江、岷江在宜宾汇聚发展江,汉、僰、苗、彝多民族和蔼杂居,此地控滇黔,为通蜀的重镇,因而有 “西南半壁”之称。初到宜宾,当地的原谅之风令黄庭坚线人一新,毕竟出息茫然,他自称“寒灰槁木,不省世事”。而这片热土向他伸开了温暖的怀抱,遍山翠竹、涌流甘泉,打开了贰心灵的另一扇大门。
山石为骨,灵竹为肌
黄庭坚是盛极一时的江西诗派的开山鼻祖,在“苏门四学士”中,位列秦不雅观、晁补之、张耒之前,可谓首席。他笔走图画,行、草、楷自成一家,与苏轼、米芾和蔡襄并称“宋四家”。当时,黄庭坚已然是文化界红得发紫的人物。
一到宜宾,黄庭坚即享受超级网红报酬,王侯将相、文人士绅、贩夫走卒对其顶礼膜拜,争先求见。川南地区自古以来茶树成园,唐时便有“惟蜀茶南走百越”之说,“以茶榷马”繁荣了商业,物质丰腴的戎州人,更加觊觎文气昌盛。
州守彭道微的激情亲切令黄庭坚颇有感触,他给侄子黄朴写信说:“初到戎,彭道微作守,甚有亲亲之意。”宜宾民风淳厚,“亲亲之意”道尽了宜宾人的待客之道。
这里盛产荔枝,唐时已作为贡品。人们深爱其色彩之淡雅而富有诗味,便酿造出一种颜色与之近似的美酒,冠名“荔枝绿”。一次,黄庭坚到朋友家作客时,品尝到甘果与美酒,诗兴大发,赞道:“谁能同此胜绝味,唯有老杜东楼诗。”
原来,唐时杜甫从成都乘舟东下途经宜宾,受朋友约请在东楼宴饮时,写下了“重碧拈春酒,轻红擎荔枝”的佳句。这间隔300年的唱和,串联着宜宾的景致与文脉。
当时的戎州副州官黄斌老,是画竹大师文同的妻侄,他师从文同,善画墨竹。黄庭坚与黄斌老交往甚密,斌老画了一幅横竹送黄庭坚,黄庭坚作诗回赠:“中安三石使屈蟠,亦恐形全便飞去。”
心中不平,化为苍墨,吐出来画作青竹岁月峥嵘。画中安置的三块怪石使青竹屈蟠,却还是担心把竹子的形体画全了会化成竹龙凌空飞去。一句诗,精妙地概括了神乎其技的画功,也使戎州的竹、石文化跃然纸上。
经由千万年的江水磨砺,宜宾三江九河中的石头变得自然灵动,竹苞松茂,“墨玉”之“珙”曾贡朝庭;而竹的灵物,墨客绘其气质韵味,禅者诵其静而化神,平头百姓喜其造物代价。兴文石海以雄奇称绝,蜀南竹海以奇丽称美,山石为骨,灵竹为肌,构建了宜宾人耿直灵动的灵魂之骨。
彼时的黄庭坚,在奇石的沧桑纹理中,参透人间悲喜沧桑;在竹的客气直节处,寻觅到安身立命的淡泊。他对官场的不济命运愈加淡然,取别号“山谷道人”,钟情于诗书、禅学,游山玩水。
流杯池的流觞曲水,让无数文人骚客为之憧憬。
一天,黄庭坚与学儒名流游离至催科山下,见山谷有一天然裂痕,有涓涓溪水流淌谷中。于是,他效仿晋代王羲之《兰亭集序》中“流觞曲水”的意境,在此山谷建成了至今有名遐迩的流杯池。羽觞顺水而下,流到谁的跟前,作不出诗便罚酒一杯。
在黄庭坚的影响下,尚酒与文学联姻,戎州的饮酒风尚向雅、礼、诗方向发展,即崇尚文人雅集,浅斟慢酌,不再崇尚狂醉滥饮。
刚到戎州的彷徨不安消弭了,黄庭坚在黄斌老住的戎州东园里品尝苦笋,爱上这种微苦之物,并从中引申出智者的处世哲学:“盖上士不谈而喻;中士进则若信,退则眩焉;下士信耳而不信目,其顽不可镌。”
上等之人明道理,毋庸多言;中等之人当面虽相信,可过后又迷惑;下等之人专听谣传,如岩石不能雕刻与凿穿。如今,在流杯池公园中,常有游人在诗刻前容身、冥思,似有所得。
贤良育人,世族昌文
连接宜宾与南溪的S307省道,依长江顺势铺沿。江边翠竹遮天蔽日,江面开阔大气,来往的船只仿佛凿穿了光阴,那船头矗立的人儿,是苏轼、黄庭坚……他们在这里留下诗文遗迹和亘古不变的人文踪迹。
黄庭坚寻觅着苏轼的足迹,与此时远在海南的恩师达成了精神对接。山水林泉秉赋了文人雅士拂拭心灵的机会和园地,他们又反哺着宜宾的文运。自宋以来,后人在流杯池周围相继建筑了涪翁楼、涪翁亭、山谷祠、吊黄楼等,形成现在的流杯池公园,“曲水流觞”更是成为宜宾“古八景”之一,为历代文人雅士酬唱之所。
黄庭坚在宜宾三年,“蜀士慕从之游,讲学不倦,几经指授,下笔皆可不雅观”(《宋史》)。受其熏陶最深的任渊,“尝以文类试有司,为四川第一”。宜宾地区的文昌,正是起始于北宋。至南宋嘉定四年(1211年),叙州宣化县(县治在今叙州区蕨溪镇)程公说、程公硕、程公许三兄弟俱登进士第,三川震撼。
明代时,宜宾有52人中进士,居全川第三。文教兴盛,尔后孕育诗书世家。在S307省道旁的南溪街道九龙村落东南方向400米旁边,名为“包宽牌坊”悄悄矗立,牌坊上的青狮、白象抱鼓石虽有毁坏,但“指顾散千金,耻登游侠朱陈传;头衔宗两汉,不数文章甲乙科”的楹联,仍不惧光阴摧残。
道光三年(1823年),因好扶植寒士,襄助义举,包宽被举为“孝廉方正”,送部引见,不幸在途中逝世。当地老百姓向朝廷请愿,把其业绩上报,将包宽列入乡贤祠受祀。
其子包融芳,从小随着父亲学习书法诗词,热心义举。包融芳之子包弼臣的成绩青出于蓝而胜于蓝,20岁所作辞赋名已经在宜宾流传。四川学政何绍基按试叙州府,对其诗文字画大为赏识,称他与嘉定府教授罗肃、宜宾进士赵树吉为“叙州三杰”。
25岁时,包弼臣随叔父赴京深造,得礼部侍郎李文田赏识,后者拿出名书法家阮元的《南贴北碑论》和包世臣的《艺舟双辑》给包弼臣阅读。包弼臣暗思创派、立格,苦练书法,30岁出头便一反传统推崇的“馆阁体”、取石本之长创“包体”。
“竖子下笔如此狂乱,不遵古道师训!
”墨守成规的老师一看,不得了,赶紧把字拿给慈禧看,慈禧给了他“字妖”的称号。顶着“字妖”的骂名,包弼臣愤而作诗“白眼可遭,精不可销”,将不拘泥传统的创新精神贯彻到底。百年后的本日,“包体”已然成为研究、借鉴的工具。曾经的“不合时宜”,见证了宜宾人的敢为人先。
包世家族留给宜宾的文化遗产是德与艺,江安县的夕佳山民居、屏山县的龙氏山庄,同样见证了家族在教养民风民俗的功绩。锡氏、龙氏世家大族,聚财富、人脉、名望于一身,或礼贤下士、热心公益,或诗书传家、以文载道,为润养一方水土的安宁与文昌,发挥着隐秘而持久的文化力量。
寻根苦难,铸梦未来
从某种程度来说,宜宾的“宜人”“宜宾”,跟其名字一样来之不易。滔滔江水边的品茶人、真武山上的徒步者,对面前的繁荣平和,彷佛都怀有敬畏感。在与当地人互换中,敬畏的来源逐渐显现,那便是苦难。
南广河上游的珙县以南50 多公里处,有一个名叫麻塘坝的地方,这里峭壁绝壁吊颈挂着许多棺材。先秦期间,僰人便在此地繁衍生息。他们骁勇善战,各周围民族相处融洽,但历朝统治者却大多认为其“叛服无常”,因此常被排挤和弹压。
明代崇祯十一年(1638年),宜宾同时兴建了“百二河山坊”“江城锁钥”“双龙飞控”等石牌坊,个中“百二河山坊”寓意宜宾城有二万年夜军就可借古城防御工事,抵挡百万敌军。这样的希冀,是对和平生活的神往。
一名宜宾的文化人谈到僰人消亡的历史,仍心有戚戚焉。他说,三国期间,宜宾地区的各民族为了守卫生存资源,便已戎马倥偬。宜宾人在浩瀚的历史中学会了抵御苦难,并从中汲取灵感、力量和聪慧。
中国新文化运动先驱者之一、高县人阳翰笙,在《生之哀歌》等文学作品中,描述了三个青年在阴郁社会的生活经历,两个丧子失落业,一个断腕流浪;儒学大师唐君毅同在《人生之体验》中感叹“人生之路,步步难”,并哲学性地提出了对生命的希望,“须把自然生命之流之浩浩狂澜翻到底”。
刻画苦难,终极指向对人类的大悲悯情怀,是宜宾人从未间断的文化血脉。黄庭坚尝苦竹而悟大道、兴文凌霄城抗元故事、李庄人扛起抗战大旗,人生的味道、生命的意义,宜宾人有着深刻独到的理解。
古代宜宾雄秀的山河给苏轼留下深刻印象。
嘉祐四年(1059年)初冬,苏轼带着一大家子游历戎州。他与弟弟苏辙见此地山脉迂回,树木蓊郁,诗兴大发,同体作诗《戎州》。面对战乱历史,两兄弟都抒发出反战的人文情怀。苏轼说“何足争强弱,吾民尽玉颜”——都是和颜悦色之人,何必争出个大小强弱呢?
古代宜宾雄秀的山河给苏轼留下深刻印象,离开宜宾后,他又作诗《见夷中乱山》:“秾秀安可适……谁能从之游,路有豺虎迹。”他感叹戎州地是块宝地,但沿路有虎豹豺狼踪迹,谁敢去山里游览啊。
假如苏轼穿越到本日的宜宾,要做的第一件事,恐怕便是改改当年那句诗吧——他一定会被面前横贯的高速公路、高铁线路与鳞次栉比的高楼震荡。如今,鼎鼎西南半壁,巍巍水陆码头,正以新的姿态创一方热土的祥和、繁荣。
审核 / 邓苗苗
视觉 / 瓷明晰
© 廉政瞭望原创内容 转载请联系后台
下滑到留言区 揭橥你的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