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正文之前,为了帮助读者先在观点上有一个基本的诗体框架,请读一下旅旭在其《韵海浪花》(2017年版,p117)一书中的一段话:“关于格律诗,有人称其为旧体诗或旧诗,实在是不对的,至少是不科学、不严谨的。五四新诗之前的诗词歌赋统称为旧体诗,也便是我们平时所说的古典诗词。旧体诗包括古体诗和近体诗,古体诗也称古风,其特点是:除了押韵外,格律自由,不拘字数,不遵平仄,不讲对仗。唐代之前的诗称为古体诗;唐代及之后的诗称为近体诗或今体诗,近体诗是诗歌主流,当然仍有不少唐宋墨客乐意写不讲格律的古体诗,如李白、王维等。请把稳,“近体诗”是沿袭唐宋人对诗的说法,便是本日我们所称的格律诗。格律诗之以是高雅,被誉为“艺术皇冠上的明珠”,就因格律诗的笔墨精髓精辟、词华幽美、格律严谨、对仗工致、音韵和谐、节奏光鲜,读之琅琅上口,诵之声韵萦耳,思之其妙无穷。”
本文不是大略的、概括性的诗体辨析,而是在辨析中融入了干系知识和辨析方法。全文一万余字,分上、下半两部分揭橥。朋友们读后,如果能说:不错,有所收成。我们就知足了,感激了。
一、诗与诗歌
首先先容一下诗与诗歌的关系。为什么我们常日把“诗”称作“诗歌”呢?这个称谓又是若何来的呢?实在“诗”和“歌”原来就不是一个可以结合在一起的东西,所谓“歌”是先民在劳动过程中情不自禁发出的感叹声,如嘿、啊、嗨、唉、兮等,这些感叹词的产生远在笔墨形成之前,当然比诗更早得多。笔墨涌现之后,逐步形成了文学,用笔墨书写的词配上大略的音乐,就成为一首歌。最初的诗也配上音乐吟唱,由此诗与歌这两个不同的观点就结合起来,以至于更多的时候人们将诗称之为诗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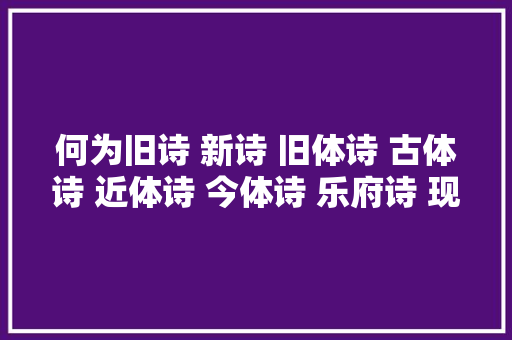
朱光潜认为:“诗歌与音乐、舞蹈是同源的,而且在最初是一种三位一体的稠浊艺术” 。 (《朱光潜美学文集(第二卷)》 1982年版,p171)诗歌是最精髓精辟的措辞形式,是一种歌咏的措辞艺术。无歌不成诗,有诗就有歌;诗歌的这种内涵,充分地表示了其音乐性。唐诗作为中国诗歌壮盛期间的文学形式,节奏铿锵,音韵悦耳,读来琅琅上口,给人以巨大的听觉享受。
卞之琳光鲜指出,诗完备属于“听觉的艺术” 我国古人对“吟诗”极其重视,“新诗改罢自长吟(杜甫)”、“吟安一个字,捻断数茎须(卢延让《苦吟诗》)”、“二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贾岛《题诗后》)”之论,无一不证明吟诵是诗歌音乐美得以实现的必不可少的手段;离开了吟诵,诗歌格律就失落去了存在的根本,当然也就失落去了美感和活气。从公元前11世纪至前6世纪的《诗经》一贯到五四新时期文学,中国的诗词歌赋始终秉承着其音乐性、歌咏性特色。
二、古体诗与近体诗的差异
(一)从《中国诗词大会》提及
自2013年河北卫视《中华好诗词》和2016年央视《中国诗词大会》开播以来,掀起了全民学习、诵读、创作古诗词的热潮,唤起了人们内心深层对中国古典诗词的热爱和对精良传统文化的认同感。在《中国诗词大会》第一季后,《中国青年报》评论道:“《中国诗词大会》以经典诗词为切入点,从诗经楚辞、唐诗宋词到近当代诗词、伟人(注:变通一下,读者会明白的)诗词,与不雅观众共享诗词之美、感想熏染诗词之趣、传承文化基因。”
这里所称的“古典诗词”,指的是唐代前后的旧体诗和宋代的词;“近当代诗词”指的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及之后的新诗(也称当代诗或自由诗);“伟人诗词”是旧体诗中的近体诗(格律诗)。
《中国诗词大会》的点讲高朋康震、郦波、王立群、蒙曼、杨雨五位教授饱览群书,博闻强记,文学功底深厚,他们对诗词的讲解独到而精妙,集知识性、思想性、意见意义性于一体,深受广大不雅观众的欢迎和好评。但是当康震和郦波教授在2017年诗词大会第二季末了一场决赛结束前朗读了各自创作的诗后,却涌现了不同的声音。在决赛现场康震教授声情并茂地朗诵了自己的诗作(因篇幅关系,略去郦波教授的诗作)。
大江东去流日月,
古韵新妍竞芳菲。
雄鸡高歌天地广。
一代风骚唱春晖。
对此,人们的评价比较中肯和尖锐。比如:
苏子聊斋在其微博(2017/02/09)中说:“康教授这首绝句平仄有误,粘对有失落,语句不通,诗味全无。与他之前在屏幕上朗诵点评的幽美诗词比较,真是寰宇之别。”
层城鵷雏(文化问答达人、文化领域创作者)在《今日头条》(2017/07/06)上说:“他们既不理解诗词的基本知识,也不懂诗词的创作技巧,他们只会在诗词的意境方面深挖,讲述诗词如何好、如何妙。”
韩军在线(2017/02/10)转自王永江在《对联中国》的评论:“这首所谓的诗当然也赢得满场的掌声。但是掌声过后,我们再来看,却不得不嗟叹。首先来看一下康教授的履历:康震,男,1970年3月生。现为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北京师范大学党委办公室、校长办公室主任。曾多次作为《百家讲坛》主讲人,开讲李白、杜甫、苏轼、李清照等而得到好评。从这种履历来看,康师长西席基本可以说是中国文学界国学领域的精英人物了。但是就这么一位精英人物写的诗却是一首格律不通、意思干枯的蹩脚作品。”
“上面那首诗,从形式上看该当是七绝,但是除了押韵以外,却完备不符合唐诗的基本格律。我们也听过这句话:平平仄仄平平仄,仄仄平平仄仄平(估计很多人听过这句话还是在台湾组合SHE的歌曲《中国话》里听到的吧)。实在这两句便是唐诗句子的基本平仄格律规则,平仄两两相间。而看康教授的诗,其平仄没有一句是对的。非但如此,如果按照他的开始两个字的平仄来看整首诗的格律,该当是平平仄仄平平仄,仄仄平平仄仄平。仄仄平平平仄仄,平平仄仄仄平平。可以说,整首诗的平仄也是完备不搭调的。”
“撤除形式,看内容。这首诗的立意以及措辞,基本上可以说是十分苍白和干枯的,短缺诗词该当有的内蕴和韵味,读起来基本可以说是“老干体”(不懂这个词儿可以百度)。”
南宫寻欢(优质文化领域创作者)在《今日头条》(2017/08/11)上说:“康震师长西席诗兴大发,写了一首小诗,献给诗词大会和电视机前的不雅观众。我大致看了下平仄格律,最最少有五处缺点。郦波师长西席也朗诵了自己的小诗,作为七言绝句,有三处出律,如第三句,‘非吾有’的‘吾’应为仄声;第二、四句扫尾的‘喷鼻香’和‘乡’撞韵(不是撞韵,而是连韵,即,相邻的两个押韵句的韵脚用了同音字作韵字——作者注)这些都是绝句的大忌。”
还有更尖锐刺耳的评论,如“就目前所见,此二位的诗词水平属州里级,我们县里的一些诗词爱好者都比他们强。”
为什么在网上竟是险些一边倒地给予两位教授不认可的评论呢?这是由于全国广大诗词爱好者的诗词知识、创作技巧普遍提高了,他们鉴赏诗词的水平也提高了,他们希望他们喜好的文学教授所写的诗该当是文辞精髓精辟、格律严谨、对仗工致、音韵和谐、意境幽美。
据统计,2017年央视播出的10期《中国诗词大会》累计收看不雅观众达到 11.63 亿人次。自此,数以亿计的爱好者把诗词作为一种修身养性的办法和精神寄托。十年来,凡有盛大之事皆有全国性或国际性的诗词大赛,引人关注和积极参与;每一次比赛都征集到数十万件作品,个中佳作迭出。目前刊发诗词作品的不仅是全国浩瀚的纸质媒体、上百种的纸质诗词刊物和上千种的电子诗词刊物,更是大大小小、不计其数的诗词网站。而诗词刊物在投稿哀求上均注明所投作品必须遵守格律,也便是说必须是近体诗(格律诗),不是古体诗。
以是说,在普通的诗词爱好者的心目中,写诗便是写格律诗,而不是不守平仄、不遵格律的古体诗。当他们看到两位讲解诗词的高手却写不出一首像样的格律诗时,批评之声也就自然而然地涌现了。
所谓“平仄”,指的是字的音调,平声和仄声。当代汉语有“四声”,即一声(阳平)、二声(阴平)、三声(上声)、四声(去声);平声包括一声和二声,仄声包括三声和四声。中古汉语的“四声”是平声、上声、去声、入声,除了平声,别的三种统称为仄声。当代汉语和古代汉语在“四声”上有着较大的不同。诗或词有了平仄,诗句就产生了光鲜的节奏,读起来抑扬抑扬,给人以美感。
我们的不雅观点是:
康震、郦波两位教授,对付诗词,很明显侧重于研究,研究并不是创作。谈诗与写诗不是一回事。谈得好,未必写得好。王国维的《人间词话》论诗谈词很有见地,是诗词界的经典著作。他写的诗词自视很高,但反响平平。这是其一。其二,作为文学教授,尤其是作为全国最高层次的遍及诗词节目的点讲高朋,该当客气接管建媾和批评,重视诗词格律,写出高水平的近体诗,以飨广大诗词爱好者和读者。其三,一些评论显然是爱之殷,责之切,我们不妨换个角度不雅观察,不把二位的诗作看作是近体诗,而是古体诗,这又何妨?
(二)从五个方面看古体诗与近体诗的差异
清楚地辨别古体诗与近体诗这两种诗体,理解两者的特点以及干系知识,对付诗词鉴赏和创作具有主要的意义。可以从如下五个方面做一辨析:
1、字数
古体诗不拘字数,包括二言诗( 清 许印芳“秋鸿,毛丰。长安,顺风。洞庭,月明。弹筝,吹笙。”;网络墨客戴丹 “心喧,难卧,无眠,静坐,莫言,独我。”)、三言诗(颜真卿 “喜嘉客,辟前轩。天月净,水云昏。”;网络墨客查红胜“烛影寒,感伤瞒。琴声沸,苦涩酸。”)、四言诗(《诗经》,如“关关雎鸠,在河之洲。”;曹操《不雅观沧海》“东临碣石,以不雅观沧海。”)、五言诗、六言诗(王维“桃红复含宿雨,柳绿更带朝烟。花落家童未扫,莺啼山客犹眠。”)、七言诗、八言诗(历史上八言诗极少,网络墨客查红胜“尽欢年末碎撕残梦,心有念牵寒风莫恸。冬雪瑞丰他岁务农,喜撩斑鬓颤声催送。”)、九言诗(南朝宋谢庄“百川如镜天地爽且明,云冲气举德盛在素精。木叶初下洞庭始扬波,夜光彻地翻霜照悬河。庶类收成岁功行欲宁,浃地奉渥罄宇承秋灵。”)、多言诗、杂言诗(佚名“上邪,我欲与君相知,长命无绝衰。山无陵,江水为竭。冬雷震震,夏雨雪。天地合,乃敢与君绝。;李白《蜀道难》,“噫吁嚱,危乎高哉!
蜀道之难,难于上上苍!
”)
五言、七言在唐代之前是诗歌的主流,五言称为五言古风,简称五古;七言称为七言古风,简称七古。
近体诗利用五言和七言。五言、七言是唐代及之后诗歌的主流。五言的称五言绝句,简称五绝,五绝是每句五个字,每首四句,共计二十个字;七言的称七言绝句,简称七绝,七绝是每句七个字,每首四句,共计二十八个字。
2、句数
古体诗不拘句数,几十句乃至上百句的古体诗也有。
近体诗限定句数,绝句统共四句,分五言绝句和七言绝句;律诗统共八句,分五言律诗和七言律诗;超过八句称为排律或长律。在五律和七律中,每两句成一联,共四联,习气上称第一联为首联,第二联为颔联,第三联为颈联,第四联为尾联。每一联的上句称为出句(或起句),下句为对句(或承句)。
3、格律
古体诗除了用韵外,没有平仄、粘对、对仗的哀求。但是近体诗,除了用韵外,还哀求平仄;五律和七律的中间两联还哀求对仗(名词对名词,动词对动词,形容词对形容词,副词对副词,数词对数词,介词对介词),一联内的出句和对句平仄相对,两联间要粘连,“粘连”即下联的出句与上联的对句平仄同等。
4、用韵
古体诗,用韵方面没限定,可押平声韵、也可押仄声韵(比如孟浩然的《春晓》: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晓”、“鸟”、“少”都是押的仄声),并且中途可以换韵。
近体诗,用韵方面有限定,只能押平声韵,不能押仄声韵,中间不可换韵,必须一韵押到底。在近体诗中,押韵只能押偶数句,首句可押可不押,也便是在绝句中,第二、四句押韵;在律诗中,第二、四、六、八句押韵,第三、五、七句是“白脚”不押韵,否则便是“押韵八忌”之一的“撞韵”。
5、朝代
唐代以前的那些诗都是古体诗,唐代往后的诗绝大部分是近体诗。但唐代有不少墨客钟情于古体诗,除了写一些近体诗外,大部分诗还是古体诗,比如诗仙李白的诗大部分是古体诗。
为了对上面五点有个明晰而直不雅观的理解,下面仅以伟人的一首七律《送瘟神》为例,大略示范一下其格律的利用。
东风杨柳万千条,
六亿神州尽舜尧。
红雨随心翻作浪,
青山着意化为桥。
天连五岭银锄落,
地动三河铁臂摇。
借问瘟君欲何往,
纸船明烛照天烧。
看图片,《送瘟神》这首七律用的是平水韵,其平仄、粘对、对仗、押韵是非常严谨规范的。由此可见伟人的诗词成绩之深厚。
在近体诗的平仄上,出句和对句中的每个字都哀求平仄相对,当然也有“一三五不论,二四六分明(一三五不管,二四六必须)”的说法或基本原则。详细说来,便是五言各句的第二、四字,七言各句的第二、四、六字都处在节奏点上,因此平仄是严格的、光鲜的;但五言各句的第一、三字,七言各句的第一、三、五、七字在有的情形下是可以变动的、无关紧要的。
对付《送瘟神》这首律诗,我们试做简析。以首联为例,处在出句二、四、六位置上的“风”、“柳”、“千”与处在对句二、四、六位置上的“亿”、“周”、“舜”在平仄上是相对的(平仄平与仄平仄相对立)。在两联之间的粘连上,处在首联对句二、四、六位置上的“亿”、“周”、“舜”与处在颌联出句二、四、六位置上的“雨”、“心”、“作”在平仄上是同等的(仄平仄与仄平仄相同等)。再看对仗,颌联和颈联的对仗工致精妙,颌联中的“青山”对“红雨”、“着意”对“随心”、“化为”对“翻作”、“桥”对“浪”,颈联中的“地动”对“天连”、“三河”对“五岭”、“铁臂”对“银锄”、“摇”对“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