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
诗写得很牛,听说曾让李白搁笔。此诗问世前,黄鹤楼是一座赛诗楼,无数名家都留下了墨宝;此诗问世后,敢在黄鹤楼题诗的人少了许多。而崔颢这首诗,也成为千年来极少有人敢仿的七律。直到1933年,鲁迅一气之下仿写了一首。
众所周知,鲁迅的脾气是不小的,气头上写的诗文也不少。当年被传得了脑炎,一气之下,写了首《报载患脑炎戏作》,令人拍桌赞叹。这一次,他生气不是为自己,而是为北平的万千学生们。
1932年,东北被占,华北岌岌可危,当局准备撤出北平。北平的大量文物被分批运往南京等地。这种情形之下,他们却不让大学生逃难。这种只重文物不重人的做法,让鲁迅十分愤怒,鲁迅写下这首七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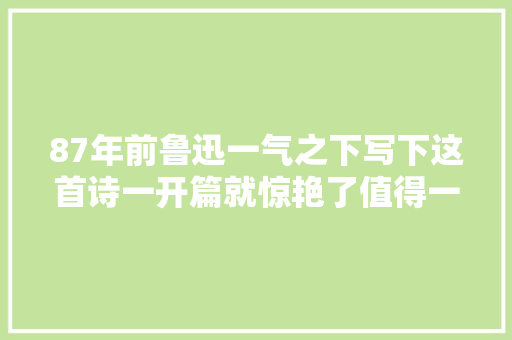
《剥崔颢黄鹤楼诗吊大学生》
[近代] 鲁迅
阔人已骑文化去,此地空余文化城。
文化一去不复返,古城千载生僻清。
专车队队前门站,不利重重大学生。
日薄榆关何处抗,烟花场上没人惊。
诗的第一联开篇就惊艳了。“阔人”指的是当局的官员们,他们带走了文物,不正是“骑文化” 而去了吗?一个“骑”字,充满了讽刺意味。他们走了,北平也就成了空空如也的“文化城”了。
七律的次联,一贯是最磨练文人笔力的。鲁迅这一联不但工致,而且末了“生僻清”三个字,也颇有杜甫《登高》中“不仅长江滚滚来”的意蕴。这前四句都在模拟崔颢的《黄鹤楼》,却仿出了新的高度,令人面前一亮。
颈联“专车队队前门站”,写得是专列在前门火车站运送文物的繁忙景象,彷佛让我们看到了一群准备逃跑的“王侯将相”们忙乱的丑态。可是他们却敕令不准求学的年轻人逃难,彷佛和这些冰冷的文物比较,北平求学的年轻人,倒反而成了“不利重重”的人。
尾联用“日薄榆关”对“烟花场上”,对仗工致,一语双关,可谓讽刺之锋芒,几欲倾圯字面。所谓“日薄榆关”,既是仿“日暮乡关”,写夕阳西下,照在榆关。而更深层次的意思,则是说侵略者都打到面前了。所谓“烟花场上”,仿的是“烟波江上”,明写王侯将相的醉生梦去世的欢场,暗写战役的硝烟,在这些王侯将相看来,不过便是楼头的烟花。
全诗的末了三个字,犹如一把匕首,“不用惊”,将讽刺的利刃,直插作歹者的胸膛。对付那些只在乎文物的王侯将相,实在哪里是关心什么文化,不过是由于这些东西随时可以变卖成金钱罢了。他们对付面前的侵略者,对付苦难中的大众,对付空空荡荡的北平城,都根本“不用惊”。
鲁迅这首诗,本日读来依旧有一种雄浑的气势和傲岸的凛然正义之气,值得一读再读。这样的诗,这样的鲁迅,令人惊叹,师长西席不愧是“民族的脊梁”。师长西席这诗,大家以为如何?欢迎谈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