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
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
这首诗千年以来,凡是喜好中国诗词的人,全都能够吟诵,难怪章太炎把这首诗称之为“绝句之最”。可惜的是,王之涣墓和他的故居我都查不到任何信息,要纪念这位大墨客,只能去探访因他的这首诗而名扬天下的鹳雀楼了。
鹳雀楼景区入口处的广场足够宽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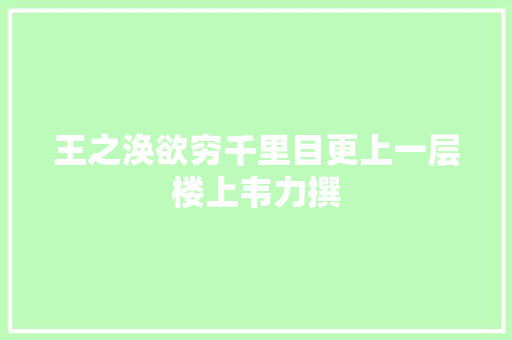
这种建筑风格听说是仿唐
鹳雀楼位于山西省运城市永济市郊黄河岸边。运城的张总安排司机把我送到了这里,而今的鹳雀楼已变成了一个巨大的景区,门票60元。现场购票之人,当时仅我一位,这跟整排的售票厅形成了很大的反差。司机抢着去买票,然而他却只买了一张,他说自己不想进内。我以为他是开车开累了,趁我游览的工夫可以打个盹儿,于是我孤零零地走进了这鹳雀楼景区之内。
进门之后还有着很长的路
烈日曝晒下的广场没有一丝的遮挡
本以为鹳雀楼便是黄河边的一个楼阁,没想到其面积之大远超我的想象,我觉得占地有几百亩。从进门走到楼下,至少有三、四百米的路程,从这个巨大的广场走过,看不到任何的植物,哪怕是一棵小草。虽然是早春,今日的气温还是达到了33℃,走在这无遮无拦的广场之上,觉得被太阳晒得有些头昏。
巍峨
步步高升
新的鹳雀楼建得很是高大,可以跟新建的滕王阁相颉颃,门口挂着一些铭牌,个中一个上面写着“中国名楼副会长单位”,我猜不出“会长”应该是哪个楼,不知道会不会是滕王阁。中国的四大名楼除了这两座之外,还有岳阳楼和黄鹤楼,而今来到了鹳雀楼,这四大名楼我算是跑遍了。在这四大之中,三座叫“楼”,只有滕王叫“阁”,由它来当会长,至少从名称上有点儿不得当,那该当让谁来当呢?我以为自己有点儿咸吃萝卜淡操心。
不知哪座楼能当“会长”
画栋雕梁
《集异记》上称有四位歌伎,然而这个画面上彷佛多了几位
进入楼内,一层是巨大的殿堂,殿堂的正前方以全景加雕塑相结合的办法展示着,听说是古代的楼景四围的原貌,两边的侧墙上绘制着跟鹳雀楼有关的故事,个中一段名曰“旗亭画壁”。这个故事太有名了,原来记载于唐薛用弱所撰的《集异记》,好在本文不长,我将其全文抄录如下:
开元中,墨客王昌龄、高适、王之涣齐名,时风尘未偶,而游处略同。
一日,天寒微雪。三墨客共诣旗亭,贳酒小饮。忽有戏班伶官十数人登楼会宴。三墨客因避席隈映,拥炉火以不雅观焉。俄有妙妓四辈,寻续而至,奢华艳曳,都冶颇极。旋则奏乐,皆当时之名部也。昌龄等私相约曰:“我辈各擅诗名,不自定其甲乙,今者可以密不雅观诸伶所讴,若诗入歌词之多者,则为优矣。”
俄而一伶,拊节而唱曰:“寒雨连江夜入吴,平明送客楚山孤。洛阳亲友如相问,一片冰心在玉壶。”昌龄则引手画壁曰:“一绝句。”寻又一伶讴之曰:“开箧泪沾臆,见君前日书。夜台何寂寞,犹是子云居。”适则引手画壁曰:“一绝句。”寻又一伶讴之曰:“奉帚平明金殿开,强将团扇共徘徊。玉颜不及寒鸦色,犹带昭阳日影来。”昌龄则又引手画壁曰:“二绝句。”之涣自以得名已久,因谓诸人曰:“此辈皆潦倒乐官,所唱皆下里巴人之词耳,岂阳春白雪之曲,俗物敢近哉?”因指诸妓之中最佳者曰:“待此子所唱,如非我诗,吾即终生不敢与子争衡矣。倘是吾诗,子等当须列拜床下,奉吾为师。”因欢笑而俟之。须臾,次至双鬓发声,则曰:“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羌笛何须怨杨柳,东风不度玉门关。”之涣即揶揄二子曰:“田舍奴,我岂妄哉!
”因大谐笑。
诸伶不喻其故,皆起诣曰:“不知诸郎君何此欢噱?”昌龄等因话其事。诸伶竞拜曰:“俗眼不识神仙!
求和清重,俯就筵席。”三子从之,饮醉竟日。
这里提到了李瀚
“旗亭画壁”故事先容牌
这个故事讲的是,在唐初的某一天,王之涣、王昌龄、高适三人在一起聚会,他们到旗亭饮酒,巧遇戏班名部在此唱曲,个中的四位歌伎长得很俊秀,这让三人来了兴头,于是王昌龄发起说:“我们三人都善于作诗,却未决牝牡,本日伶官唱谁的曲多,谁就为最佳。”二人赞许王昌龄的发起,结果前面所唱的几都城不是王之涣所写,这让他有些沮丧。他说这些歌伎怎么就不会唱点儿阳春白雪的歌,于是他就用手指着歌伎中最俊秀的一位跟两位朋友说:“如果她的所唱,还不是我的诗,那我一辈子也不敢跟你们比诗了;如果假如的话,你们要当场拜我为师。”果真,这位俊秀的歌伎所唱的正是王之涣的《凉州词》。这个结果让王之涣大感愉快,于是三人饮酒直到大醉。
登高下望
沿着楼梯上到了楼顶,觉得到新建的鹳雀楼高度超过了百米,站在楼高下望,体味着“黄河入海流”的真切,远处的黄河水缓慢地流淌着,顺着水流向黄河的尽头望去,当然,看不到海,但却看到了这条长龙划过天涯线所显现的朦胧。这种朦胧感让我的心态溘然分开了尘世,瞬间觉得自己回到了千年之前的古代,乃至听闻到了这三位大墨客在旗亭之内饮酒唱歌的繁盛热闹繁荣声,不知面前的黄河是否曾经看到那场欢快的酒会,它的无语东流让我无法理解这种沉默代表了若何的代价不雅观。
《旗亭记》二卷,清乾隆二十四年卢氏雅雨堂刻本,书牌
《旗亭记》二卷,清乾隆二十四年卢氏雅雨堂刻本,卷首
至少我以为《旗亭记》有着一定的历史事实,由于这是唐朝的故事,而作者薛用弱也是唐代的人。更为主要者,薛用弱便是河东人,而河东即本日的山东永济这一带。既然有这么多的附近点,那么这《旗亭记》总不会是空穴来风。更何况,王之涣的资料太少了,如果连这个故事都是假的,我真不知道将如何写这位大墨客。
可惜的是,他的这首千古传唱的《登鹳雀楼》,竟然有人否定王之涣拥有著作权。这个说法出自《国秀集》,此书是唐人所选的唐诗选集,书中称《登鹳雀楼》的真正作者名叫朱彬。但这种说法的依据,《国秀集》中却没有点明。如果连这一点都否定掉,这让我情何以堪?好在这种说法还没有成为业界的共识,而《旗亭记》的故事则因金兆燕改编成了《旗亭记传奇》,而使得家喻户晓。
金兆燕是清乾隆时的进士,曾做过国子监博士。在京期间,他还参与《四库全书》的校正,后因病辞官,就来到了扬州。不知他为什么喜好《集异记》中的这个故事。金兆燕以此为原本,同时又从很多文籍中搜集一些业绩,编成了这三十六出的《旗亭记传奇》。写完之后,金兆燕想将此出版,可能是没钱,于是他找到了扬州有权有势的卢见曾。卢看了金的改编,很感兴趣,答应给金出版。而后就以卢见曾雅雨堂的名义将《旗亭记传奇》于乾隆二十四年刊刻了出来。
《旗亭记》二卷,清乾隆二十四年卢氏雅雨堂刻本,卢见曾媒介
为此,金兆燕请卢见曾写了篇媒介,并刻在了本书的前面。卢在此序中讲到了金兆燕对付此书的付出:“全椒兰皋生,矜尚风雅,假馆真州,问诗于余。分韵之余,论及唐《集异记》‘旗亭画壁’一事,谓古今来贞奇侠烈,逸于正史而收之说部者,不一而足,类皆谱入传奇。双鬟,信可儿,能令吾党生色,被之管弦,当不失落雅奏。而惜乎元明以来词人,均未之及也。兰皋唯唯去。经年复游于扬,出所为《旗亭记》全本于箧中。余爱其词之清隽,而病其头绪之繁,按以宫商,亦有未尽协者。乃款之于西园,与共商略。又引戏班老西席为点板场面,稍变易其机轴,俾兼宜于俗雅。间出醉笔,挥洒胸臆。虽素不谙工尺,而意到笔随,自然合拍,亦有不自解其故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