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野外阅读,期待了良久,野外,采风,行走,这些浪漫的词,给过我很多想象。终于成行,实际觉得却五味杂陈,时而昂奋,时而消沉。原操持三个月,起初嫌短,后来嫌长。
没什么可抱怨,酒店和交通都很方便,只是要花不少钱。安居在家,吃住行按既定程序自动运作,出门在外却凡事都得安排,都是磨练,每天忍受吃住的不适,虽然这也是离开舒适区的题中应有之义。
走在路上,多少有点堂吉诃德式的悲情与凄惶,出身《诗经》的时期早已过去,如同一个孩子已经终年夜,你可以怀念童年,但再也回不到童年。
雪夜访戴的故事,重点不是连夜乘小舟就之,而是兴尽而返何必见戴。来和去,坚持和放弃,同样是自由的选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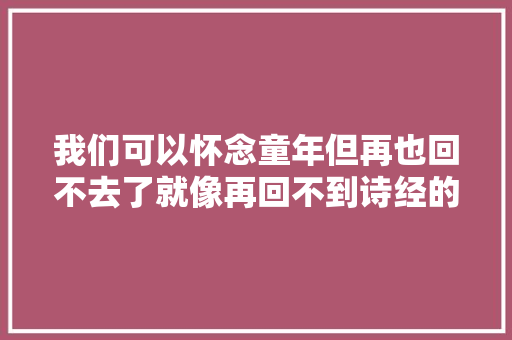
撰文 | 三书
5月12日
曲沃,几幕场景
曲沃,我喜好这名字,于是来到这里。
酒店附近的街巷,脏得兵荒马乱,走在人行道上,根本觉得不到有树,也觉得不到人行道,由于到处摆摊。一位七旬老妪在街边卖布鞋,黑平绒布鞋,小孩穿的虎头鞋,红绿喜气,所有鞋底都是针针线线纳出来的。我选了一双,老妪递鞋给我时,看着我的眼睛说:“我像是在哪儿见过你。”我理解这种觉得,但看她并不面熟,她却喃喃道:“是见过,在哪儿见过呢?”说着,她竟落下眼泪,仍痴痴地望着我,像是在努力回忆起。
县城外有些农田,都种大棚菜,弘大的白塑料棚,一排排像工业区,路边渠里淌着的水散发出有毒的气味,渠边密密麻麻都是扔掉的黑塑料套袋,看大小应是套过西红柿什么的。一位老农拿瓢往桶里舀水,舀满了两桶,然后挑去浇菜,全体过程面无表情,那种面无表情的表情,像是心如去世灰之后的沉着。
大棚菜地那边是一条公路,新修不久,一个男人骑马过来,马蹄踏在水泥路上嘚嘚响,男人三十多岁,穿藏青短袖黑西裤,皮鞋踩着马镫,手里牵着缰绳,他大声喊着“驾、驾”,黑马疾趋但没有跑起来。我站在路这边看,马经由我时,那男人看了我一眼,十几米外他转头又看我,我当然是看他骑马,但他看什么,我不知道。
往山那边是一条煤渣路,路旁两行白杨,飘尽柳絮飘杨絮,白蒙蒙乱扑人面。半路有几间房屋一个院子,院门上榜着“茶苑”,门外树荫下站着一位大爷,我上前问路,大爷说他在这里看大门,并见告这一带原来是河滩,有几百米宽,长满芦苇野草,三四十年来河滨了,现在有的种菜,大多滩地都开拓成工业区了。我依稀记得方才见过一条长满荒草的沟渠,他说那便是汾河,上游修了好几个水坝,下贱就没水了。大爷说他是这里土生土长的,我问为何他有河南口音,他竖起大拇指,夸我“高人”,说他父母都是河南人,1940年代逃荒来山西的。
城里最好的风景是街上的叫卖声。尚未开业的美食城路口,一个二十几岁的女孩在卖梅菜扣肉,她坐在三轮车上玩她的手机,扩音器一遍遍叫卖:“刚出锅的梅菜扣肉,梅菜扣肉!
”我喜好这叠句,像又一个波浪推过来,那女声似杨柳新枝般明净,我不吃肉,也彷佛尝到滋味。
叫卖的一律用普通话,酒店楼下的面馆门口叫卖“包子、花卷、馒头”,是洪亮的中年男声,别无张致,功夫全在口音,那花卷的“卷”音发得很卷,而且是小小的卷儿,馒头的“头”,则听着圆圆的,且带笑意,彷佛他很爱吃馒头。
民间叫卖声的天然妙韵各地皆有。在老家那两周,无事便坐在平房上,听沿街叫卖声川流而过。卖油饼的叫:“谁要热油饼,油饼是热的,新鲜的!
”沙哑的老年女声,她不是念,是在唱,婉转抑扬,村落里的小孩都学她叫卖。另有一个卖辣椒面的,像在和你倾谈,面包车缓缓移动,车后门洞开,里面堆着几个麻袋,扩音器里值得相信的男中音款款言道:“兴平的辣子送来了!
先吃辣子后付钱,有各种粗细的辣椒面,又辣又喷鼻香,不怕辣的有指天椒,你先吃辣子,好吃再付钱,辣子不好吃,咱还不要钱!
”
5月13日
闻喜县,下邱村落
大概真有所谓“对的地方”。三天前乘火车途经,瞥见窗外的丘陵,田间阡陌,油然神往,以是就来了。
到了闻喜,忽然觉得统统都对了,街道整洁,楼房疏朗,即便老城区,亦闾巷洒然。城郊不远即是村落庄,村落庄也像村落庄,县城和村落庄,但见人家迤逦散在山川风日里。
下邱村落去城三四里,村落里都是豪宅,至少从表面看来如此,大门都很阔气,两扇红漆铁扉,高大到须仰视,匾额上书四个墨色大字,常见的有:瑞宅卧龙、天赐百福、金枝玉叶、鸿福云集,文气的有:竹韵松涛、宁静致远。这是新村落,一派新发气候。
绕到新村落后,坡上有些旧屋,土墙青瓦,门是黑漆木门,拙朴谦善,匾额皆是两个字,诸如“务本”、“朝晖”、“迎春”。此是老村落遗址,巷边长着酸枣树,碾场的石磙仍在,临巷某家院墙,是和了麦草的泥墙,并不显旧,倒是恢伟大气,整洁可喜。
某家门前铺有一段青砖路,夹路两行矮冬青,木门上了锁,锁有些生锈,门匾上书:务本。门口左边一株槐树,苍翠古朴,槐花簌簌飘落,右边生着绿苔的地上,有一块长方青石,我便在这石上坐下歇息,遥想村落里从前的生活。“你来了。”忽听得老妇的声音,举头见她笑眯眯、颤巍巍地过来,吓得我灵魂出窍,一时难辨她是人是鬼。
“走,进屋里坐。”老妇走近我,仍笑盈盈,手伸进上衣口袋里摸钥匙,额上汗涔涔。那么是人了,我想。对这个坐在她家门口的陌生人,大娘很友好,乃至没问我在这里做什么。我等她开门,自然而然,彷佛我坐在门口就为等她,而她也知道我要来。
进门使我一惊,里面藏着偌大一个院子,足有半亩地,翻耕不久,土壤痛快酣畅地袒露着,边上长些菜蔬。大娘耳朵背,说话我也听不太清,但我们都很高兴。大娘带我参不雅观她家的屋子,院东两间新盖的平房,南边三孔窑洞,我第一次进窑洞,颇觉新鲜,没想到中间有孔道相通,且窑洞里这么宽敞,碧绿蔬菜透过窗玻璃照映得炕头十分通亮。
大娘在电磁炉上烧好一锅开水,烫了两碗燕麦片,与我坐在院子里喝茶谈天。她一个人住在这里,四个儿女有一个住新村落,其他几个都在附近的城里。她说再过几天老伴就三周年,这屋子和门口的砖道都是老伴修的。我问阁下那麦草泥墙的院里有没有人住,她说有人在那里搞田舍乐,也想买她的屋子,有段韶光每天来问,一天来三次,但她不卖,“卖了往后,儿女想回来就没有退路了。”大娘说。
辞别大娘,出来正值日午,烈日当头,一片一片树荫,呆滞在路上。
5月14日
黄花岭,东官庄
连日放晴,烘烘的就到了夏天,城里女孩都穿上裙子,清新可人,亭亭如荷花。黄地皮上,尘土飞扬,她们的面庞这般白净,不知是否用了什么殊效美白产品,洁白的脸,艳红的唇。
向来怕冷的我,本日也换上短袖,走路尽拣阴凉处走。通往郊野的水泥路面上,热浪在烈日下抖动,古老的夏天,岁月的蜃景在远方映现。
去岭上田间看了看,有的麦子快要黄了。一对夫妇在除草,坐在小板凳上,地头停放着三轮车,地里种着马鞭草,开着眇小紫花,根是中药。他们说自家有十多亩地,儿子在县城事情,从不来地里干活,务农没啥收益,只有上年纪的人才乐意干。
东官庄某家在翻修窑洞,门口两个六十多岁的男人在搬砖,他们停下手中的活,和我聊了会儿天。屯子的现状都一样,大家渴求的都是钱,种地不挣钱,农业彷佛不再是本,而是边缘之末。我说现在很多城里人,都把屯子抱负得很安逸,田园生活,但若真叫他们在屯子住下,他们又不肯的。
我这话一出口,急速以为彷佛在说自己,如果吃穿不愁,我乐意还乡下安居吗?陶渊明归园田之后,连基本生活保障都没有,苦于无酒,时常饿肚,乃至不得不去讨饭,但他无怨无悔,又能从日常生活中处处拾得欢畅,树木交荫,时鸟变声,暑天北窗下卧,遇凉风暂至,便欣然自谓羲皇上人,且还能把讨饭写成诗。他全体儿无为,纯然活在当下,写诗也不过是自娱,千余年后,吾辈犹觉难以企及。
采风期间,与我说话、待我为客的全是老人,村落里年轻人很少见,纵然见了,他们也不会和我打呼唤。只有一个少年,某天中午,我坐在田埂上,他从路高下来,手机里播放着什么,他在几米之外狐疑地看着我,用普通话问:“你是哪位?”我说我不是哪位,只是在这里坐一坐。他愈加狐疑地走了,我听见他在崖下和人说话,那里有房屋,屋上冒起炊烟。
在南召县乡下,有个收狗的,四十多岁,第一天在白河附近的村落路上,我见他骑摩托转悠,车后架着三个铁笼,里面是空的,扩音器喊:“收狗!
”明天将来诰日又在中王庙村落口遇见他,他停下车,关了扩音器,笑道:“你也来这里转呢。”我说是的,他语气亲密,仿佛我们是同类,又道:“一起去桥头吃个午饭,我宴客!
”车后座上和左侧笼里各有一匹土狗,它们并不吠叫,目光悲哀地看着我。我回绝了。
直觉式的生命感知
还古诗本真面孔
“周末读诗”第二辑
《春山多胜事》
《春山多胜事:四季读诗》
作者:三书
版本:天喜文化·天地出版社 2023年4月
本文为独家原创内容。作者:三书;编辑:张进;校正:赵琳。未经新京报书面授权不得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