仰视毛泽东,品味其诗词,吸纳伟人精华,康健我辈心灵。
《五律·张冠道中》
一九四七年
朝雾弥琼宇,征马嘶北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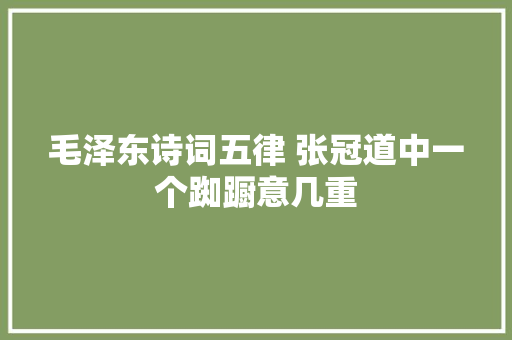
露湿尘难染,霜笼鸦不惊。
戎衣犹铁甲,男子等银冰。
踟蹰张冠道,恍若塞上行。
1947年3月中旬,胡宗南指挥国民党军二十三万余人,向中共中心肠点地陕北及延安发动进攻。3月18日晚,毛泽东率领中共中心计心情关撤离延安。随后,他在陕北延川、清涧、子长、子洲、靖边等县转战。张冠道,是他当时转战中经由的一条道路。
这是毛泽东为数不多的五律诗。
毛泽东在与陈毅谈诗的一封信中自谦说:“我对五律,从来没有学习过,也没有揭橥过一首五言律诗”。毛泽东的五律诗的确不多。在毛泽东诗词选中,仅有《五律• 喜闻捷报》《五律 •挽戴安澜将军》《五律 •看山》《五律• 张冠道中》。这几首诗,也都是诗中佳构,各有特色。
《五律• 张冠道中》生动的描述了一幅苦寒行军图。
朝雾弥琼宇,征马嘶北风。“征马”一词,精妙点出是行军途中。朝雾弥琼宇,夸年夜的手腕,写出雾大且浓。
露湿尘难染,霜笼鸦不惊。清晨的露水很重,寒露打湿黄地皮,尘土难以熏染衣物。寒冷的景象,鸟雀都怕冷,都待在窝里不鸣叫了。
戎衣犹铁甲,男子等银冰。景象寒冷,战士身上的衣服因雾沾露湿而结冰,像铁衣一样又重又硬,就像铁甲一样。眉毛胡子都因天寒而结满了冰。
以上几句,集中写出了寒冷的景象,战士们不畏寒冷,不惧艰险的乐不雅观、倔强精神。
尾句“踟蹰张冠道,恍若塞上行”。是对前文的收束。在张冠道中慢行,仿佛像在塞北行走。“表现了墨客有压力、有留恋,有寻思的繁芜感情。”(引)
“踟蹰”,本意是犹豫未定,原地徘徊之意。这里蕴含是非丰富的内容。如学者所说“繁芜感情”。从字面理解,是在张冠道慢步辇儿军。深意则没有这么大略。
胡宗南进攻陕北,敌我力量是10:1,彭老总率领仅有2万多人的西北野战军,只能以“蘑菇“战术,拖垮仇敌、拖去世仇敌,寻机歼敌。毛泽东、周恩来率领的党中心计心情关这支小部队也只能以“蘑菇“的形式,不断行军,不断转移,不断转山,以是,行军只能是“踟蹰”。只能在陕北沙场“踟蹰”行进,以达到吸引仇敌、迷惑仇敌、花费仇敌的目的。这是“踟蹰”的一个含义。
客不雅观地说,当时的陕北沙场,形势是严厉的。敌强我弱,力量悬殊陕北地贫民脊,供应困难。沙场形势变化多端,战役的决策也就不是人们在影视作品中看到的那样,彷佛统统都是胸有成竹,所有都是胜利在望,“谈笑间”就可以看到“灰飞烟灭”。以是,毛泽东,彭老总承受着巨大的压力,他们的战前决策也不得不反复“踟蹰”。这是“踟蹰”的另一个含义。
有人认为此处 “表现了墨客的犹豫满志”,是欠妥的,是望文生义。
解放战役初期,我党我军整体形势是出于计策防御阶段,整体形势都很严厉。毛泽东既要面对全国的形势,及时发出指令,又要面对身边的“蘑菇”战法,及随时面临的险境。作为一个伟人,而不是万能的“神”,毛泽东的压力、焦虑是客不雅观存在的,其感情也会“踟蹰”,这当是“踟蹰”的另一层含义。
这首诗,毛泽东的心绪是有几分凝滞、沉重的,但整体还是豪放大气的,在之后的《五律 •喜闻捷报》中,是明快、喜悦的。由于西北野战军盘踞了蟠龙旋转了霸占,转入了计策反攻。这两首诗,描写的季候不同,一个是天寒地冻,一个是天高气爽;战局不同,一个是计策防御,一个是计策反攻。作者的心情自然也不同。把这两首诗结合来读,就能更准确理解“踟蹰”的深意。理解学者所说的“有压力、有留恋,有寻思的繁芜感情。”
参考冯葱《陕北转战的真实写照——读,<五律张冠道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