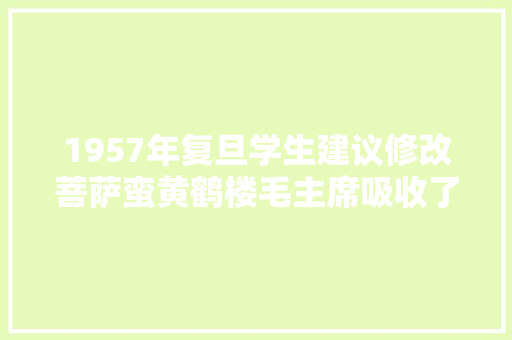虽然这首《菩萨蛮·黄鹤楼》的创作韶光比较早,但是正式揭橥的韶光却比较晚。由于直到1957年的时候,才由《诗刊》将这首词揭橥出来。
不过在《诗刊》揭橥《菩萨蛮·黄鹤楼》不久之后,就有三位来自不同地方的读者,分别给毛主席写信,指出这首词中有缺点。那么,这到底又是怎么回事呢?
一、《菩萨蛮·黄鹤楼》赏析《菩萨蛮·黄鹤楼》
茫茫九派流中国,沉沉一线穿南北。烟雨莽苍苍,龟蛇锁大江。
黄鹤知何去?剩有游人处。把酒酹滔滔,心潮逐浪高!
口语翻译:
穿过广阔无垠的时空,长江的九条支流,源源不断地汇入了汉江。两岸的粤广铁路、平汉铁路连成了一条线,贯通全体南北。
江上迷蒙的烟雨,笼罩着武汉三镇。江岸上的龟山和蛇山,就像是一把大锁一样,扼住了长江的咽喉。
传说中的黄鹤,飞到哪里去了呢?如今只剩下一处景点,供人游览。我把杯中的美酒,浇向滔滔的江水。心潮翻滚如江潮,一浪还比一浪高。
《菩萨蛮·黄鹤楼》是毛主席早期的作品,这首词中表达的感情与毛主席后期的诗词,略有一些不同。由于这首词创作于大革命失落败前夕,毛主席当时的心境是起伏苍凉的。
杨开慧在读到这首词的时候,曾经对毛主席说:这首词的前面几句太伤感了。不过读到末了两句的时候,基调忽然变得十分昂扬,让她的心潮也难以平复。
中国古代的墨客,向来有登楼赋诗的传统。古往今来,黄鹤楼上最出名的题诗,莫过于唐代崔颢所题的七律《黄鹤楼》,就连“诗仙”李白都自叹不如。
只不过崔颢的这首《黄鹤楼》,表达的是一个仕途失落意的才子,迷惘的内心天下。以是整首诗伤感的源头,实在是崔颢的个人遭遇。
但是,毛主席这首《菩萨蛮·黄鹤楼》中的苍凉感,并非是他个人的遭遇,而是源于他对国家和民族命运的深深担忧。
词中的“茫茫九派”,出于汉代刘向《说苑》中的神话故事。相传,上古时大水泛滥,禹王治水时为长江凿了九条支流,让长江“九派”,分散进入五湖;末了再经由五湖,搜集到大海。
这里的“九”,不一定是实数。按照汉语传统,三、九常常做虚数,指“多”。“茫茫”又指时空的深远广大,与“九派”合并成为词组,讲的便是亘古不变的天下格局。
词的第二句“沉沉一线穿南北”,讲的是今人修的铁路。毛主席借铁路的纵横贯穿,意喻新时期有了新的政治格局。
词的三、四句,是一个迁移转变,毛主席用烟雨莽苍,比喻大革命失落败前夕的政治氛围,以及自己对出息的短暂迷惘。
“龟、蛇”,指的是盘踞在长江岸上的龟山和蛇山,他们是阻挡正义的绊脚石。在毛主席这首词中,“龟、蛇”因此山的形式涌现的,解释反动派的力量非常强大。
词下半阕首句“黄鹤知何去”中的“黄鹤”,与崔颢的“黄鹤”都是指个人空想。词上半阕多用隐喻的办法表现作者的迷惘,这里却是昭示情形的变革,由于未知革命的下一步将如何提高。
词末端的两句,在感情上来了一个大反转,将此前的那种苍凉之感一扫而空。毛主席以杯中酒,洒向奔流不息的江水,意喻武断革命的决心。
1927年的春天,毛主席有感而发,创作出了这首词。但是当时毛主席内心的那种迷惘与困惑的心情,并未持续多久。
由于到了1927年8月,毛主席就在中心紧急会议上面就提出了“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的不雅观点。随后,毛主席去湖南、江西边界领导了秋收叛逆。
二、读者写信指出错误纵不雅观毛主席生平创作的大量诗词作品,像这首《菩萨蛮·黄鹤楼》一样平常苍凉起伏的作品,还是比较少见的,以是这首词在毛主席的词作中显得并不那么突出。
因此这首词,直到1957年才首次由《诗刊》揭橥。毛主席之以是赞许把自己的旧体诗词揭橥出来,是由于《诗刊》杂志的主编臧克家写信对主席说:
社会上流传着有8首主席的诗词,但是由于手抄传诵,导致字句与原文有出入,以是希望毛主席能正式揭橥一个定稿。
换句话说,毛主席诗词的揭橥,本意是想纠正社会上手抄稿中的缺点。谁知诗词正式揭橥后,却有三个人同时写信给毛主席,指出个中一处存在缺点。
那么,这三个人分别是谁呢?个中一个是复旦大学的学生黄任轲,一个是江苏省泰县的某小学校长,还有一个则是福建南平的陈治。
这三人指出的这一处缺点,正是涌如今前文提到的《菩萨蛮·黄鹤楼》中。原来,这首词原文里面的倒数第二句“把酒酹滔滔”的“酹”是“酎”,这三人都认为有误。
“酎”是指把美酒进行第二次酿造,制成的“醇酒”。当代人大多已经知道,像《水浒传》这类古典小说里面提到的酒,实在紧张是“浑酒”。
古人下层公民饮用的,大多是只经由一次酿造工序加工出来的酒。它采取大米、高粱之类的粮食,经由大略发酵制成,含有很多杂质。
把这种酒加以蒸馏,那就成了“重酿酒”。如果再把初酿酒和蒸馏酒进行勾兑、再加工,那就成了“醇酒”,比如日本的清酒便是这类酒。
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里面提到:酎,三重醇酒也。意思便是说,“酎”实在是酒的一个品类。特指经由三重酿造技能加工后得到的美酒,因此它是一个名词。
《菩萨蛮·黄鹤楼》原稿里的“酎”被误当成了动词,以是这三位读者建议改“酎”为“酹”。“酹”是指把酒洒在地上,借以敬拜或赌咒,这显然更加符合毛主席这首词的本意。
后来,复旦大学的黄任轲回顾往事时说,当年他凭借对宋词的热爱,能通过直觉意识到这可能是一个“笔误”。但是翻遍《诗刊》和《公民日报》,创造所有文章里面都写的是“酎”。
于是黄任轲大胆预测,毛主席的手稿可能已经出错了。于是他就鼓起勇气,写了一封信给毛主席,但是他并没想到毛主席会给他复书。
没过多久,中共中心办公室就给黄任轲回了信,信中说:你的来信毛主席已经看过,他说你提的见地是对的。从此往后,这首《菩萨蛮·黄鹤楼》中的“酎”就改成了“酹”。
结语毛主席曾经说过:客气使人进步,骄傲使人掉队。天下上没有哪个创作者能担保自己的创作永不出错,有错就改,实事求是,是毛主席一向坚持的思想路线。
因此毛主席在诗词创作生涯中,时常主动向社会各界求教。实际上,通过替毛主席诗词“指误”而成为毛主席“一字之师”的大有人在,比如罗元贞等人便是这样。
以是按照这个标准来看的话,复旦大学的黄任轲、福建的陈治和江苏的那位小学校长,也可以算是毛主席的“一字之师”。
在那个年代,之以是会涌现这种情形,完备是由于毛主席本人乐于客气接管他人的见地与建议。这一点对付如今的这些创作者来说,依旧非常值得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