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歌贵在创新。所谓创新,并不是追求笔墨表面的奇诡生僻,也不是说古人用过的词句,后人就不能再用。诗的创新,关键是在于能否自出新意。我国古代作家强调\"大众能自树立\公众,要\"大众意新语工\"大众,这些见地是深刻的。清代叶燮在《原诗》中,有这样一段话:
出而为情、为景、为事,人未尝言之而自我始言之,故言者与闻其言者,诚可悦而咏也。使即此意、此辞、此句虽有小异,再见焉,讽咏者已不击节;数见,则益不鲜,陈陈踵见,齿牙余唾,有掩鼻而过耳。这便是说:诗歌创作不能千篇一律,仿照抄袭,否则就会令人\"大众掩鼻而过\"大众。江西诗派的代表人物黄庭坚作诗,讲究法度规摹,鼓吹所谓\"大众夺胎换骨\公众之类的写作方法,结果,他的一部分诗作却是仿照抄袭,致招剽窃之讥。其《谪居黔南十首》,俱摘抄白乐天《寄行简诗》诗句,只不过是改易数字而已。例如白诗云:\"大众渴人多梦饮,饥人多梦餐;春来梦何处,合眼到东川。\公众黄把它改为:\"大众病人多梦医,囚人多梦赦;如何春来梦,合眼在乡社。\"大众有人为之辩白,说黄山谷只不过是\公众摘其数语写置斋阁,或尝为人书,世因传以为山谷自作\公众(史容)。实在,上述之诗并不是摘抄,而是洗面革心,故王若虚斥黄为\"大众剽窃之黠者\"大众,这不是没有道理的。以\公众夺胎换骨\"大众为名,行剽窃抄袭之实,这不仅在江西诗派中偶尔有之,其流毒所及则至于后世。曩读《随园诗话》内有记\"大众新安方如川秀才\公众一则,袁子才认为其学生弟子中\公众未有雅如秀才者\"大众,特录其席间赠诗一首。诗云:\"大众烟笼明月月笼烟,十里湘帘卷画船。阿翠不知秋已老,调筝犹唱杏花天。\"大众人们一看,自然就想到杜牧的《泊秦淮》:\公众烟笼寒水月笼沙,夜泊秦淮近酒家。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大众一对照,就可看出方秀才的诗是偷来的,无论是立意、章法都是一样,只不过是改了名字和题材而已。
如果说,作者只因此杜牧诗为借鉴,而能独出新意,立意新,境界新,那是无可厚非的。但方诗却非如此,通篇仿照,就不免拙劣了。叶燮在批评明代前后七子诗风时指出,他们\"大众专以依傍临摹为事,不能得古人之兴会神理,句剽字窃,维持原状\公众。这样的诗,只会\"大众令人哕而却走\公众。这些话用之于方秀才的诗,则更是贴切。诗本情性,境界求新。一味模拟,已使人生厌,而剽窃抄袭,则更是\"大众伤廉而愆义\公众了。袁子才论诗,不乏独到见地,以其学识之渊博,诗才之横溢,评诗自当别具慧眼,而对方秀才之歪诗,竟以风雅称誉,岂识之不鉴,恐一时惑于私情也。所谓\"大众人未尝言之而自我始言之\公众,便是要创新,便是要有奥妙的构思,新颖的意境。不同的作家,写相同的题材,由于构思互异,意境不同,就可写出各具特色的好作品来。戴复古说得好:\"大众意匠如神变革生,笔端有力任纵横\"大众,在这方面,我国古代不少墨客已给我们作出很好的范例。
这里,以写东风的诗为例,谈谈古人是若何不断创新的。东风是几千年来被人们反复歌咏的题材。古人的诗词中写东风者,何止千百!同是写东风而别出新意,自成一格的,的确不少。个中年夜家的妙用,实在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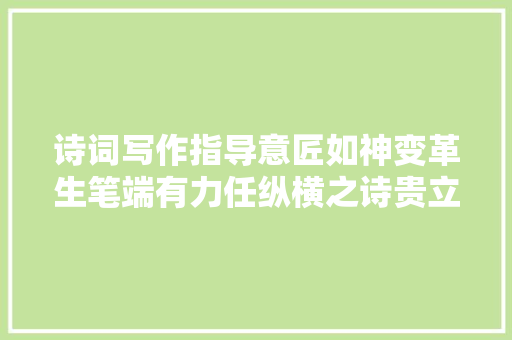
我们首先会很自然地想起自居易的\"大众野火烧不尽,东风吹又生\公众这一名句。这里的东风,是不可抗拒的生命力的象征,是给人们带来新生的青鸟使,它给受伤害的公民以鼓舞和希望,它给战斗者以必胜的信念。诗句脱口而出,明白易懂,形象光鲜而寓意深远。东风对付自然界的这种回天力量,在王安石的笔下,得到另一种极其生动的表现,这便是随处颂扬的《泊船瓜州》中的\"大众东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公众之旬。这个\公众绿\"大众字,究竟好在什么地方呢?我想,紧张之点恐怕是\"大众绿\"大众字在这里有动态,有色彩,把抽象的东风写活了。在这里,东风是详细形象的,它象征新生,象征力量。一个\公众绿\"大众字就把东风和江南岸联系起来,构成一幅大地春回,活气勃勃的画面。自居易笔下的东风和王安石笔下的东风,都象征着新生和力量,但是境界不同,互不相袭。
有些墨客喜好用东风去表现青春年少,年轻仙颜,怀春幽情,写法多样,形象生动,感情细腻。在这方面,李白是有代表性的。例如我们在前面已引用过的《春思》,头两句写景,中间两句抒怀,倒也平常,但末了两句\"大众东风不相识,何事入罗帏\公众,把东风拟人化,蕴藉蕴藉,感情诚挚,意境深远,使人玩味不尽。李白诗中写东风之处甚多,但并不使人感到重复和俗套,面是各出新意。他喜好用东风衬托妇女的年轻貌美,例如\"大众胡姬貌如花,当垆笑东风\"大众,\"大众东风东来忽相过,金樽绿酒生微波……,美人歌醉朱颜酡\公众等等。\"大众笑东风\"大众一语,生动地写出了胡姬的娇态,其俏丽动人的姿容,快乐豁达的性情,跃然纸上。这种表现手腕,在崔护<游南门题诗>中得到新的利用: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东风。这里直接写的是桃花、东风,但中央是写\"大众人面\"大众,是写人的,写得非常婉转、蕴藉。李白是用\公众笑东风\"大众去突出人物的俏丽以及由此而产生的骄傲得意的心情;崔护则以此表达对美人的眷恋。有的诗却相反,写的不是人笑东风,而是东风笑人。鲍令辉《寄行人》云:\"大众桂吐两三枝,兰开四五叶,是时君不归,东风徒笑妾。\公众这里表现的是一种深闺春怨之情。把人笑东风,改为东风笑人,两字易位,情景迥异,写法不同,但各有千秋,俱使人为之一唱三叹。
东风固是喜庆、幸福、新生的象征,但也常被用来衬托生离去世别之苦、羁旅行客之愁。用欢畅的场景反衬悲哀,或者用泪来反衬极度的喜悦,这是我国古典诗词中常用的手腕。由于墨客的处境、心情的不同,同是东风,给人的感想熏染也就不一样,它可以给人喜悦,也可增长愁怀。写离情别绪的,如李白的\公众东风知别苦,不遣柳条青\公众、\"大众东风复无情,吹我梦魂散\公众、\"大众坐思行叹成楚越,东风玉颜畏销歇\"大众,这是把东风和离情直接联系起来的写法,也可以说是直叙。有的墨客则把东风作为衬托心情的范例环境来写,例如刘禹锡的\"大众城外东风吹酒旗,行人挥袂日西时\"大众,杜牧的\公众东风十里扬州路,卷上珠帘总不如\"大众 等等。又如温飞卿的《客愁》:客愁看柳色,日久逐春深。荡漾东风里,谁知历乱心。这首诗中的\"大众柳色\"大众、\"大众东风\公众,都是为了衬托\"大众客愁\公众而涌现的,在饱经动乱、离乡背井的游子心中,东风柳色都只不过是增长愁苦的景物罢了。上面的例子,都是写一样平常的惜别之情,有的则用东风去写去世别之苦,情调更为伤感。如温飞卿的《和朋侪悼亡》中的\"大众东风几许伤情事,碧草侵阶粉蝶飞\"大众。这里的碧草、粉蝶都和东风有关,显然是春意盎然的春天景致,这种景致本来是使人感到欢快和喜悦的,但是对付因去世别而满腹\"大众伤心事\"大众的人来说,却只会引起无限伤感了。可见,同是一样的东风,由于感情不同,构思不同,表现手腕不同,在不同的诗作中就产生不同的艺术效果。
至于用东风去表现自然景致的诗篇,则更是俯拾即是,这就更须要独出心裁,别开生面,否则最易流于俗套。有的以东风写春色,寓情于景,兴寄深远,如李白的\"大众东风正澹漾,暮雨来何迟\公众、\公众轻条不自引,为逐东风斜\"大众;温飞卿的\"大众莫惹喷鼻香梦绿杨丝,千里东风正无力\"大众、 \"大众觉后梨花委平绿,东风和雨吹池塘\"大众、\"大众宜春苑外最长条,闲袅东风伴舞腰\"大众,还有雍陶的\"大众村落园门巷多相似,处处东风枳壳花\公众。有的把东风比作给人们通报感情、播送幸福的信使,如李白的\"大众此曲故意无人传,愿随东风匍策然\公众、\公众谁家玉笛暗飞声,散入东风满洛城\"大众。这里的东风,是和歌舞升平的景象联在一起的;反之,如果东风不到之处,那就意味着是一片荒凉景致,纵然有笛声,也是哀怨凄婉,王之涣的\"大众羌笛何须怨杨柳,东风不度玉门关\"大众,不便是这种情景吗?
谈到这里,彷佛关于东风的描写,已经是穷形尽相,难得再创新了,实在不然。艺术创造便是这样一种奇特的精神活动,它有无限广阔的天地,有才华的艺术家,自有其无穷的创造力。正如陆士衡说的\"大众辞程才以效伎,意司契而为匠\"大众,只假如情自内发,意从己出,独具匠心,那么,\"大众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落\公众,新的意境,自会不断涌现。东风年年有,为诗代代新,宋代王禹傅的《春居杂兴》,就给东风的描写,开拓了新的境界:两株桃杏映篱斜,妆点商山副使家。何事东风容不得,和莺吹折数枝花。这首诗的艺术构思是极其新颖的。东风本来是吹绽蓓蕾、吹放百花的,但这里的东风却成了\"大众容不得\公众杏桃盛开的对立物,竟然吹折了数枝花,岂不成了摧残群芳的反面形象?实在,墨客正是利用这样的写法,表现出春意之浓,使读者感到:不但是桃杏争春,便是东风和鸣莺,也都在争春。至于东风为什么\"大众容不得\"大众,那就让读者自己去领略吧!墨客兴会所至,是不必太拘泥落实的。
临了,又想起贺知章的《咏柳》来:碧玉妆成一树高,万条垂下绿丝绦。不知细叶谁裁出?仲春东风似剪刀。真是妙极了!东风竟然被比喻作剪刀,而苗条的柳叶,竟被想象成用剪刀裁出来的。独特的构思,奇妙的想象,把人们带到美妙的艺术境界中去了。究竟谁是剪刀的操持者呢?谁用碧玉来装点这万条垂柳呢?是造物者?是神灵?还是诗的作者?这统统,都留待读者自己去想象吧!
文艺是一种具有独创性的奇迹,只有不断创新,才能得到不朽的生命。如果因循守旧,照搬照抄,那是不会有出路的。客不雅观天下是无穷尽的,人的认识也是无穷尽的,因此,艺术上的创新也是永无止境的。任何一个有造诣的作家、艺术家,他总是有自己的独特风格,在某些方面有所创造,有所提高。\公众东风\"大众二字,尚可在古人的诗词中不断翻新,为什么我们本日的文学艺术,就不能大胆地去闯新路,辟路子,创造出无愧于我们这伟大时期的新艺术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