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是一年清明至,我踏上还乡祭祖的旅程。
随着车轮的滚动,城市渐远村落庄渐近,耳畔的鼓噪归于宁静。风拂过堤岸,鹅黄的嫩柳叶在微风中摇荡,犹如村落庄的裙摆在春光里飞动。村落沉静如水,默默诉说着岁月的故事。
甫至村落口,一阵阵艾草的暗香便沁入鼻不雅观,这是家家户户在做清明果。我老家的清明果有别于江浙的“青团”和川中的“欢畅团”,乃因此新鲜的艾叶为质料,艾叶洗净煮开后,将汁和叶分开,再与糯米粉、面粉稠浊制成面团,包入馅料。口味有三种:原味的什么都不放,拍成各种造型的粑粑即可;咸味的馅料有豆干、肉末、鲜笋、雪菜等;甜味的馅料有白糖、芝麻、猪化油。无论哪种口味,蒸熟后均晶莹碧绿,一口下去满口生喷鼻香,味美且有祛湿散寒的功效。儿时物资匮乏,能吃上几个清明果无疑是最大的享受,即便是现在,想起那种软糯暗香的味道也是舌底生津,忍不住流哈喇子。
我们执著于这一团绿,不仅仅是对美食的嗜好,更多的是一种情绪寄托。它是清明祭祖必不可少的供品,承载着我们对先人的敬意和对生活的热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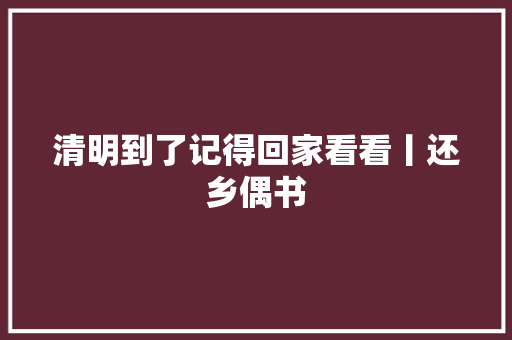
走进自家院子,父亲栽种的红豆杉和桂树已经枝叶婆娑。我抚摸着树干,仿佛能感想熏染到它岁月的沧桑。父母已经老去,他们的身影不再挺立,但眼中的慈爱依旧如初。
清明节前后一周都是祭祖的日子。准备好各种供品、喷鼻香烛纸钱和炮竹,一大早就开始去“挂山”。以前屯子没有义冢,先人的宅兆散落在不同的山头,后人到先祖坟山去扫墓,砍掉坟堆周围茅草,将纸钱挂在坟堆上方,点燃喷鼻香纸鞭炮,以纪念逝去的亲人,是为“挂山”。
由于迁徙住处,远祖的宅兆已经找不到了,祖父祖母的宅兆倒是不远,就在我家屋子后面的小山上。按程序清理完坟场周边的杂草,摆上供品,点燃喷鼻香烛纸钱,我在祖父祖母的坟前默默跪下来,思绪回到承欢祖父母膝下的稚童时期,脑海中闪过一幕幕祖父祖母疼爱我的画面:我顽皮,祖父惯着;我赖床,祖母宠着;我饕餮,祖父祖母变着办法知足;天寒地冻,祖父上山砍杉木条给我做红缨枪;狂风骤雨,祖母迎了十几里接我放学回家。酷热的夏夜,我躺在竹凉凳上看星空,祖父端来一盆煮豆荚,祖母则轻摇着蒲扇驱赶蚊虫,直至我进入梦乡……最让我印象深刻的是祖父每次上街赶集,除了给我带零食,还一定会给我买各种有趣的故事书,日积月累装书的樟木箱子满满当当。祖父读书不多,可他朴素地认为书是笨伯药,总是希望我多读点,我的文学启蒙完备是祖父给完成的。
我当时就想,等我终年夜了一定好好侍奉他们。可祖母在我十二岁时逝世,翌年,祖父也走了。人间间最不愿散去的宴席,非亲情莫属,可终极还是要曲终人散。就像我的祖父母一样,从来处来,到去处去,尘归尘土归土了。
我还能做什么呢,只有在清明时节,无论身在何方,都毅然踏上归途,回到这片熟习的地皮,为祖父母扫墓,寄托哀思。“挂山”是我与祖父母心灵沟通的特有办法,我在这一刻又重新感想熏染到了老人慈爱的目光,像阳光一样温暖,像东风一样柔柔。
做完祭祖仪式,到村落庄里转转,想摘些新鲜的艾草回来,重温一下和家人一起做清明果的觉得。路遇一发小从山高下来,两眼红肿,显然是刚刚哭过。他是个苦命的孩子,少年丧母,父亲也在前两年走了,一个人在外打工。他跟我说春节有回来过年,本来清明不打算回来的,然而,前天夜里溘然梦见父母,父亲跟他讲:
“崽啊,清明到了,记得回家看看。”
梦醒后,他泪流满面,急速决定无论如何都要赶回家,到了村落庄里还没进家门就直接来到父母坟前叩拜。和我说这些时,他眼含热泪:
“爸妈一贯惦记着我呢!
”
这几天,村落庄里的热闹一点不亚于春节,很多过春节没回来的人都回来了。路上的行人或步履匆匆,或神采凝重,他们该当都和我一样,心中装着对先人的思念和对故乡的眷恋。
当代化进程导致很多传统习俗在逐步消逝,人情味淡了,仪式感少了,尤其是我们这些流落异域多年的游子,大多已经融入了当地的生活,还乡犹如度假,刚到家就想着走了,唯有心中那份对先人的敬畏从未消散,我们无法忘怀先人的恩宠。
清明时节,我们仿佛听到了故乡的召唤,感想熏染到了先人的期盼。于是,我们整顿行囊,踏上归途,只为在那一刻,为先人献上一束鲜花,为故乡留下一份思念。它让我们在劳碌的生活中找到了回归家园的契机,与亲人团圆、共享明日亲之乐。当我们站在先人的坟前,心中涌起的不仅是无尽的思念,更是对生命的敬畏和对未来的憧憬。
(作者为福建福州市民)
• (南方周末App“hi,南周”栏目之“还乡偶书”,欢迎来信分享关于村落庄的所见所闻所思。投稿邮箱:nfzmreaders@163.com)
王卫华
责编 温翠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