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日我们来聊一聊古诗词中的“帘幕”。
在古诗词中,与帘幕有关的诗词特殊多。大家非常熟习的,有李清照的“帘卷西风,人比黄花廋”;南唐李煜的“帘外雨潺潺,春意阑珊,罗衾不耐五更寒”;刘禹锡《陋室铭》中的“苔痕上阶绿,草色入帘青”。
可以说,在中国古代的室内装修设计中,帘幕是非常常见、非常实用的一种装饰。
当然,帘幕也分为很多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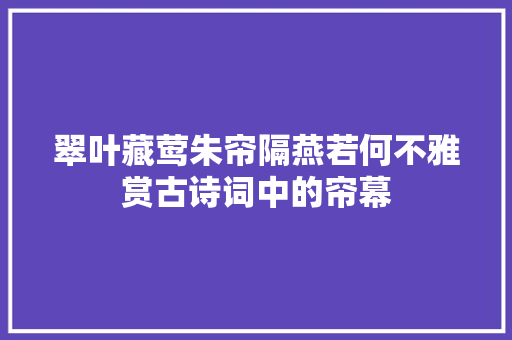
唐代高骈写《山亭夏日》,“水晶帘动微风起,满架蔷薇一院喷鼻香”,这里是水晶帘;
李方叔作《虞美人》:“好风如扇雨如帘,时见岸花汀草涨痕添”,这里是雨帘;
元朝黄庚写《江上客怀》:“梅花应念人孤寂,寒夜吹喷鼻香入竹帘”,这里是竹帘;
《红楼梦》中,林黛玉专门有一首《桃花行》,“桃花帘外东风软,桃花帘内晨妆
那么,古人为什么这么喜好帘幕呢?
据我看,至少有三种浸染:第一,装饰房屋,表示视觉美;第二,分隔空间,打造空间美;第三,陪衬气氛,营造氛围美。而这三种浸染并不是各自独立的,事实上,在所有的词作中,“帘幕”都是既具美感,又有实用功能。
比如,在唐代高骈的《山亭夏日》中,“水晶帘动微风起,满架蔷薇一院喷鼻香”,“水晶帘”解释这里的帘子是用一颗一颗水晶一样的珠子做的。此处不仅写出了帘幕的精细可爱、晶莹剔透;更是写出了听觉的效果——试想一下,当微风吹动水晶帘时,珠帘碰撞会发出若何悦耳的声音?
而微风吹过期,不仅我们的耳朵能听到帘珠碰撞清脆悦耳的声响,眼睛能看到帘珠闪耀精光残酷的效果,鼻子也能闻到醉民气脾的花喷鼻香——下一句“满架蔷薇一院喷鼻香”,想象一下,微风拂过,蔷薇满架,全体小院涌动着令人陶醉的花喷鼻香,这是若何一种美好的生活?
再仔细想一下,会发觉“水晶帘”在这里切实其实是绝妙:
不能是布帘(或竹帘),由于如果是布帘,微风吹过不会有悦耳的声响;隔着布帘也看不到满架的蔷薇;而布帘密实,花喷鼻香自然也不能轻易透过。以是唯有水晶帘,才可以有这种花喷鼻香幽幽、似隔非隔、有遮挡更胜无遮挡的效果。
再比如,宋代词人晏殊写过一首《踏莎行》:
小径红稀,芳郊绿遍。高台树色阴阴见。东风不解禁杨花,濛濛乱扑行人面。
翠叶藏莺,朱帘隔燕。炉喷鼻香静逐游丝转。一场愁梦酒醒时,斜阳却照深深院。
下阙中的“翠叶藏莺,朱帘隔燕”同样非常值得玩味。
首先,朱帘,指赤色的帘子,为什么帘子假如赤色的?看上一句就明白,“翠叶藏莺”,“朱帘”是要和“翠叶”相匹配啊,此处表示的是古人在颜色搭配上的范例审美。
而《红楼梦》中也有这么一段经典的“绿配红”:第四十回,贾母带着刘姥姥游大不雅观园,到了黛玉所居的潇湘馆,创造黛玉的窗纱旧了,当场命令凤姐为黛玉换窗纱。
换成什么样的呢?贾母的审美是“这个院子里头又没有个桃杏树,这竹子已是绿的,再拿这绿纱糊上反不配.我记得咱们先有四五样颜色糊窗的纱呢,明儿给他把这窗上的换了。”后来凤姐拿来了名贵的“软罗烟”,贾母直接说“可不是这个!
”“明儿就找出几匹来,拿银红的替他糊窗子。”你看,绿竹配红窗,翠叶配朱帘,审美这个东西啊,才是富朱紫家的标配。
而此处的“朱帘”除了与“翠叶”搭配,表示视觉美,更由于一个“隔”字,表示出空间美。
比如,在这首《踏莎行》中,“朱帘隔燕”,帘子把燕子隔在室外,首先划分了内外的空间;而接下来的场景,“炉喷鼻香静逐游丝转”,“斜阳却照深深院”,更是写出了室内场景与室外场景的不同:
室外是满眼的绿意与活泼的莺燕,而室内,是炉喷鼻香袅袅,喷鼻香烟像游动的青丝一样盘旋上升,而再往里走,是庭院深深,斜阳无言地散发着末了的一抹余晖。作者从一场愁梦中醒来,他感想熏染到的是什么呢?
是庭院的“深”与“静”,是内心的“空”与“安”:只有在这样幽深、空寂的环境里,在这样连炉喷鼻香的烟雾都可以打着旋上升、而不会被风吹散的安宁中,他才可以放荡地醉酒、发泄着内心的愁苦,而后,来一场清闲的、无人打扰的酣眠。
以是, 假想一下,如果如何没有这一道朱帘,墨客如何去享受这一份安宁?这一道朱帘,帮他隔开的不仅仅是自然环境的鼓噪,恐怕更是世俗的的骚动。
而最能表示帘幕所营造的氛围美的,当属秦不雅观这首《浣溪沙》:
漠漠轻寒上小楼,晓阴无赖似穷秋。淡烟流水画屏幽。
清闲飞花轻似梦,无边丝雨细如愁。宝帘闲挂小银钩。
室外春寒阵阵,寒意袭上小楼,天色阴阴沉沉,乍眼望去犹如深秋。在这样一个凄清的清晨中,飞花袅袅飘落,柔柔如同一场梦境;而丝雨无边挥洒,绵密犹如墨客内心的忧闷;
而室内,宝帘闲挂,画屏静立,淡烟流水,意境幽然。而相较于室外小雨轻寒、天地间一片愁苦,室内则是一片放松与清闲。尤其“宝帘闲挂小银钩”中,“宝帘”与“银钩”解释墨客物质环境优渥,生活并不窘迫,而“闲”字更是真切地写出了墨客的心不在焉与随意慵
那么,宝帘在这里究竟有什么浸染呢?除了室内的一种装饰,实在它更是一个“定位点”: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墨客这样一个富贵闲人,在这样一个阴雨蒙蒙的景象里,他在干什么呢?
从全诗来看,他彷佛什么都没做,只是倚靠在宝帘阁下,向外安静地看,一个人安静地想:
既然“飞花如梦”,那同样“梦如飞花”,是否墨客内心的梦想正如飞花一样平常被雨丝无情打落?既然“小雨如愁”,那么同样“愁如小雨”,是否在现实生活中,各种不快意带来的愁苦像这漫天的雨丝一样让人无法解脱?
以是此处的一道宝帘,是内与外的一个分隔点,更是虚与实的一个交汇点,帘外是作者的漫无边际、无拘无束的感性,帘内则是真实存在的、触手可及的生活。
正如民国期间美学大家宗白华师长西席在《美学闲步》一书中所说:
“美感的养成在于能空,对物象造成间隔,使自己不粘不滞,物象得以伶仃绝缘,自成境界;舞台的帘幕、图画的框廓,雕像的石座,建筑的台阶、栏杆,诗的节奏、韵脚,从窗户看山水、黑夜笼罩下的灯火街市、明月下的幽淡小景,都是在间隔化、间隔化条件下出身的美景。”
你看,大师所说的“间隔化”、“间隔化”,正是帘幕最基本的特色。以是,如何理解古诗词中的帘幕?很大略,不要只把它想象成一种装饰,更要把稳它背后空间的分隔——要知道,间隔所产生的美,每每更值得抚玩、更动人心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