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夜吴歌》之《冬歌》
唐·李白
明朝驿使发,一夜絮征袍。
素手抽针冷,那堪把剪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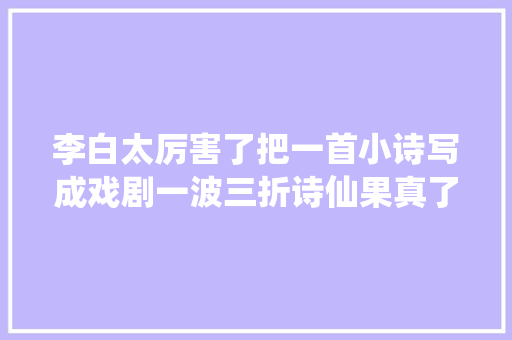
裁缝寄远道,几日到临洮。
驿使明早就要出发,思妇一夜在紧张的为丈夫赶制棉服。冬夜的抽针真冷啊!
更不用说握那剪刀了。我把衣服做好寄给远方的你,要几天才能捎到临洮呢?
起句就独具匠心,充满紧张气氛。
本来呢,丈夫在外戍边,妻子在家操劳,虽然想念,却也是无可奈何。溘然有一天,驿使降临,这是多么让人大喜过望;但驿使明早就要出发,这让这位妻子有些措手不及。难得的机会不能错过,一定要给丈夫捎点东西。
怎们也比“立时相逢无纸笔,凭君传语报安然”好一些,好歹还有一夜的韶光。仓促之下,她决定挑灯夜战,为丈夫缝制一件御寒的冬衣。为什么用“絮”而不用“做”呢?由于是冬天,做的是寒衣,妻子是絮一层又一层,恐怕絮薄了,难以抵御边塞的风寒。多少情意都落在一个“絮”上。正所谓:“蓄意多添线,含情更着棉”。驿使到来地惊喜,韶光紧迫地埋怨,内心地发急,紧张地劳碌,这些都凝缩在这两句诗中。
接下来便是紧张的劳作过程。
她如何“絮”,如何“剪”等详细过程均被省略,只选用了一种觉得——“冷”。冬日的寒夜,金属制成的“针”和“剪”是冰冷的,抽针把剪的手是更冷的。但是,这些都没有让她停滞事情。她在想着,家乡都是这么冷,那千里之外的大漠塞上,那迢遥的临洮边关该是更冷的。想到此,她飞针走线的手,纵然还冷,却更快了。万般顾虑都寄托在劳碌中,都寄托在这双手上。
末了,衣服准期做完,准期交到驿使手中,本来该当松口气,但新的抵牾冲突又来了。昨天还埋怨韶光不充足的思妇,本日又嫌韶光太“长”了,迫不及待地问了句:“几日到临洮”?这回她又恐怕驿使延误行程,愿望驿使早走、快走,早点把衣服捎到。此时不是驿使在催,而是思妇在催。
唐朝女墨客陈玉兰有“夫戍边关妾在吴,西风吹妾妾忧夫。一行书信千行泪,寒到君边衣到无”。这“几日到临洮”不便是“寒到君边衣到无”吗?
一首小诗,三十个字,却像一出戏剧,写得跌宕起伏,抵牾频发,生动动听。一波而三折,语浅而情深,这既是民歌的风格,更是李白的精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