咸丰七年(1857年)隆冬里的一天,已戎马倥偬多年的曾国藩,给初出茅庐领兵作战的九弟曾国荃致信一封,洞开肺腑,痛剖自己在修身为学方面的各类弊病,以之为镜鉴,供弟参考。
曾国藩谈到,当年甫入京师供职翰林院,本当潜心诗词书法,孰料自己好高骛远,阅读了不少杂书,致使学问不成体系,纷乱了志向。后来追随理学名家研读性理著作,这应是花大力气啃硬骨头之事,他却又按捺不住好奇,反过来翻了一大堆汉赋唐诗宋词元曲,影响了个人治学的专精取向。等到赴六部事情,由于早已习气了看闲书,每每沉不下心来研讨本部门业务,犹如半瓶水,似懂非懂,始终未成为该领域的里手里手。眼下形势所迫,曾国藩以为自己依旧有些三心二意,征战之余,还总惦记在营帐之内读读书、写写字,舞文弈棋,附庸风雅,结果倍感左支右绌,“坐是垂老而百无一成”。
既然是前车之鉴,曾国藩自不肯望九弟再蹈覆辙,忠言他:“凡人做一事,便须全副精神注在此一事,首尾不懈,不可喜新厌旧,做这样想那样,坐这山望那山。人而无恒,终生一无所成。我平生坐犯无恒的弊病,实在受害不小。”
世间有趣故意的事情,固然不少,然人生有限,倘不紧缩战线,任着性子四处出击,到头来难免落得个乱花渐欲迷人眼,竹篮打水一场空。曾国藩所言的“无恒”,实在是个人成功之大敌,不雅观其从前经历,其弊端大致有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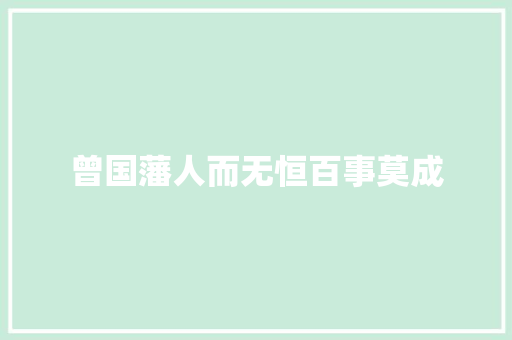
其一,无恒则易惰,徒费光阴。曾国藩能从“科考小省”脱颖而出,斩获翰林之誉,加之年纪尚浅,初入京师不免懈怠,进取心不敷,颇有些安于现状乃至漫无目标。况且翰林院平常管理宽松,无需每天点卯,日子久了,曾国藩与朋侪要么饮酒至三更,要么对谈到天明,晚睡不起成了家常便饭,不良习气在此期间悄然养成。如进京后的第二年,其日记里面常涌现“晏起”二字,意即常睡
其二,无恒则散漫,缺少毅力。一旦有了惰性,每每干事的动力便会不敷。留在翰林院后,曾国藩意识到自己学问较之来自江浙一带的同年,差距甚大,原打算发奋研究。刚好朝廷给了一个多月假期,用来闭门读书再得当不过。奈何表面的天下太精彩,曾国藩“日日玩憩,不觉过了四十余天”。异日后总结,这么多天,除了给家里写过几封信,帮人作了一篇寿文之外,“余皆怠忽,因循过日,故日日无可记录”。恒心不足,不仅做不成大事,就连往昔本可完成之事,也难于坚持,无异沦为半个废人。
曾国藩故居·丰硕堂
其三,无恒则丧志,百事莫成。当然,无恒心无定力的最大危害,想必还是将一个人的心志消磨殆尽。王阳明曾言:“志不立,天下无可成之事”“今学者旷废隳惰,玩岁愒时,而百无所成,皆由于志之未立耳”。可见志向对一个人的发展有多主要。仕途初期,曾国藩也怀有经邦济世之志。然而在自身
或许有人认为,曾氏以上毛病,无非是发展的烦恼。不过此烦恼倘不应时战胜,就会在潜滋暗长中固化为生平的烦恼,紧缚于身,挥之不去。
人最难战胜的毛病,常是积弊,必须痛下杀手。曾国藩之以是破茧重生,亦是从除积弊入手。
改变自己,须大处着眼,要树立真志。道光二十年六月初七深夜,曾国藩回顾九年前自己改号为涤生,寓意“涤其旧染之污”“从前各类,譬如昨日去世;从后各类,譬如今日生”,可惜光阴匆匆,自己仍是“不学如故”。深惭之余,曾国藩决心“勤俭有恒,无纵逸欲,以丧先人元气。困知勉行,期有寸得,以无失落词臣体面”。如果日日用功有常,自能无愧于己,无愧于人,无愧于天地。
志向好比船舵,指引航向,若想乘风破浪,还需毅力。
丰硕堂·图书馆
说到底,恒心之名贵,在于平日践履,关键在“勤”。立志后,曾国藩果真不再晚睡晚起,形成了良好的作息习气,学问事功精进。自悟后,方可使人悟。日后在家书中,其颇费笔墨评论辩论此事。九弟带兵后,军务繁重,且战局繁芜,常使人不免心生倦意。曾国藩多次告诫其利用精力犹如磨刀,越磨越快,“惟干事贵于有恒,精力难于持久,必须日新又新”“精神愈用而愈出,不可因身体素弱过于保惜;聪慧愈苦而愈明,不可因境遇偶拂遽尔摧沮”。
对付持家,曾国藩亦提醒子弟“要实施勤俭二字”“书、蔬、鱼、猪,一家之生气;少睡多做,一人之生气。勤者生动之气,俭者收敛之气。有此二字,家运断无不兴之理”。此话讲得朴实在理。古今多少家族无不是兴于勤,而败于惰?
同治二年,曾国荃出掌浙江巡抚,跻身封疆大吏。然而曾国藩写来书信,几句祝贺外,便是提醒九弟要仔细研讨奏折写法,“不可
之以是对家人如此时时忠言,“穷追不舍”,缘由便是曾国藩坚信的一个理念:“天下古今之庸人,皆以一惰字致败”。有恒勤奋,便是非凡之人,如是而已。
◎本文原载于《中国纪检监察报》(作者王学斌),图源网络,图文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