颜色是人类不雅观察天下的一种主要元素,能够超过种族、措辞等各种障碍,反响到措辞中便形成了颜色词。随着措辞的产生与发展,描述各种色彩的颜色词逐渐丰富起来,并被授予了各具特色的文化内涵。汉语的颜色词是一个弘大的系统,因此,全面研究某一期间颜色词的利用状况和利用特点,瞄准确认识该期间的社会面貌和历史文化,具有主要参考代价。
在我国古代,《内经》中就有“五色”之说,详细指“青、赤、黄、白、黑”五种颜色。“五色不雅观”在我国先民的生产生活和社会实践中逐步形成并发展起来,深深植根于中华传统文化之中。当然,随着人们对天下的认知逐步扩大和加深,颜色词也在不断增加。虽然详细颜色各有不同,但大致都能根据该颜色词所具备的范畴化特点归入“五色”种别中。
以往对古代颜色词的研究多根据传世文献,特殊是古代韵文的记载来展开。比如,汉赋喜堆辞藻,极尽铺陈排比之能事,措辞丰富且富丽,有各种颜色词近50个,自然成为研究两汉颜色词最具特点的文献。但必须指出的是,汉赋等传世文献多由文人学士所撰,反响的也多是上层社会的生活面貌,不能全面反响社会各阶层的用词特点。
近百年来,随着考古学的兴起,两汉出土文物越来越多。比如,以居延汉简为代表的河西简牍,包括居延汉简、敦煌汉简、武威汉简、肩水金关汉简及水泉子汉简等。据不完备统计,迄今为止,河西地区共出土了6万多枚两汉简牍,占全国出土简牍的四分之一旁边,占全国汉简出土量的八成以上。这些汉简不仅内容丰富,而且未经后世修正,是当时边塞生活和实用措辞的真实写照,具有主要的汉语史研究代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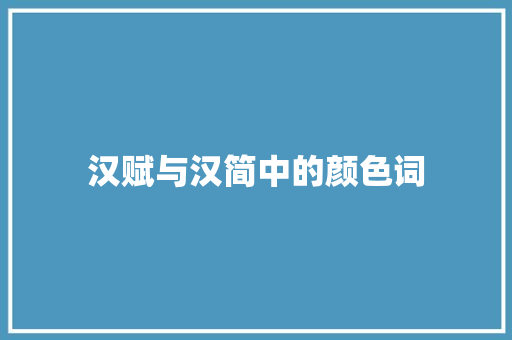
日本学者太田辰夫曾用“同时资料”和“后时资料”来区分语料性子。所谓“同时资料”,指某种资料内容及其形状(即笔墨)是同一期间产生的,如甲骨、金石、木简、作者手稿等;所谓“后时资料”,指资料形状的产生比内容产生晚,即经由转写、转刊的资料。与好用典故词的汉赋比较,河西汉简显然更能反响两汉期间的措辞征象。本文考试测验结合传世文献和出土文献,对汉代颜色词作较为系统的描述,以更加深入和全面地认识汉代社会的文化面貌和措辞特点。
赤
笔者在传世文献和出土汉简中共搜集到14个单音节赤类词,分别是“红”“紫”“缇”“绀”“緅”“縿”“朱”“丹”“彤”“绛”“赭”“赪”“赤”和“赩”。从语义上看,这些词紧张分为以下几类:第一类专指丝帛的详细颜色,如“红”“缇”“绀”等。《说文解字》记载:“红,帛赤白色。”“缇,帛丹黄色。”“绀,帛深青而扬赤色。”从《说文》的释义可知,这些颜色词虽然都含有赤色,但颜色的深浅、亮度等均不相同,可以看作“赤”类颜色词中的杂色。第二类表示本身是赤色或者能染成赤色的物品,如“朱”“丹”“绛”等。《说文》曰:“朱,赤心木,松柏属。”“丹,巴越之赤石也。”第三类泛指不同程度的赤色,如“赤”“赩”。《说文》:“赤,南方色也。”“赩,大赤也。”据《中国颜色名称》记载,“赤”泛指赤色,或表示比朱红略浅的颜色。
在汉赋中,“朱”是利用频率最高的赤类颜色词,共涌现70余例。单独利用时,“朱”紧张表示含有赤色的花草或者玉器,如东汉文学家班彪《览海赋》中的“朱紫彩烂”,墨客王粲《玛瑙勒赋》中的“杂朱绿与苍皂”。与其他名词搭配时,“朱”比范畴内其他颜色词的搭配范围更广,不仅可以与动植物类名词搭配构成“朱鸟”“朱柯”“朱荣”等,还可以与纺织、建筑、人体类名词构成“朱绂”“朱堂”“朱唇”等,更可同五行类搭配构成“朱夏”“朱形”等。可以说,“朱”是汉赋中“赤”类颜色词的原型词。
其次是“丹”“红”和“赤”,它们在利用频率上基本靠近,但在搭配时,均有不能与之相搭配的种别。如“丹”和“红”没有同动物类和五行类搭配的范畴,“赤”不能与建筑和纺织类搭配。颇故意思的是,“赤”在出土文献中却有与纺织品相搭配的实例,如居延汉简中的“赤缣”,指的便是赤色的双丝织成的细绢。当然,也不乏相似之处。在汉简中,“赤”也作为五行种别涌现,如居延简有“方赤”。在汉赋中,“缇”仅仅可与纺织品类搭配构成“缇衣”;而居延简中既有“缇绩”,也有“缇行縢”来表示橘赤色的织品。
在居延等其他河西汉简中,颜色词常常单独利用来表示某种带此颜色的物品,如居延简中的“用绛一匹”,地湾汉简中的“缇二丈三尺”,还有肩水金关汉简中的“赤色”。赤类颜色词在出土文献中利用较为零散,在与名词搭配时,多表示丝织品,涌现较多的是“赤”“绛”等,而“朱”在河西汉简中则寥寥无几。
白
笔者在传世文献和出土汉简中共搜集到表示“白”色的颜色词11个,分别是“白”“素”“皦”“皑”“皤”“皎”“皓”“缟”“粉”“霜”和“麃”。“白”的本义是“通亮”,人们对白色的详细感知与光芒的明暗相联系。详细来说,“皎”表示月光亮,“皦”形容玉石亮,以及形容洁白的“皑”和老人头发白的“皤”。它们在亮度上比表示丝织品白色的“素”更高。
在汉赋中,“白”是利用频率最高的“白”类颜色词,涌现了近百次。单独利用时,“白”常常借代表示白色事物,如在东汉文学家马融的《围棋赋》中,“白黑纷乱兮于约如葛”的“白”指白色的棋子。在与其他名词搭配时,“白”显示了强大的搭配能力,如“白鸟”“白鹿”“白杨”“白丝”“白日”“白首”等。“白”可看作汉赋中“白”类颜色词的原型词。
其次是“素”。除了与丝织品结合构成“素丝”“素旃”“素帱”外,“素”也与植物类组成“素华”,人体类“素肌”“素齿”等。然而,出土文献中的“素”却险些不用作颜色词。比如,居延汉简中的“素”大量被用作表示针织品的本义,“白素”“缣素”等都是此义。
与汉赋一样,“白”也是汉简中利用频率最高、范围最广的“白”类颜色词。它不仅搭配丝织品,如“白紬襦”“白布”“白韦绔”,也与兵器搭配,如“白玄甲”“白刀”。在敦煌汉简中还有“白粺米”“白草”等用法。
青
表“青”的颜色词有“绿”“缥”“綦”“蓝”“翠”“碧”“葱”“青”“苍”和“艵”。“青”在当代汉语中利用频率很低,“青”究竟是什么颜色,学界谈论颇多。从汉代文献来看,“青”以“蓝色”和“绿色”为主,且表“绿色”义多于表示“蓝色”或者“蓝绿色”及“玄色”义项。两类文献中,“青”利用频率最高,搭配范畴最广。
而在河西汉简中,“青黍”多处可见,是居延汉简吏卒廪食簿中常见的谷物。“青”还特指丝织品或者与丝织品连用,如地湾汉简中的“青一丈九尺”及悬泉汉简中的“青帷”。
黑及黄
传世文献和出土汉简中表“黑”色的颜色词共有8个,分别为“缁”“黔”“皂”“黑”“玈”“黯”“玄”和“卢”。汉赋中利用频率最高、搭配最广的是“玄”,占绝对强势地位,而其他颜色词零散散落,不成系统。但反不雅观出土文献,情形却完备不同。在出土文献中,“黑”和“皂”霸占主流地位,个中,“黑”描写动物颜色,如地湾汉简中有“牛一黑犗齿七”的记载,居延也有“黑牛”;“皂”紧张与丝织品搭配,如“皂布”“皂练”“皂领”等。
表“黄”色的颜色词较少,紧张是“黄”“缃”和“黈”。在两类文献中,“黄”均霸占核心地位。
通过以上剖析不难创造,虽然同为两汉语料,但出土文献和传世文献中的颜色词利用大不相同。考其缘故原由,紧张在于两类文献的写作特点不同,前者多为真实生活记录,后者强调文学夸年夜描写;前者的作者多是普通民众,后者的作者则居于庙堂。因此,在措辞表达上,出土文献中的颜色词利用不如传世文献丰富,多集中在与普通民众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丝织品和农作物的记录与描写上。这充分解释汉代河西地区不仅因时制宜栽种各种粮食作物,还积极引进内地前辈农业生产技能,并广泛用于普通民众和边塞吏卒的日常生活。这不仅知足了人们基本的物质需求,而且有力地支持了汉代在河西的边防防守和军事行动,确保了边陲安全与稳定,为当地文化的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
《光明日报》(2024年05月19日 05版)
来源: 光明网-《光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