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笔者认为,解读《卷耳》诗篇的最精彩之处,并不是诗歌主题的多元化,而是对面落笔的抒怀办法和层层推进的篇章构造。这两大写作手腕,不仅给《卷耳》诗增长了抒怀效果和艺术传染力,更成为后世“思君怀人诗”的学习榜样。尤其是它们所传达的“相思之妙境”,更是后来诗家们所追求的核心。
《卷耳》:石竹科,卷耳属植物。
个中,对面落笔常作为高考古诗词鉴赏的艺术手腕之一,诗词曲中皆有所用。诗如杜甫的《月夜》、王昌龄的《送魏二》、白居易的《邯郸冬至夜思家》等;词如韦庄的《浣溪沙》、柳永的《八声甘州》、欧阳修的《踏莎行》等;曲如郑光祖的《醉思乡王粲登楼》等。
层层推进的篇章构造,即“递进式构造”,是文章的构造形态之一,多种文体均有利用,但常见于议论文。在《卷耳》诗中,此构造紧张表现为情绪的由浅入深,由淡转浓,回环相扣。详细通过对山、对马、对人、对酒、对情绪的不同层次描述,如马的“虺隤——玄黄——瘏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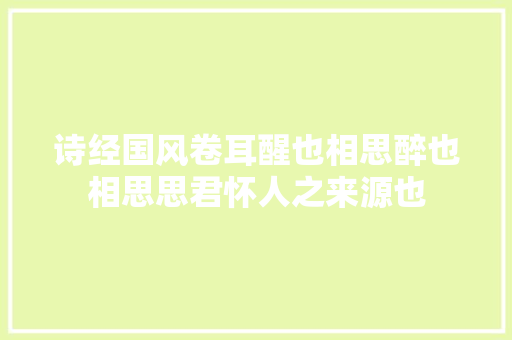
《卷耳》:球序卷耳,卷耳中的一种。
1.《卷耳》之对面落笔作为“怀人思乡诗”中的经典笔法,对面落笔指墨客并不直接写“我思人”,而是从所思之人出发,着力写“人思我”,或者由“我思人”转入“人思我”。前者是诗人情感的直接流露,每每是实写,后者是诗人情感的弯曲反响,每每是虚写。这就使读者能够透过抒怀主人公的遥想和梦呓,将所思之人的“思之浓”发掘重构,进而体会到抒怀主人公的深情。
比如,我们所熟习的《玄月九日忆山东兄弟》,前两句便采取“直接法”,直言自己身为“异域客”,每到佳节就“倍思亲”;后两句并未直线延伸,而是用“对面落笔”手腕,遥想千里之外的兄弟们,在登高“插茱萸”的过程中,因独缺墨客而生出无限遗憾。至此,全诗便如同一幕戏剧,一场对歌,超过了韶光和空间的阻隔,将墨客思乡念家的情愫推至高潮,远远超出了单边抒怀的效果。
《茱萸》:吴茱萸,芸喷鼻香科植物。
《卷耳》诗,如《玄月九日忆山东兄弟》一样,都是先直抒胸臆,再转写所思之人。诗歌首章写的是采卷耳的妻子,由于怀念远方的丈夫而延误采集,甚至于她所采摘的卷耳“不盈顷筐”;后三章则对面落笔,三次写妻子想象中的丈夫登山、马病、仆疲,以及借酒浇愁、长吁短叹的景况。结合《诗经》“诗乐舞”一体的特色,《卷耳》诗布局了一场男女相对而唱的和歌,也浑然造诣一幕浓郁的抒怀长卷。
“采采卷耳,不盈顷筐。嗟我怀人,寘彼周行。” ——《卷耳》第一章
《路》:周行,环抱的道路,特指大道。
详细说来,诗中的妻子,心不在焉地采卷耳,以是她的筐子怎么也装不满,乃至筐儿丢在大路旁也未察觉,可见她“怀人”之深切。而诗中的丈夫,则登上一座座高山,旅途艰险、长路漫漫,便是那随行的马儿,都疲倦生病、毛色玄黄。虽然有一杯又一杯的美酒,亦难解贰心中伤怀。不巧,又遇上仆人疲病不能行,断了归程,只好长吁短叹、无计可施。此中,更见丈夫难以归家的无奈和苦涩。
真可谓“一种相思,两处离愁”!
当然,对这位丈夫来说,除了超过两地的离愁,还有超过韶光的忧闷,即酒醉酒醒之间的愁!
《相思豆》:红豆感化相思意。
实际上,《卷耳》并不是《诗经》中唯一采取对面落笔的诗,其余还有《魏风·陟岵》和《豳风·东山》,但它们的对面落笔与《卷耳》诗不太一样。比如《魏风·陟岵》,只管它的每个诗章开篇都与《卷耳》后三章类似,即都写抒怀主人公三次登上高山,但它紧接着写的是“展望父兮”、“展望母兮”、“展望兄兮”,随之而来的是他想象之中父母兄长分别对他的叮嘱内容,由此来实现对面落笔。
“陟彼岵兮,展望父兮。父曰:嗟!
予子行役......”——《陟岵》第一章
《岵》:岵指多草木的山。
而在《豳风·东山》中,虽然也有对面落笔,但所涉及的人物描写较少,即直言“所思之人”的内容不多,仅有“妇叹于室。洒扫穹室,我征聿至”句。其他诗句,更多是诗歌主人公对从征生活、家中光景、新婚往事的遥想,从而扩大了该诗“思念”的工具,由“怀人诗”拓展为“思乡诗”。
由此看来,对面落笔的范围不但局限在“怀人”,也可包括写景、状物、叙事,但常见形式还是借“所思之人思我”来表达“我”的思念,犹如前述的《卷耳》与《玄月九日忆山东兄弟》一样。
《山景》:漫山红透,不解相思意。
2.《卷耳》之“递进式”抒怀在《卷耳》诗中,利用“递进式”构造抒怀的是诗歌后三章,它紧张通过重章叠句,来实现不同层次和深度的词汇更换,从而表达逐渐加深的情绪。
“陟彼崔嵬,我马虺隤。我姑酌彼金罍,维以不永怀。
陟彼高冈,我马玄黄。我姑酌彼兕觥,维以不永伤。
陟彼砠矣,我马瘏矣。我仆痡矣,云何吁矣!
” ——《卷耳》后三章
《崔嵬》:高山,波折不平,有路通畅。
首先,这三章诗的首句都说登山,但攀登的是不同的山,依次用陟彼“崔嵬”、“高冈”、“砠矣”区分。三者的差别在于山势的险要程度不同。个中,“崔嵬”指高大波折的土石山;“高冈”指高耸的山脊,“冈”为山脊、山岭之意;“砠”本义是路途中的巨石障碍物。以是,从山的可翻越程度和难度看,三类山之间呈递进关系。
其次,伴随着不同难度的山,以及隐蔽着的韶光推进,随行的马也有不同的表现,分别用我马“虺隤”、“玄黄”、“瘏矣”加以概括。只管在不少讲授中,把这三个词都阐明为“病”,但实际上三者病的程度不同,大致呈现病情加重的趋势。毕竟,在言语简练的《诗经》中,不大可能重复表意,况且此处也有不少文献资料的佐证。比如,《尔雅音义》中提出,“虺隤”为“马退不能升之病也”。
《高冈》:山脊、山岭,狭窄危险,勉强有路。
综合各家说法,“虺隤”可认为是马过于怠倦而腿脚发软,精神活力损失,无力攀登艰险之地;“玄黄”是指马因病情加重而毛色“由黑变黄”;“瘏矣”则是马病得很重,几近垂死,不能行走。将此“三病”结合前述“三山”的变革,可找到隐蔽信息,即这位旅人在路上奔波许多时日,早已超越千山万水了。
接着,诗歌便由“写山”、“写马”,转去写“人”了。第二、三章所述之人,是采卷耳的女子所思之人。他由于这漫长旅途的孤苦和寂寥,唯一能做的便是饮酒,以是诗歌用“姑酌”一词。至于“金罍”与“兕觥”,都是酒具。前者体型较大,不大可能随身携带,而后者偏小且有盖,该当有方便携带的功能。这样的安排有利于将他旅途中的“短暂勾留”也表现出来,更符合“行旅”特色。
《砠矣》:石山,虽未高耸入云,却是旅途之障碍。
第四章所写之人,是男主人公的仆人。仆人怎么样?“痡矣”!
与马“瘏矣”类似,仆人也因过度疲倦而生病,再不能行走了。
至此,摆在男主人公面前的是道阻且长、马瘏仆痡,连美酒也难以遏制他的伤怀悲叹。不过,这种伤怀悲叹也是逐层表现的。诗歌先以不切实际的“不永怀”、“不永伤”面貌涌现,再说“云何吁矣”,忧闷难尽,这便将美好欲望的破灭表现得淋漓尽致,宛如出演一幕标准的悲剧!
《皿方罍》:大型盛酒器和礼器。
综上所述,《卷耳》诗后三章,是由几组递进关系搭建而成的,其间所通报的不但是构造精美,逻辑精当,更多的是诗歌抒怀手腕中的情与景的交融,物与我的合一。
3.笔者说笔者此文,重在阐发《卷耳》诗的两大艺术手腕,即对面落笔和层层推进。但不可忽略的是,《卷耳》诗的思想代价、美学代价、历史代价等也是极高的。
《西周兕觥》
若读者有志于深入学习,请自行研读。笔者此举不过一家之言,仅是“抛砖引玉”罢了。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