晾衣竿上的秋日
·庞培
我的妈妈去河边晾衣裳
一阵风吹来。牢牢捂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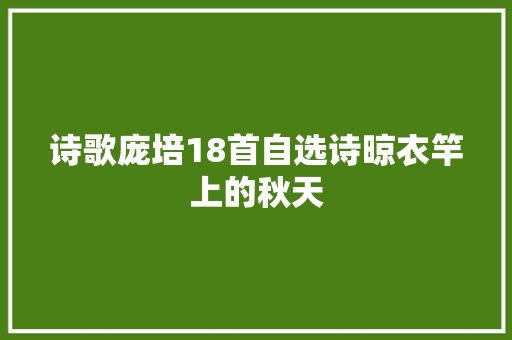
书包里的蟋蟀
河水是教材的几页
一条街的住户随风飞扬
棉单枕巾被套亵服裤……。女工们
在贫贱的弄堂口格格笑着
她们的胸很白。秋日来到了大地骄傲的私处
食堂里的早饭是一碗薄粥
车工、泥水匠和街上的小贩交头接耳
由于有人身披军管队的棉大衣
有人去了郊野的刑场
县城悄悄静
如布告上“枪毙”一词的字样
孩子们回家经由的弄堂
酷似某人亲手扣动的扳机
零散枪声似的新年
子弹从小年夜大开始,逐个发射
穿过被寒冷优待的反革命份子
推开房门,是大年初一的雪地
女友踏上了楼梯
她把脚上的雪跺在楼道里
惊喜地解开一本十九世纪的小说
阳光下,她瘦得好刺目耀眼
去世者温暖的身躯
被家常的琐事融解,五斗橱上的
“三五牌”台钟,散发一股
居委会、读报小组味
在另一个秋日
她去阳台上晾衣裳
她看来酷似当年的妈妈
连抖动棉单的手势也一样
有一次,她取出一张人为单
……衣裳洗到一半,才创造
于是晃动满手臂的水珠
在秋风中格格笑起来
那声音至今在每年的秋日
回到耳边,那去世者的冤屈
那街上的雪
也一样
凉 风
我朝阴郁索要这个词:凉风
小小船户的凉风
河面窗户的凉风
推开波光,里面
一枚水乡的玉轮
我朝埋没的州里索要这个词
丛生荷叶的野外上的风
少女般暗黑的凉风
这不会有多少人争抢占取
这是我仅存的甜蜜肃静
油条豆浆
好的感情就像油条豆浆
就像清晨的寒风
——题记
清晨呼啸着通过另一些清晨
进入日间。在图书馆资料库
一名历史学家翻查新的一页
花园宁静而湿润
是被证明了直觉
窗外飞行的鸟儿
纷纭被笔墨埋葬
晨曦犹如被扩大的义冢
新城,旧城
行间距清晰
我住地的对面是我多年前的
一次离家
我身体的旧恋人帮我醒来
一场弄堂口的大雾刚把她
送走。我俩在早点摊上坐下
亲吻和目不斜视
就着呼呼响的寒风
吃了一碗油条豆浆
(我坐在多年往后的屋子里
我能听到呼啸声——
能从我的身体里,听到
吹走我的那阵风——)
秋风阵阵
日间消逝的长长的弄堂
被一口水井填没的童年影象
有我母亲的脚步和街坊邻居
阳光下刺目耀眼的脸
河里的运粪船缓缓驶过
码头边的草丛停着朵朵白云
祠堂的天井顿时暗下来
大概我可以拣一件晾衣竿上的笠衫
做我的翅膀。不为人知
在我出生的北门街
我只是那街巷深处的围墙阴影
像小学黑板上的粉笔字,阒无人迹
被夜凉如水轻轻拭去
存在着多少命运的可能性
多少体面安静,温顺的性情
你知道一幢屋子有多少吃苦刻苦?
它的白墙发黑。它的主人远去外洋
有多少波浪轻轻拍打过思念?
一棵树上曾长出多少次寻访落空
玉轮在树下久久徘徊,吐露真情
恋人背叛了彼此
勤俭持家的夜色
有一整间屋子那么大
一长条街那么深!
工厂汽笛声
有时半夜响起,像插进土里的
黄铜的炮弹壳
五十岁那年的秋日
我想起乡下的田埂,城里坍塌的围墙
彷佛活下来的吓破了胆的士兵
想起一场战役!
我最怀念的,竟是人的受侮辱
不言不语。母亲自上干净的衬衫
波光粼粼,在地板房里走路
一间堂屋里去世者遗像的味道
一处埋没的天井,长满荒草
隔壁评弹声。收音机一样喧华的
菜市场。街道是人们挣扎着活下来的印迹。而夕阳下
河里的运粪船缓缓驶过
秋风阵阵!
秋风阵阵
夜 曲
我想说我喜好玄色。黑夜的颜色
喜好入夜下来,街上人家
亮着灯,仿佛星星
蟋蟀在草地上叫,仿佛压抑住尖叫的
音乐会上的琴童。四周的阴郁
逐步合拢,赴约的恋人们
正从四面八方赶来
书房里,我独自亮着灯
给多年以前的她,一个旗子暗记
这旗子暗记在秋日,能够照见春天
能够照见她的芳心
我手上的书页,在她
目光的温暖陪伴下
钢琴的流水声掩隐少女脸上的羞色
在莫札特的名字下面
她有一双大胆的眼睛
无数听众鼓掌起立,如醉如痴
我是他们中的一员
我也在秋夜的戏院里,轻轻地
被象牙的琴键按向玄色,摁向生命
沉静的泪水……
我喜好玄色
我从阴郁中来,走过我爱的人身旁
入夜下来!
——那是初恋的颜色
那时候还没有星星
闪烁在你懂事的眼眶
我俩在入夜后的街上跌跌撞撞
彷佛所有路面,每一幢房屋
下一秒钟,就要变成酒店的卧床
阴郁使你沉醉,也把同样的热切无常
通报到我身上。是的
这爱的色调无边无涯
永夜般握住黎明的小手
指尖和指尖,星星般相扣……
我不想要天亮,亲爱的
我想要你——阴郁中的你
夜一样平常消逝的你——有着
和我同样的阴郁
这阴郁,我俩正在相互交流
这窗外多年往后的夜色
曾经是最美的信物
恋人脸上全部的亲吻
都在这里,曾在这里……
等 待
应有若何的等待
我才能等到你
若何的日子
若何的目光
若何的手能够握到你……
不,留住你?!
一种若何的轻盈
属于你走近我的脚步
什么样的阴郁
溶解成你的美?
无数的痛楚成为期许
一个“爱”字
在你脸上伸展
夜和昼,面面相觑
什么样的力气
什么样的海洋
什么样惊人的无常
我才能得到你!
晶莹的和声
在你面庞的晶莹和声里
我拥有芬芳的影象
这一双手快速移动
这一双眼睛格格笑
没有风。没有时令。没有草地
没有深秋的月色朦胧的春夜
我手指的触摸
仿佛一个音符——
今夜这俏丽的声音重又回荡
你的到来萦绕,重重砸向
我的怔忡,你端坐如仪
永不中止。大概刚刚开始……
新 秋
秋日
我的心离不开蟋蟀的欣喜
清晨的清凉
离不开灌满整间屋子
风中一阵阵的往事
新的出行
在露湿的草地
窗户,书房都在说
那是新的秋日
新的诗句
轮船仿佛闯进了闹市区
拉响的汽笛声把江面上的风浪
提高——生活被形容成
滔滔白浪!
拍浮者奋力
回到了岸上
——我同样也离不开你
蚊叮虫咬的夏天
那些沿街的树荫
把一条老街的住户商铺
钉在了我火热的影象里
一曲难忘
我们没有不雅观众席,也没有掌声
没有灯光。所有能够点亮的灯
都是阴郁本身
没有音乐。有电视
但没有乐队进入超薄液晶屏
恢宏通亮的歌唱自迢遥的美洲或
欧洲大陆传来,如漂移的
另一颗星球
我们不在这个星球上
在另一个角落
屏幕上。奥地利维也纳的街道
仿佛女儿生日晚宴上的巧克力蛋糕
来自中国的钢琴家涌如今舞台上
彷佛宇宙员从一个神秘太空舱的侧门
现身。那不是我们的夜晚
我们没有这样的骄傲
当剧院空气说出“朗朗”这个名字
大家松了一口气,才知道
我们自己的星球
间隔音乐有多远
萨蒂的秋日
在举过的火把的印迹里
在情人的叫喊似的峡谷
空气写下“秋日”两字
生命与生命,交流
最宝贵的信物:恐怖
清晨,并非萨蒂本人
是萨蒂的钢琴曲出门
阳光的孤零零的泪水
在晨曦的眼眶里打转
秋日,我们全都心怀恐怖……
我不能使这一天开始
我不能使新的一天结束
我走到窗前。彷佛人类所有的努力屈辱
都随着我一起醒来了!
我明白,我在自己体内发明了火……
我爬出万人坑。我跃上战马
我劳作在一团混沌深渊似的中原屯子
我听的音乐比我更早绝望了
这是被停演的夏天!
留大胡子
戴夹鼻眼镜的秋日来了——
(——1924年11月24日《停演》首演。萨蒂的末了一部作品)
家门口的山
(赠陈虞)
我想要一座家门口的山
山的那边有一条江
就像长江
各处蟋蟀声中
我们爬山
就像虞山
踏歌古岸
李白过青弋江
桃花在踏歌声中
汪伦在汪伦墓边
读者是一场送别
人间是一场送别
惟诗歌相见
送别。相见
倒映开阔的江面。村落
白屋子的荡漾
出于好客和虚构
墨客的形象,一贯被江流涌动
被留在了踏歌古岸
雨 夜
……雨还不才吧!
窗户受伤的声音
活着的统统都在抽咽
都接管无奈现实
深夜里
仅亮了一盏灯的雨的陷害……
我起床,试着走出深夜——
走到你们面前——可是
诗出卖了我
雨更大了!
醒 来
一个墨客醒来,
对腐烂的黑夜说:
“这里有一颗清晨的心。”
接下来的日间更腐烂
但请先从草地上
唧唧虫鸣开始
——卡车发动机般的晨曦
寂静深处
一股短暂的飓风
知 识
知识的海浪翻卷
无人得以生还
聪明人变得更加聪明
笨伯更加蠢
但终极他们在一个浪中
相聚。在书房里
他们是同一个人
时而是我,时而是你
看着桌上成堆的书
我意识到我的生平在书本天下
形成一股危险的飓风
我被我自己刮倒——
我是冒死嚎叫但听不见的水手
是折断的桅杆
是深海漩流
覆舟之上的闪电!
……珍藏本,简体版
便携式开本
每一个浪大小均匀。书脊、
内容、修辞也一样苦涩
不!
我不说大海是我的葬身地
当永恒的日间奔跑
云层投下风凉的阴影
请给我一页诗歌!
生 前
一个人在去世之前
数月和数年去世去。他停滞呼吸
不会精准到他倒下那一刻
他并非真的去世于末了咽下的
那口气
我想起一名去世去的朋友
想起我曾打给他一个电话,在他生前
来了几个外地朋友
夜排档上。电话里我邀他出门
赶来饮酒
可是他就不出来,禁绝许
仿佛停放着的尸体
在电话里,我说话的分贝
几次提高,喊他的外号、小名、昵称……
用很难的话骂他。谩骂、起誓、领导
彷佛在对旷野上逐渐熄灭的篝火
说话,像用树棍拨开篝火的余烬
那年深秋。他生病去世了
我脑筋里一贯有个声音在嘀咕
表示悲哀、费解
两年后的一天,我一个人在屋子里
忽然想起打过的那个电话——
啊!
他不想这么晚出门了
他无法加入我们的欢聚
他去世了。乃至连自己以为很累
也无法见告我们了
一名去世者无法见告生者的
他都见告我们了
针 箍
我的母亲去世了
她出纺织厂门
走完了河边的弄堂
把被子晒在天井的蟋蟀声里
她用门前涨潮落潮的水
留给家人一只童年的针箍
缝缝补补,递给我
一条人生的河流
她去街上买菜
她8岁的儿子在屋顶和瓦砾堆
独自练习飞行
向宇宙的中央,纵身一跃
后 记
我来自长江边的一处田埂,一个滩涂;来自童年夜大空用手指捂住仍旧清晰可见的星星。妈妈利用中班和夜班安歇的间歇亲手缝制的那只书包,来自书包沿途晃荡时,内心的轻盈欢畅。来自江南水乡的冬天的水泥船,船舱里装载不值钱的粪便和长久刺鼻的氨水味。来自一间尘封的图书馆,那里面成排的书脊被贴了“思想反动”、“暂不外借”封条。来自我儿时去野外远足的一次履历。树荫、云影、河流,各处荆棘丛的树林。我不准备向黑夜、向住地的屋子里无手电筒屈从。我睡过阁楼、地板房、铺稻柴草的空地,北方堆栈和夜轮船的底层舱房。我睡过山里的石阶,溪流边的小木屋。睡在舞台人去楼空后的音箱旁。我睡我自己的书房。无数个清晨醒来,我空空如也,头脑空空。我来自大地的无限和人的致命的空虚。16岁那年我写出第一首诗歌,但没有措辞。我书写我生命中的最初的哑默,推倒一堵墙一样暴力而温顺。我来自米沃什一首关于被点火而去世的作家布鲁诺的一首诗“当他临终/从他痛楚的口中,找不出/丝毫或者半句人类的措辞……!
”是绿原译本。诗歌,是人类文明及命运残缺的译本,我来自这译本的某一行某一页,片言只语。大雨倾盆的章节,深夜的字行,一整片阴郁中波光粼粼的江面,一个被遗忘的我,一个内心充满谬误、失落败和自我冲突的我。来自街道般怯懦的人群。失落去了爱,也失落去了对美的崇奉。来自人类社会的古老的吊儿郎当。就像电影《英国病人》里的音乐。像我起身刚去了一趟卫生间,从那里得到下午晴朗、又一年秋日的讯息。我来自生活中许许多多奇妙细致的讯息,但不用措辞,用影象袒露的伤口。
我找到了一枝笔,我坐在了去世者中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