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书文化的先决条件是必须有书,否则统统无从谈起。那么何时才有书?有一种非常盛行的说法,认为甲骨、金石笔墨便是书,乃至在第62届国际图联的公开宣布中也采取了这种成说。我认为这是对书的功能缺少足够的认识。我们承认甲骨文和金石笔墨都是将人的思想言行通过笔墨、图画记录在专用载体上,并保存在一定的场所,但它们却短缺书的最主要功能。由于正式图书必须具备三项条件:一是用一定符号(笔墨或图画)所表达的内容;二是有一定形式的专用载体;三是有广泛的移动和传播功能。而末了一项是图书的最主要条件,唯此才能使人类文化得以传播、丰富和发展而形成为一种文化征象,甲骨和金石笔墨正好短缺这一主要功能,因此它们只能是档案,而我国图书的最早形态应是简书。 简书的涌现已有二千多年的历史,根据文献记载,西周至春秋已利用加工过的竹作为专用载体,可惜至今尚未创造这一期间的简策实物。而战国期间的竹简早在晋朝就有汲冢竹书的创造。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来则有大量竹简和部分木简的创造,于是简书的形制内容大体清楚。特殊是1975年湖北云梦睡虎地秦墓中创造千余枚秦文书竹简,证明简书由秦都流传到湖北的事实。简书具备了图书必须能流利的社会功能,确立了简书作为图书起源的不容置疑的地位。简书为藏书文化的开端供应了必需的根本。 “藏书”一词最早似见于《韩非子·喻老》篇,有一名叫王寿的人负书而行,被另一名叫徐冯的人在途中见到,徐冯即问:“智者不藏书,今子何独负而行?”于是王寿因焚其书而舞。王寿的藏书量虽然不多,但“藏书”既成为交往用语中的专名词,可见其已是一种比较普遍的社会文化征象。 《韩非子》,赵用贤万历十年刻本。 二、藏书文化发展的担保——藏书系统编制 可以这样认为,随着藏书的涌现,藏书机构也就涌现,并在历史进程中逐渐发展完备,纵然在战乱动荡的时期也并未忽略,因而它形成一套完全的藏书系统编制。中国的藏书系统编制大致可分官藏、公藏和私藏三大系统。直至今日似仍未能超越这三者的范围。 官藏在藏书系统编制中最早涌现,在古代文献中可以看到夏商期间已有类似管理图书的职官;但也不用除这是根据后来官制比较附的可能。不过,到西周中期以来似已有专职管理职员,《左传·昭公十五年》记周襄王对晋大夫籍谈说“女,司典之后也”,乃指籍谈九世祖伯鯈掌管晋国文籍并由此得姓而言。这种以所从事的奇迹为姓氏的事实正反响西周中期已有专司图书的职官,但还不能认为已有官藏机构。真正官藏机构是老子为周王室“守藏室之史”的藏室(《史记·老子韩非列传》)。孔子“西不雅观周室,论史记旧闻”的“室”[1],估计便是“藏室”的简称。西汉武帝在经由多次求书的根本上,正式建立了官藏机构,分宫廷的内书和政府的外书。内书分藏石渠阁、天禄阁、麒麟阁、兰台、石室、延阁、广内等处;外书则有太常、太史、博士、太卜、理官之藏。东汉则立七大藏书处,有辟雍、宣明殿、兰台,石室、洪都、东不雅观和仁寿阁等。由于藏书文化的发展,东汉政府在延熹二年(159)创建了中国第一个管理图书的中心最高机构——秘书监,正式列入国家职官系列。三国是一个纷争战乱的时期,但魏有秘书、中外三阁,蜀、吴均有东不雅观,都设有固定的职官。这解释藏书文化已成为任何一个政权所必须保存和发扬的一种文化征象。安定繁盛的时期更受到重视,如唐朝除由秘书省统管全面事情外,尚有弘文馆、崇贤馆、司经局、史馆、翰林院、集贤院等藏书和整理藏书的专设机构。宋朝除三馆(昭文馆、集贤院和史馆)与秘阁作为国家中央外,还有国子监、学士院和司天监的藏书,宫廷内府则有龙图阁、太清楼和玉宸殿,藏书文化得到极大的发扬。清代虽未设专门官藏机构,但在内府天子休憩办公之处如武英殿、懋勤殿、昭德殿、南薰殿、养心殿、昭仁殿、紫光阁、南书房、皇史宬、内阁等处都有不同数量的藏书,而乾隆帝为分藏四库全书所建南北七阁,其规模和布点可称官藏机构之最。 公藏指社会教诲、宗教机构的藏书,紧张是书院藏书。元代书院比较发达,据一种统计共有227所,个中杨惟中、姚枢所建太极书院即选取宋代文籍8000余卷作为书院藏书。清朝雍正朝之后,书院发展近2000所,许多名人提倡书院藏书,如张伯行在福州创建鳌峰书院,即“出家所藏书,充牣个中”[2]。阮元在杭州、广州先后创设诂经精舍和学海堂,即将其所编纂与刊行的各种书本用来充足这两家书院的藏书。这对推动藏书文化起到一定的浸染。 钱仪吉编《碑传集》,光绪十九年江苏书局刻本。 私藏险些与官藏先后涌现,在《韩非子·五蠹》篇中已叙及私藏图书之事。战国时的逻辑学家惠施,“其书五车”,私藏数量已不算少。西汉私藏业绩,史传颇有记载。东汉时私人藏书家亦为数不少,如杜林、班固、蔡邕、华佗等皆富有藏书;藏书量也大增,如蔡邕私藏几近万卷。历代私藏奇迹一贯在发展、丰富,显示出很大的造诣,如宋代的晁公武、陈振孙和郑樵等人不仅拥有大量私藏而且还对藏书的理论与实践作出贡献,形成社会上比较明显的文化征象,对推动藏书文化的遍及与发展起着重要的浸染。直至清代,不仅学者大多家富藏书,而且某些富商殷商亦多以藏书来标榜自身的文化气质,其覆盖所及,几遍全国,特殊是东南沿海地区私藏蔚然成风,藏书文化趋于壮盛。 中国以官藏、公藏和私藏的三大渠道汇聚了古往今来的文化精萃,形成一套完全的藏书体系,为藏书文化构筑了必不可缺的实体间架,并发挥其应有的担保浸染。 三、藏书文化与人文主义精神 中国的藏书文化包含着浓郁的人文主义精神,它的核心则是“仁人爱物”。所谓“仁人”便是把书与人的关系紧密地联系起来,使所藏只管即便发挥其培养人才的社会功能。从官藏来看,早在老子主管周藏室时,便曾激情亲切地接待孔子来查阅百二十国史记,彼此还进行了学术研讨。魏晋期间,国家藏书还曾应读者的借阅哀求而赠书,如西晋皇甫谧向晋武帝借书,武帝应求赠书一车。唐宋各代也将官藏作部分开放,如北宋的官藏即向一些官员开放,如因事情须要还可经由一定手续外借。清代尤看重官藏利用问题,在四库全书纂修以前,多位学者就有机会抄录官藏《永乐大典》所收各书,有一些主要而散佚的著作得到抢救,学者全祖望、徐松等都做过抄录事情,而《宋会要辑稿》之类的主要文籍因此得以流传。《永乐大典》还被《四库全书》作为采录佚书的来源之一,使古代文化得到更广泛的流传。《四库全书》修成后,不仅北京文渊阁可有条件地备人参阅,更在南北要地分建六阁,以便各地士人就近抄用,嘉惠士林,保存和遍及文化,所尽仁人之心,功不可没。公藏如书院之藏书本以供士子阅读为主旨,自不待言。至私藏之表示仁人之心更为显著。东汉末年学者蔡邕私藏近万卷,当他创造王粲是一位文采斐然的好学之士,虽然其女蔡琰也颇有学识,但他还是要将藏书数千卷赠予王粲以培养人才[3]。宋晁公武之以是能写出一部私家目录名著——《郡斋读书志》,也是得力于他得到四川转运使井度的年夜方赠书五十箧,使晁公武合个人私藏去重后得24500余卷,乃录诸书要旨而成书,表示了藏书文化的仁人效果。 藏书文化的仁人精神不但局限于汉民族圈,也润泽着周边各民族,并循着文化同化律的趋势发展。辽、金、夏各族以民族笔墨大量翻译汉籍,与当时各民族的政治民生密切干系,特殊值得把稳的是公元1190年由西夏编成的《蕃汉合时掌中珠》,是汉夏、夏汉的对译字典,在夏字旁注汉字读音与汉字释义,汉字旁注夏字对音和译语,两两对照,极便校阅阅兵,对沟通民族的文化互换与交融起了主要浸染。元朝也很看重提倡藏书文化,译书有《通鉴》《九经》《贞不雅观政要》等等。其文种之繁,数量之多,范围之广,都已超越前代。尤其是设立秘书监的分监,颇类似图书馆的分馆,也可视作一种流动图书馆。分监原是随着天子去上都避暑时带一些备参阅的政书和类书,但因年年如此,也便形成固定的制度。运书既有苇席、柳箱的包装,又有专人押送,并可经由严格的手续在一定范围内流利,这是前此所没有的方法。[4] 晁公武《郡斋读书志》, 嘉庆二十四年汪氏艺芸书舍刻本。 有些藏书家为了发扬藏书文化的仁人精神,亲自为人办理藏书借阅,如南齐崔慰祖聚书万卷,邻里少年来家借书,他都“亲自取与,未尝为辞”[5]。有些人如晋范蔚藏书7000余卷,“远比来读者恒有百余人”,他不仅供应阅读,还为读者“置办衣食”[6]。明清两代不少藏书家逐渐树立外借流利的不雅观念,如明末藏书家李如一就持“天下好书,当与天下读书人共之”的不雅观念,以是他“每得一秘书遗册,必贻书相闻;有所求借,则朝发而夕至”[7]。杨循吉的《题书厨诗》更直抒“朋友有读者,悉当相奉捐”的年夜方气度。许多藏书家都把借阅抄录作为丰富知识、扩大藏书的一种方法,如世学堂纽氏、澹生堂祁氏、千顷堂黄氏、绛云楼钱氏、天一阁范氏等大图书馆都曾接待著名学者黄宗羲进楼抄书。黄氏也不忘所本,诚挚地名其藏书处为“钞书堂”以志来源。黄氏之成为清初大学者未始不得力于此。藏书文化为之大放异彩。 藏书文化的爱物精神首先表现在对图书的爱护上。从汉代开始,就用竹制小箱(箧)将图书分类置放,以免丢失毁坏。东汉发明造纸术后,使藏书保护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如用檗将纸染黄后再用以防蠹[8]。当时还有一个名叫曹曾的人,家多藏书,他为此修了一个石窟以藏书,称为曹氏书仓。隋朝是藏书文化趋于高潮的期间,炀帝虽是后世所非议的人物,但他爱护图书的心极强而为史乘所称道,如《旧唐书·经籍志》即盛称:“炀帝好学,喜聚异书,而隋世简编最为博洽。”乃至博学如宋人郑樵也在其所著《图谱略》中极称“隋家藏书富于古今”。他不仅把稳典藏,还对图书的形制爱护备至,曾精选其正御本书写五十副本,分上中下三品,用不同颜色的卷轴分藏书室,并建立起能自动启合的门窗和书橱等举动步伐。唐承隋风,私藏图书超出万卷者已不在少数,而爱惜图书者更非个别。如李泌藏书三万余卷,对经史子集分别标红绿白三色以差异藏书质量。宋代除看重图书形制外表的保护改进外,还对图书的内容进行纠谬正误的订正事情,由崇文院总管秘阁和内府藏书的整理和订正,并规定逐日日课数量,有一大批著名学者如曾巩、苏颂、黄伯思等都对校订官藏有所贡献,为后世留下主要的履历。学者对个人私藏尤加存心,宋敏求家多善本,颇着意于校书,更利用这些珍本文献著书立说,成为一代著名学者。尤袤著《遂初堂书目》著录图籍的各种版本,开版本学研究之先河。 明代范钦精心营建的宁波天一阁,是至今巍然独存四百多年的古代图书馆,在它二百年后的清乾隆帝为《四库全书》建阁存书时,犹命地方督抚绘制天一阁图纸作建阁依据。它不仅拥有七万余册的藏书量,被誉为藏书天下第一家,而且对爱护图书作了多方面的设想,如防火、防蠹、防潮、防散失落等等方法,更是蜚声海内外,为众人所称道,充分表示了藏书文化的爱物精神。其他许多藏书家也多看重图书的装订、刊印和收藏,可见藏书文化精神的遍及程度。尤其是对古善珍稀的文籍更视若拱璧,不惜巨资大量地精工传抄,因而有吴抄、文抄、王抄、姚抄、祁抄、谢抄和毛抄等著名抄家,特殊是毛抄更是驰名遐迩,后世所谓毛边纸之称便是毛氏抄书的专用纸张。这种一时成风的抄书活动的文化征象,极大地丰富了藏书文化的内涵,应给以充分的研究。清初以来,藏书文化有显然的长足发展,不仅官藏、公藏看重搜求典藏,还由政府组织了工程浩大的《四库全书》的编纂事情,有选择地概括了古代、中世纪以来的中国传统文化,并将抄本分置在自东北至东南的繁盛之地。私藏尤为普遍,险些是学者无不藏书,藏者无不是学者,差异仅在于数量之多寡。 藏书文化的意识已牢牢地树立,藏书文化的精神得到极大的发扬。不少学者为了丰富所藏,不惜移居书市附近,以便疾足先得搜求到佳本善刻,当时声名卓越的学者如王士祯、罗聘、孙星衍和黄丕烈等都在京师旧书集中地附近居住,这无异是推波助澜地使慈仁寺、琉璃厂先后成为最大的藏书文化的中央而经久不衰。学者们在这里互换藏书,传播文化,造就人才,研讨学问,从各方面研究图书,于是版本、订正、目录和辑佚等专学相继涌现,逐渐完善,成为清学的紧张部分。不仅如此,多少富商殷商也被藏书文化的年夜水卷进去了。他们绝不惜啬地藏书刻书,养士编书,对藏书文化作出了应有的贡献。由于全社会能从仁人爱物的角度来重视藏书文化而把藏书文化推向了壮盛。 尤袤《遂初堂书目》,明代抄本。 以仁人爱物为中央而构成的藏书文化,对社会、民族本色的影响很大。但是,近年来由于社会转型期板块移动和撞击的波及,不仅藏书文化的不雅观念逐渐淡漠,而且藏书词汇也在人们特殊是青年人的头脑中靠近消逝,这是一种非常恐怖而严重的反文化征象,非常须要我们不遗余力来提倡和宣扬以仁人爱物为中央内容的藏书文化。 四、藏书文化的基本理论 中国藏书文化的基本理论便是环绕着“藏”与“用”的问题而展开的。从全体中国藏书史的发展过程看,“藏”彷佛是主要支点,而“用”每每处于一种次要地位,以是“藏书”的观点比较早地形成。藏书一词,千百年来未能动摇。为了藏好书,在单篇传写的时期,首先要网络零散的书加以整理与编纂,孔子是有确实姓名记载的最早的整理与编撰图书的人。他“修旧起废”,将历代遗留下来的档案、文献,整理和编订为诗、书、礼、乐、易、春秋等六大类,为藏书奠定了良好的根本。他在整理古诗三千余篇时,提出了有关藏书文化的最早理论原则,即“去其重”和“可施于礼义”者,按当代话阐明,前者是运作标准,后者则是政治标准,二者成为藏书的基本依据。他把诗先按性子分为风、雅、颂三大类,“风”下又按地域分为十五小类,这是藏书二级分类的雏形。他把六艺作为选择藏书标准,以是司马迁说:“夫学者载籍极博,犹考信于六艺。”孔子这些片段理论虽不足完全,但却为以藏为主的基本理论奠定了根本,而其影响及于后来。荀况在《王制》中说“以类行杂”和《正名》中所说“同则同之,异则异之”,都为藏书分类提出了辅导性原则,为藏书文化的发展和形成作出了主要贡献。 王先谦《荀子集解》,光绪十七年校刊本。 与此同时,“用”对藏书的浸染也被学者正式提出。韩非在《三难》篇中说“法者,编著之图籍,设之于官府而布于百姓者也”;又在《五蠹》篇中说:“今境内之民皆言治,藏商、管之法者家有之。……境内皆言兵,藏孙、吴之书者家有之。”商鞅在所写《君臣》篇中说“诗书与则民学问”。后来汉武帝为实现其大一统而不断用兵的须要,特命专人从积如丘山的简书中去整理兵书、体例《兵录》等。这些辞吐和活动都解释藏用的开始结合。 这样就形成了以藏为主、藏用结合的藏书文化基本理论。在近代以前,这一基本理论一贯辅导着历代的图书奇迹,特殊是藏书活动,乃至近代以来尚在辩论着藏与用的关系问题。这一基本理论既对藏书文化的延续发展有担保浸染,但也局限了藏书文化的发展速率和涵盖面。 在以藏为主的理论辅导下,加以历史上的兴衰治乱的不断交替,以是,藏书培植问题被放在比较主要的位置上。历代都非常看重重修和规复藏书,如汉代三次全国性的求书活动在藏书史上即霸占相称的地位。两汉之际,刘向父子的大规模整理国家藏书,为做好国家图书典藏事情和完善典藏制度树立了范例,其所编《别录》《七略》又为“用”创造了检用藏书的方便。各代相沿都有程度不同的求书活动和相应方法,如唐代不仅建立了完全的藏书机构、组织了较大规模的校书活动,还建立了典藏和利用制度。宋代由于雕版印刷的盛行,政府的看重文化和著名学者的参与,以是特殊努力于图书搜集和典藏,如南宋时曾制订多项求书方法,包括求诸著名藏书家、求诸故执政家、求诸旧秘书省主座、检索旧藏书遗留文献、求诸印刷出版业发达地区、求诸战役毁坏影响轻的地区、求诸寺庙。政府公开下求书诏,征集私家藏书目以访求遗缺书,充足典藏。 在出版物繁多、品类丰富、出版办法多样、藏书方法逐渐完备的情形下,藏书培植的理论初步形成。那便是成长于两宋之间的学者、藏书家郑樵在其所著《通志·校雠略》中提出的“求书之道有八论”,即即类以求、旁类以求、因地以求、因家以求、求之公、求之私、因人以求、因代以求的八种求书方法。郑樵生于宋代,既能看到唐以前遗留的残简旧篇,又遍不雅观当代公私藏书,总结了当世的图书采访履历和个人的采访体会,写出了“求书八法”,成为中国藏书史上对以藏为主的基本理论所作的一次比较系统的理论概括。 郑樵《通志》,元三山郡斋刻本。 明清往后,藏书奇迹更为发达,藏书文化以藏为主的理论得到进一步丰富,其最有代表性的是明万历时的大藏家祁承㸁及其《澹生堂藏书约》。祁承㸁是嗜书如命而拥有藏书十万余卷的大藏书家,自称是“蠹鱼之嗜,终不懈也”。所著有《澹生堂集》《澹生堂书目》和《澹生堂藏书约》等。个中《澹生堂藏书约》是祁承㸁在丰富的藏书根本上所形成的有系统的藏书培植理论。此书除序言外,《读书训》和《聚书训》是抄录古人聚书、读书的业绩,《藏书训略》分“购书”和“鉴书”两节,是他对自己平生购书履历的总结,也是古代藏书培植的主要文献。《藏书训略》提出“购书三术”“鉴书五法”。“购书三术”即“眼界欲宽,精神欲注,而心思欲巧”。所谓“眼界欲宽”是指要放开视野,“知旷然宇宙,自有大不雅观”,购书时不局限于某一类。所谓“精神欲注”是指养成读书嗜好,即购书者要逐渐移各类嗜好于嗜书。所谓“心思欲巧”是指要多动脑筋,多想办法。祁承㸁在郑樵求书八法外,又设想了三种搜求书本的路子:一为辑佚,二为将某些书一分为二,三为拟待访书目。“鉴书五法”包括“审轻重”“辨真伪”“核名实”“权缓急”和“别品类”等。所谓“审轻重”是指对各种图书之刊刻、亡佚与时期推移的关系给予不同的重视。所谓“辨真伪”是指负责考辨图书的作者、成书和刊刻时期的真伪。所谓“核名实”是指搞清书本的内容,以不被古人在书名上搞的各类花样所迷惑。关于书本的名实,他认为有五种环境可予把稳:“有实同而名异者,有名亡而实存者,有得一书即可概见别的者,有得其散见而即可凑合其全文者,又有本一书也,而故多析其名以示异者。”所谓“权缓急”是指根据实用代价大小,对各种图书给予不同的重视。所谓“别品类”是指做好图书的分类,而分类事情该当“博询大方,参考同异”。祁承㸁对藏书的防灾方法也很把稳,他哀求建造图书馆“既欲其坚固,又欲其透风”,这一哀求直至当前仍为建馆的主要方法之一。但是祁承㸁所提出的这套藏书培植理论,有的在实际运作上是行不通的,如主见将某些书一分为二,就会毁坏原书的完全性,造成混乱,对藏书文化的发展不利。不过,从总体上看,他所提出的各种命题对藏书文化理论培植还是有着重要参考代价的。 明朝的另一大藏书家范钦则将藏书文化的藏用结合理论作了详细实践。他不仅看重藏书的防蠹、防潮、防火、防散失落等防灾方法以完善“藏”的功能,而且还能从“用”出发收藏当代图书。所藏明方志、政书、实录、诗文集等,是研究明代政治、经济、文化科技、人物的宝贵资料,远远超出了只着眼于藏的识见。 清朝前期,在公私藏书日渐丰富、书本流利日益频繁的情形下,有关图书典藏和流利的理论也有所发展。其代表性著述是曹溶的《流利古书约》(写于明崇祯间,而刊于清)、孙从添的《藏书纪要》和周永年的《儒藏说》。 曹溶是明末清初的藏书家,鉴于战役与水火是书本散亡的基本缘故原由,而藏书家对所得孤本、善本又进行封锁,使这些书本都“寄箧笥为命”,甚至“稍有不慎,形踪永绝”,曹溶认为这是不爱惜古人劳动的行为,是“与古人深仇重怨”的表现。以是,他撰写了《流利古书约》,提出了在流利中保存古书的主见。他主见“彼此藏书家,各就不雅观目录,标其所缺者。……视其所属门类同,时期先后同,卷帙多寡同,约定有无相易”。然后各藏书家使人将己有人无之书“精工善写,校正无误,一仲春间,各赍所抄互换”。并希望有财力的藏书家将未刊布的古人著作“寿之枣梨,始小本,讫巨编,渐次恢扩,四方必有闻风接响以表彰散佚为身任者”,使社会上形成家刊秘籍的风气,对图书的流利与保存有积极浸染。但这只适用于藏书量大体相等的藏书家之间的交流流利,范围相称窄,对全国范围内的图书的保存和流利奏效甚微。不过,他的流利理论将藏书文化的以藏为主向用的方向倾斜,使藏书文化的基本理论得到一定的充足。 孙从添《藏书纪要》,嘉庆十六年黄氏士礼居刻本。 孙从添是清代前期的藏书家,所著《藏书纪要》一卷是关于藏书培植理论的一部专著。全书分八则:一曰购求,二曰鉴别,三曰抄录,四曰校雠,五曰装订,六曰编目,七曰收藏,八曰曝书。这八则总结了传统的藏书理论与技能。孙从添的藏书理论侧重于藏,他对宋郑樵的“求书八法”从另一角度提出了见地。他发展了明人谢在杭《五杂俎》中的求书五难而论求书有六难说:“购求书本是最难事,亦最美事,最美谈,最乐事。知有此书而无力购求,一难也。利足以求之矣,而所好不在是,二难也。知好而求追矣,而必较其值之多寡大小焉,遂致坐失落于一时,不能复购于异日,三难也。不能搜之于书佣,不能求之于旧家,四难也。但知近求而不能远购,五难也。不知鉴识真伪,检点卷数,辨论字纸,贸贸购求,每多阙佚,终无善本,六难也。有此六难,虽有爱书之人,而能藏书者鲜矣。”他认为抄本胜于刊本,但必须有抄书的严格哀求,字样要“笔墨匀均,不脱落,无遗误。乌丝行款,整洁中带生动,为至精而备美。序跋、图章、画像,摹仿精雅,不可呆板,乃为妙手。抄书者要明于义理者,一手书写,无脱漏差误,无破体字,用墨一色,方为最善”。他认为只有这种刊本,才能比刊刻本更为贵重,而为藏书家奉为珍宝。这些理论有利于提高藏书的质量。 周永年是乾隆期间的著名藏书家和学者,藏书丰富,学识渊博。曾参与过《四库全书》与《总目》的编纂事情。他在成进士前曾提出过著名的藏书理论《儒藏说》。这一说法是明代藏书家曹学佺所提出,他想以个人之力搜集历来的儒家经典和解经著作汇为一处,以与佛、道二藏比较美,没有涉及保存和流利的问题。周永年的“儒藏说”远较曹说为详细。周永年跳出了历来私人藏书的小圈子,提倡由社会承担起藏书的任务,使藏书为社会做事。他主见将天下图书“分藏于天下学宫、书院、名山、古刹”,让“负轶群之姿,抱好古之心,欲购书而无从”的“寒门窭士”利用。但当时的情形恐难实现,以是他又提出一套过渡方案,即由各县之主座、各地之巨族出面倡议,于当地名胜之处建立义学义田,接管藏书家的赠书和捐款。各地义学应将其藏书编为《儒藏未定目录》,相互传抄,使求书者知书本的存佚情形。各义学则分置活字一副,“将秘书不甚流传者”刊印行世,分而藏之,以使“奇文秘籍,渐次流利”。周永年还亲自购买田地,捐赠藏书,建立借书园来实验自己的主见,为“好学寻思之士”创造“博稽载籍,遍览群书”的条件,使许多学人受到冲动。儒藏说在社会上产生了影响。可惜效果不佳,而当周永年去世后,借书园也随之短命。但儒藏说却为藏书文化理论丰富了内容,为藏书向"大众年夜众开放,为图书馆向图书馆迈进起到先驱浸染。 随着历史的进入近代,西方文化的频繁渗透,维新思想的宣扬,藏书文化的藏用理论在发生变革,由以藏为主向藏用结合方向发展。十九世纪末,一批维新思想家对以藏为主的藏书思想的弊端表示异议,并先容国外情形,建议公开藏书以飨"大众。如光绪十八年郑不雅观应所写《藏书》一文,首先揭示以藏为主的弊病说:“海内藏书之家,指不胜屈。然子孙未必能读,戚友无由借不雅观,或鼠啮蠹蚀,厄于水火,则私而不公也。”继而先容西方藏书及借阅情形,并提出公开图书将有利于人才的培养,取得“我中国四切切华民,必有出于九州万国之上者”的成绩。这是走向以用为主的主要设想。光绪二十四年,京师大学堂成立,其章程第一、五、七、八各章均有专节论及图书馆的建立与管理、借阅等事,为近代图书馆的创始。二十世纪初,浙江绍兴名流徐树兰父子捐资建古越图书馆,“以家藏经史大部及统统有用之书,悉数捐入,延聘通人,分门排比;所有比来译本新书及图书标本,雅驯报章,亦复购备”,“以备阖郡人士之不雅观摩,以为府县学堂之辅翼”[9]。它虽仍以图书馆为名,而实则已订立章程,公开借阅,具近代图书馆之初型,使藏书文化的基本理论已完成从以藏为主,经由藏用结合而走向以用为主的趋势。 晚近之世,图书类型有明显变革,在纸书之外,尚有录音带、胶片和光盘等等载体的涌现。由于其体积小、藏量大,“藏”的意义相对减弱,与此同时,通过高科技手段如网络化的培植与推广,使文献资源更广泛更便利于运用,而逐渐落脚于“用”,因此,未来藏书文化将在以用为主的基本理论辅导下来完善和发展中国的图书奇迹。 五、藏书文化的恶运 藏书文化随着历代藏书的恶运而延缓其发展。世皆以秦皇焚书为书厄之始,实则此前已有其事。《韩非子·和氏》已言:“商君教孝公以连什伍,设告坐之过,焚诗书而明法令……孝公行之。”这一焚书事宜发生在秦孝公三年(前359),但《史记·商君列传》中无此记载,《韩非子集释》一书对此阐明说:“所燔之书不多,故史阙而不载耳。”秦始皇在统一后的第六年,采纳丞相李斯的建议:“请史官非秦记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于是大量图籍被毁,造成中国图书史上的一次大灾害。甚至司马迁在《史记·六国年表序》中深致慨叹说“史记独藏周室,以故灭”,《太史公自序》中又说“秦拨去古文,焚灭诗书,故明堂石室,金匮玉版,图籍散乱”,可见其严重毁坏。两汉至魏晋南北朝,虽各朝多有求书之举,而战乱兵燹不断,致使图籍散乱毁损,于是隋牛弘乃有图书五厄之说云:秦皇焚书为一厄;两汉之交,长安兵起,图书焚烬为二厄;董卓移都,西京大乱,图书燔荡为三厄;刘聪、石勒进兵京华,朝章国典从而失落坠为四厄;梁元自焚图书为五厄。有此五厄,图书得而复毁,难以积累而图书文化亦回翔于以典藏为主。至隋更有焚纬之事。谶纬之学,盛于六朝,几与经史并重,甚而为篡夺政权者所利用,刘宋始禁其事。及隋统一,文帝禁之愈切,而炀帝则大举焚纬,于大业元年(605)“发使四出,搜天下书本。与谶纬相涉者,皆焚之。为吏所纠者,至去世。自是无复其学,秘府之内,亦多散亡”。其所作为,几与秦皇相侔。自唐宋以还,书本数量大增,而兵乱范围益广,图书仍在遭受毁损,致使明胡应麟继牛弘之后而有十厄之论。他在《经籍会通一》综述其事说:“牛弘所论五厄,皆六代之事。隋开皇之盛极矣,未几皆烬于广陵,唐开元之盛极矣,俄顷悉灰于安史。肃代二宗,荐加鸠集,黄巢之乱复致荡然。宋世图史,一盛于庆历,再盛于宣和,而女真之祸成矣。三盛于淳熙,四盛于嘉定,而蒙古之师至矣。但是书自六朝之后,复有五厄:大业一也,天宝二也,广明三也,靖康四也,绍定五也,通前为十厄矣。”[10] 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 光绪二十二年广雅书局校刻本。 清初以来,于图书之搜求、庋藏及编修颇为看重。至乾隆时,国家藏书比较丰富,于是有纂修《四库全书》之议。《四库全书》的纂修是结合当时正在进行的对明《永乐大典》的辑佚和大规模地搜聚民间遗书的两项活动同时进行的。它前后共用了十五年韶光,完成了一部前所未有的大丛书,共收书3461种,793009卷,分装36300册6752函。这是中国藏书文化发展到壮盛期间的重大成果。它对古典文献的保存和流传起了重大的积极浸染,各地藏书家累世珍藏的善本书和失落传几百年而文献代价极高的珍本秘籍,都因此而化私为公,变零为整,并且还进行了分门别类的系统整理。但是,这项事情是清朝作为思想文化统治手段进行的,因而使该书在收录范围和内容上都存在着严重的问题。如借修书为名,查禁并销毁了大量具有民族、民主思想,代价较高的书本。据古人估计,修书期间被销毁的图书约在3000种旁边,险些与收书量相等,再加以抽毁与窜改,以及执事职员的玩忽,不能不对藏书文化的培植产生悲观的阻碍浸染。以是,《四库全书》的纂修对付藏书文化应给以“功魁罪魁”的评价。 近代以来,图书文化本应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而发展,但是,它犹如社会经济正常发展遭到扭曲和阻碍那样,也遭到外来的灾患和内部的纷乱滋扰。两次鸦片战役期间,英国侵略军的劫掠天一阁,英法联军的点火圆明园,以及民国期间频年的军阀混战,无不阻碍藏书文化的正常发展。特殊是抗日战役时,日本军国主义者的肆意毁灭中国文化,以战火、查禁和打劫等等低劣无耻的手段和行为来摧残藏书,据蒋复璁的《最近中国图书馆奇迹之发展》一文的估计:“‘七七’战后,东南各省……图书丢失在1000万册以上。而且丢失的多是战前充足的图书馆。”皮哲燕在《中国图书馆史略》一文中估计,战前大学图书馆藏书约590万册,抗战到1939年,丢失图书约280余万册,甚至使原来藏书充足的大学都无法知足传授教化与科研的须要。可见丢失之惨重,而败北后归还的则寥寥无几。这是中国藏书史上切切不可忘却的玄色数字,对中国的藏书文化是一次极大的毁坏。 近几十年来,由于社会经济的迅速规复,文化奇迹的得到重视,藏书量激增,藏书设备改进,藏书利用普遍,藏书文化日益受到重视。虽然在“文化大革命”的年夜难中,藏书有所毁坏,但由于各藏书单位采纳各类迂反击段,如借造反组织封馆办法,尽力减少打砸抢的可能,缩小丢失毁坏,在很大程度上保护了藏书。八十年代,政治步入正轨,经济得到发展,各项奇迹逐渐复苏,藏书奇迹也同样得到明显的迅速发展,各藏书单位增建和兴建馆舍,增大藏书的回收与入藏量,完善藏书设备和逐步走向利用当代科学技能,最大限度地知足读者的需求和利用。在即将到来的新世纪之交,中国的藏书文化在对各种藏书征象的深入研究和综括的根本上,广泛地实行和全面采取新技能,不断丰富藏书量,防止“重机轻书”的方向。那么,中国的藏书文化将继续和吸取历史遗产之精华,并贯注符合时期需求的新养料,必大显前所未有的光辉! [1]《史记·十二诸侯年表》。 [2]《碑传集》卷十七。 [3]《太平御览》卷一六九。 [4]王士点:《元秘书监志》卷三。 [5]《南史·崔慰祖传》。 [6]《晋书·范蔚传》。 [7]钱谦益:《跋陶南村落〈草莽私乘〉第二跋》。 [8]刘熙:《释名》。 [9]《古越图书馆书目》。 [10]《少室山房笔丛》卷一。 载《中国古代图书馆研究》,黄建国、高跃新主编,中华书局1999年版。 来新夏教授(1923 ~ 2014),浙江萧隐士。1942年考入北平辅仁大学史学系,1951年到南开大学任教。曾同时担当南开大学校务委员会委员、校图书馆馆长、图书馆学系系主任、南开大学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在历史学、方志学和图书文献学研究方面,成果宏富,多为首创之作。著有学术专著30馀种,整理古籍多种。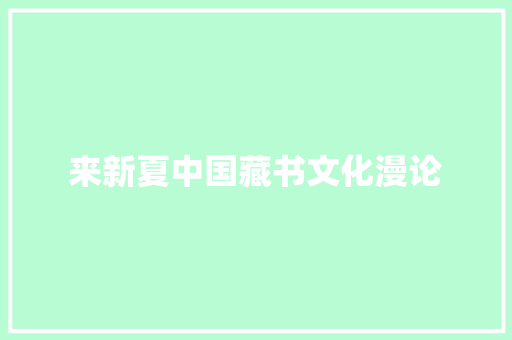
上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