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的诗词天下里,有一个很独特的意象——渔翁。许多文人墨客都喜好写渔翁,且他们笔下的渔翁形象,多多少少都带有个人情怀的寄托,比如柳宗元最有名的一首诗《江雪》,就塑造了一个"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的垂钓者形象,而这形象又分明有作者的影子:这首诗创作于柳宗元谪居永州期间,孤独一人,形单影只的垂钓者,冷漠凄清的环境,很难让人不遐想到柳宗元此时的不平境遇。
除却柳宗元外,杜甫、陆龟蒙、张志和、陆游等浩瀚文人都曾把"渔翁"写进作品中。那么,古代的文人墨客为什么喜好把自己比作"渔翁"?"渔翁"形象又详细有什么不同的内涵呢?我将不才文对此进行磋商。
一、"渔翁"形象的文化内涵:超尘脱俗,近于贤人
提及"渔翁",大家很自然就会想起姜太公钓鱼。这是发生于商周期间的一则历史传说:姜太公素有大智,每每钓鱼却都用直钩,旁人都很奇怪,问直钩怎么可能钓到鱼呢?姜太通则答:"愿者中计"。后来周文王听说姜太公的才华,与之攀谈,创造姜太公的奇才,对之加以重用,后来姜太公果真助文王推翻了商纣暴虐的统治,并辅佐武王建立了周朝。
姜太公钓的鱼不是真正的鱼,而是赏识自己的贤者。他用直钩钓鱼,实在是在等待,也是在用这样不合常理的行为为自己造声势,实质上是为了入世立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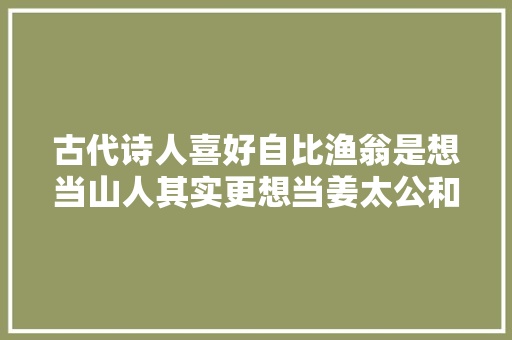
姜太公钓鱼的故事流传到后世,给渔翁形象添了不少奇幻色彩。实在文人笔下的渔翁大多都寄托着文人的情怀,虽然个中也有涉及渔翁真实生活的,但大多数诗词中渔翁形象的聪慧与豁达乐不雅观,与真正以捕鱼谋生,经历生活酸甜苦辣,乃至为生存发愁的渔翁有着实质的差异。
元代白朴有一首《沉醉东风·渔夫》,个中提到渔父虽是"不识字烟波钓叟",却"虽无存亡之交,却有忘机友,点秋江白鹭沙鸥",还"傲杀人间万户侯。"而现实天下里的渔翁真的能有如此洒脱吗?显然此曲里的形象只是寄托了作者的空想。
《楚辞》中有一篇《渔父》,个中涌现的渔翁形象也非常值得我们探究。《渔父》究竟是不是屈原所写,如今还尚存争议,但个中钓鱼江滨、避世隐身的渔翁形象则保留了下来,并与"姜太公钓鱼"一起,授予了"渔翁"意象更多的文化内涵。
当屈原被流放,政治失落意,形销骨立之时,渔翁问他何故落到如此地步,屈原答:"全球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
渔翁则说了这么一段话:
"贤人不凝滞于物,而能与世推移。众人皆浊,何不淈其泥而扬其波?众人皆醉,何不哺其糟而歠其醨?何故寻思高举,自令放为?"
渔父用充满聪慧的话表达了"变通"的处世哲学,这里的渔夫形象显然有智者的意味。当屈原并不屈服他的忠言,甘心投江也不愿与世俗与世浮沉之后,渔父只是"莞尔而笑,鼓枻而去。乃歌曰:'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遂去,不复与言。"
渔父既没不生气也不做评价,只是笑笑,唱着歌远去了,淡然无欲,给人一种博识悠远的觉得,后世不少作品中的渔父形象,都有《渔父》中这位渔钓隐者的形象内涵在,这是一"大模糊于市"的处世哲学的代表。
除此之外,《庄子》《列子》中都曾涌现过渔夫或钓鱼形象,而这形象无不使中国文化符号中的"渔翁"意象有了更丰富的意味:聪慧、豁达、淡泊。
有的乃至直接将治国比作钓鱼,如《列子·汤问篇》中的詹何,在应对楚王的发问时就说:"当臣之临河持竿,心无杂虑,唯鱼之念,投纶沉钩,手无轻重,物莫能乱。鱼见臣钩饵,犹沉埃聚沫,吞之不疑; 以是能 弱制强、以轻致重。大王治国诚能若此,则天下可运于一握,将亦奚事哉?"
宋玉的《钓赋》,则直接将圣君化为一个渔翁:"以贤圣为竿,道德为纶,仁义为钩,禄利为饵,四海为池,万民为鱼。"孟浩然的"坐不雅观垂钓者,徒有羡鱼情",指的便是倾慕垂钓者可参与政事,而自己如今则未在其位,只能倾慕一番,因此希求赏识,能得以入仕为官。
当钓鱼已经和治国联系起来,那文人们频繁写渔翁,已经不止只是表达隐士情怀,更有期盼入世的意思。
出世与入世如同一道选择题的两个选项,在中国古代封建社会里,是摆在每一个知识分子面前的,"渔翁"题材一下子糅合了这两个选项,自然是文人们绕不开的话题,古人喜好以渔翁自比,也是再正常不过的了。
二、"渔翁"的寄托:以隐求仕VS弃仕归隐
虽然同为以渔翁形象寄托情怀,不同文人在不同的心境下,其心中的渔翁形象也是不一致的,大略可以分为两类:一类因此隐求仕,一类是弃仕归隐,这实在和儒道两家的入世避世态度有些相似。
在中国长久以儒家为官方正统学说的社会影响下,多数人都是儒士出身,自小就有"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志向,以是比起弃仕归隐,以隐求仕的选择在中国古代实在更有市场。
被诗仙李白投注了无限神往和崇拜的魏晋著名风骚宰相谢安,他东山再起平定乾坤的经历,便是范例的以隐求仕。他的退隐东山是一时的选择,而这为他后来再度出仕积累了名望。
许多墨客写渔翁,实在是期盼像姜太公钓鱼那样,表达了希望有贤者赏识自己的心情。如孟浩然那首著名的《望洞庭湖赠张丞相》,表达的即是这个意思。
唐代卢仝有一首《直钩吟》:"初岁学钓鱼,自谓鱼易得。三十持钓竿,一鱼钓不得。人钩曲,我钩直,哀哉我钩又无食。文王已没不复活,直钩之道何时行。"就比较直白地用姜太公直钩钓鱼的典故,表达了自己欲求赏识却无人赏识的凄苦心境。
而《庄子》中《渔父》篇,则是"弃仕归隐"的代表。庄子通过写一名渔父指斥孔子的话以及孔子对渔父的尊敬,表达了守真、回物化然的主见。
而《秋水》中有一段《庄子钓于濮水》,则更明确地表明他这种"弃仕归隐"的态度,这里的庄子也是一个渔夫形象,当他正在钓鱼,楚王让两个大夫去请他出相,庄子说"往矣!
吾将曳尾于涂中",谢绝了出相,表明自己不慕名利,只愿在自然生活中快乐过日的欲望。
中国的大部分知识分子在一开始都是寻求积极入世的,但人生无常,生活对人的磨砺不可谓不深,更何况朝堂风云变幻,一个不慎,贬谪还是其次,身家性命都可能丧失落。以是不少人在仕途遭遇挫折或一贯怀才不遇的情状下,很随意马虎借"渔翁""桃源"等寄托情怀,这时他们笔下的渔翁形象实在是繁芜的,有的既有愿求赏识连续入仕的心思,又多多少少有着退居山野清闲度日的心态。
被认为写渔翁形象最经典的柳宗元,除《江雪》外,还有一首《渔翁》也颇为有名:
"渔翁夜傍西岩宿,晓汲清湘燃楚竹。烟销日出不见人,欸乃一声山水绿。回看天涯下中流,岩上无心云相逐。"
前四句还意境开阔,尤个中央两句随处颂扬,写得仿佛这山水美景都是由于渔夫一声呼唤而通亮起来了一样平常,给渔翁授予了极其独特的形象,但结尾两句却又苦处凝集,又沉浸到寂寞的田地里去了。这实在就表明了他一种抵牾的生理:既在山水渔翁之间找精神寄托,而这探求也确实有所成效,他的心情一时开阔,但过不了多久,遭受贬谪的事实和此刻的人生境遇让他又重新心绪低落起来。
这种心境在开阔与狭窄之间的转换,正是中国知识分子在为政路上普遍所经历的心途经程。
其余,也有一类渔翁形象,则寄托了作者对平凡大略生活的神往,不过这个中也有或多或少的表明自己追求超凡脱俗心境的意思在。张志和的《渔歌子》中的渔父,"一蓑风雨,斜风小雨不须归",就将这种无畏风雨,淡然从容应对生活的态度表达得十分贴切。
不管是柳宗元的"独钓寒江雪",王士祯的"一人独钓一江秋",还是杜甫的"江湖满地一渔翁",文人士子以"渔翁"形象来表达自己或以隐求仕或弃仕归隐的态度,或退或进,有时候以退为进,要么寄托情怀,要么隐含心绪期待他人看出,个中蕴含的心意是繁芜的,虽大略分为这两类,但详细的作品还需详细的剖析:看是战乱导致墨客想要避世,还是追忆典故表达自己同样的或出世或入世的欲望,还是如王维一样平常心性寄予田园山水,或如陶渊明一样对自然有着天生的喜好,只愿归于自然,别无所求?
入世的其余一个范例代表,当是近代的袁世凯,袁世凯在清朝末年也上演了一场“以退为进”的好戏,成功塑造了一个恬淡的“洹上渔翁”形象,但仍旧运筹帷幄,一旦机遇来临,即刻就会重新出山,重掌大权。
不管是哪种答案,都不影响"渔翁"意象在中国文化中的分外意味,透过这个意象,可知中国古代知识分子一部分的精神面貌,这在本日依然存在于我们的文化符号中,并将在日后持续发挥着浸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