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调歌头·昵昵儿女语
苏轼 〔宋代〕
欧阳文忠公尝问余:“琴诗何者最善?答以退之听颖师琴诗最善。公曰:此诗最奇丽,然非听琴,乃听琵琶也。余深然之。建安章质夫家善琵琶者,乞为歌词。余久不作,特取退之词,稍加隐括,使就声律,以遗之云。
昵昵儿女语,灯火夜微明。恩怨尔汝来去,弹指泪和声。忽变轩昂勇士,一鼓填然作气,千里不留行。回顾暮云远,飞絮搅青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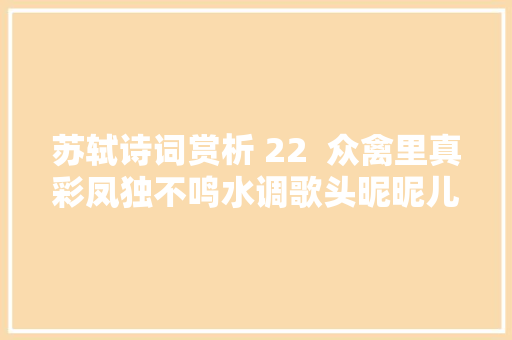
众禽里,真彩凤,独不鸣。跻攀寸步千险,一落百寻轻。烦子指间风雨,置我肠中冰炭,起坐不能平。推手从归去,无泪与君倾。
译文
初闻一对爱侣亲密地窃窃密语,在那灯火如豆的岑寂夜里。旋即由爱生怨,絮絮叨叨说来道去,弹指间说得酸楚难抑,禁不住含泪哭泣。忽然琵琶声变,如见气昂昂勇士出战,战鼓填填一马当先,驰驱千里无流连。回顾暮云已远在天边。依罕有柳絮回旋无尽,在那寥廓的上苍。传来百鸟齐鸣,唯独听不到凤凰的啼啭。声声高扬势如登攀,寸步竟有千重险,陡地一落千丈如坠崖,却又以为身轻似燕。难得你拨弄手指如有神,兴起风雨掀波澜,竟把世间冰炭凉热,一并搁进我的心田,令我心潮涌起坐立不安。推开琴任从琴师归去,我已没有泪水洒给你了——泪已流干。
【解析】
媒介对这首词的写作原由作相识释,是根据韩愈(字退之)的诗作《听颖师琴》改写而成。隐括,指依照词牌的格式和声律将原诗进行修正,使其符合词的文体形式。
韩诗如下:“昵昵儿女语,恩怨相尔汝。划然变轩昂,勇士赴沙场。浮云柳絮无根蒂,天地阔远随风扬。喧啾百鸟群,忽见孤凤凰。跻攀分寸不可上,失落势一落千丈强。嗟余有两耳,未省听丝篁。自闻颖师弹,起坐在一旁。推手遽止之,湿衣泪滂滂。颖手尔诚能,无以冰炭置我肠。”东坡改诗为词,更富有韵律感、音乐美,内容上也作了修正,既虔诚于原作,又有新意。赏析这首词有两点值得把稳。第一是通感手腕的利用。钱锺书师长西席曾将韩愈《听颖师琴》中的音乐描写与白居易的《琵琶行》里传诵的那几句著名的音乐描写作了比较,认为白居易只是用雨声、密语声、珠落玉盘声、间关鸟声、幽咽水声来比方琵琶声,“只是从听觉联系到听觉,并非把听觉沟通于视觉”;认为韩诗的音乐描写,那才是“心想形状如此,听声类型,把听觉转化为视觉了”。这就显出韩愈写得深刻,由于他写出了通感。钱锺书师长西席提出这种“通感”,即把听觉、视觉、嗅觉、味觉、触觉沟通起来的修辞方法。这在韩愈这首描写听觉艺术的诗中得到了充分的表现。他利用动态光鲜的视觉形象摹写音乐的柔柔与雄壮、高亢与低沉、徐缓与急骤、冷与热,给人一种动态美的美感。改写后的苏词保留并突出了这种通感手腕给予人的艺术传染力。
还有一点值得把稳。东坡词对韩诗的改动不可能是无缘由的,是否另有深意,试作如下剖析。如媒介中所言,朋友家的弹琵琶者要求东坡作歌词,历来有求必应、常常即席挥笔相赠的坡仙何以“久不作”?这与他和欧阳修之间的答问内容不无关系。东坡认为韩愈的《听颖师琴》“最善”,欧阳修也赞之“最奇丽”,东坡深以为然,这大约是他“久不作”的缘故原由之一,这与李白游历黄鹤楼时见到崔颢题诗而罢手停笔是一样的心态。料想东坡喜好这首韩诗的缘故原由不但是诗中通感的手腕,个中的“勇士赴战”“百鸟”与“孤凤”“跻攀”与“一落千丈”的升沉比拟、心中“冰炭”般骤冷骤热的感想熏染,不能不引起东坡关于自身仕途升沉和人生况味的遐想与共鸣。韩诗的“喧啾百鸟群,忽见孤凤凰”“百鸟”与“孤凤”并无大的空间阻隔,苏词改为“众禽里,真彩凤,独不鸣”,“真彩凤”哑然失落声于“众禽”的喧啾声中,这与东坡仕途遭受群小诬陷而贬逐流放、寂然独处的景况何其相似乃尔。韩诗入耳琴者“湿衣泪滂滂”,苏词却是“无泪与君倾”——泪已流干。何以惨痛如此?仅就琵琶听到并看到的意象——“轩昂勇士,一鼓填然作气,千里不留行”的勇往直前的悲壮,“跻攀”与“一落”之间的险恶,“肠中冰炭”的人生冷暖的感想熏染,便能引发苏轼有关自身官场浮沉的无限慨叹。料想苏轼写罢“无泪与君倾”时,该因一吐满腹愤郁而嘘唏不已了!
创作背景
此词作于元丰三年(1081)七月。苏轼黄州《与朱康叔书》说,“章质夫求琵琶歌词,不敢不寄呈”,时朱康叔任鄂州(州治在今武昌)太守。元丰四年四月,章质夫为荆湖北路(治所在江陵)提点刑狱,离黄州不远,有书信往来。但此词在寄呈《次咏章质夫〈杨花词〉》及《七夕》之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