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亦且如平日醉,莫教弦管作离声。
——欧阳修《别滁》
仲春的滁州,已是一派繁花似锦,花光残酷多姿,绿荫浓郁,垂柳在和煦的东风中摇荡着动人的身姿。春光里,繁花和绿叶是那样的活气盎然。就在北宋庆历年间的某一个春日里,滁州知州欧阳修却要离开这个事情了两年之久的地方。
滁州的百姓和欧阳修事情期间的同事们在这样一个春光骀荡的日子里,在花前设下饯别的酒宴,欧阳修也像平日一样和大家一同开怀畅饮,丝毫没有离去的伤感,他还对宴会上弹奏乐器的乐工们说,不要弹奏令人感伤的乐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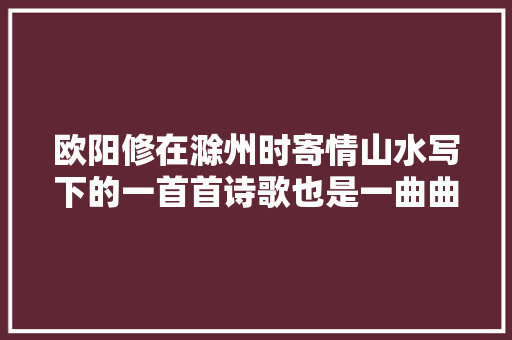
离去在即,滁州百姓对欧阳修的不舍之情,以及激情亲切的话别场面,都让他百感交集,于是欧阳修写下了这首《别滁》。
不只是滁州百姓对欧阳修不舍,欧阳修对这片地皮,以及生活在这片地皮上的淳厚的百姓也是依依不舍。
滁州,欧阳修人生旅途上的一个中转站,他在滁州事情的两年多的光阴里,这里的山山水水、这里的风土人情、这里的淳厚民风早已融进欧阳修的影象深处。
庆历五年,欧阳修来到滁州上任。刚来滁州时,由于公事繁忙,他没有空隙的韶光游赏滁州的山水,等他将事情处理得井井有条后,他便抽出韶光寄情山水。为此还在滁州琅琊山建筑了一座醉翁亭。
亭子建成后,欧阳修常同朋友到亭中游乐饮酒,“醉翁亭”因此得名。而让醉翁亭声名远扬确当属欧阳修在醉翁亭写下的游记《醉翁亭记》。
欧阳修就像是一位技艺高超的拍照师一样,将滁州的山水风光逐一摄取,他用幽美的笔墨与画面再现了滁州幽美的山水,正像《醉翁亭记》中描述写的那样:“环滁皆山也。其西南诸峰,林壑尤美,望之蔚然而深秀者,琅琊也。”
琅琊山林壑幽深、溪流淙淙,素有“蓬莱之后无别山”美誉,山中大片天然次生林保存无缺。紧连琅琊山之北是丰山,也是欧阳修常去的地方,丰山体态雄伟耸立,从西面环抱着滁州古城,是离滁州古城最近的山。
然而,欧阳修与丰山的不解之缘却在他来滁州后的第二年夏天。当欧阳修有和同事们登上丰山,创造丰山上有一条溪流绕着山势淙淙流淌,溪水清澈。
欧阳修掬起溪水品尝,味道清爽甘冽。正所谓饮水思源,于是他沿着溪流的方向探求源头,果真在不远处就创造了一泓清泉,水流便是从这眼清泉中流出去的,这让欧阳修喜不自胜。
带着创造溪流源头的喜悦,欧阳修在泉边开凿了一条小渠,将一部分泉水疏引到阵势较为平坦的地方,又形成了一个新的水泉,欧阳修将这泓新泉命名为“深谷泉”,并写了一首《深谷泉》的诗,以记其事。后来,滁州知州陈知新重修深谷泉,将其改名为紫微泉。
看着清冽的泉水,欧阳修以为在这里再搭建一个亭子,以供游人栖息容身、不雅观赏风景,就再好不过了。于是他冒着酷热,亲自方案设计了亭子的样式,并与滁州百姓携手将亭子建成,欧阳修为此亭取名“丰乐亭”。
对付以文章著称的欧阳修来说,又怎么能少得了诗文的点缀呢?以是在亭子建成后,一篇《丰乐亭记》便从欧阳修的笔端犹如丰乐亭的涓涓清泉一样流淌而出。
欧阳修“疏泉凿石,辟地以为亭”的事情,被他用细腻生动的文条记载在散文《丰乐亭记》中。文章从探求泉水水源、疏引泉水,建筑丰乐亭、取名“丰乐亭”入手,既描述了滁州山泉景致之美,又赞颂了滁州人们丰衣足食、民享安乐的太平景象。
自丰乐亭建成之后,欧阳修一有空隙便来到这里,领略滁州山水的魅力,在《丰乐亭记》中,有这样一段真切的笔墨记载下了墨客登上丰山的足迹,以及墨客领略滁州山水的心情:
既得斯泉于山谷之间,乃日与滁人仰而望山,俯而听泉。掇幽芳而荫乔木,风霜冰雪,刻露清秀,四季之景,无不可爱。
欧阳修在滁州,寄情山水,沉醉于山林之乐,沉醉于与民同乐,《丰乐亭记》与《醉翁亭记》这两篇游记就像是欧阳修在滁州的见证一样。
这两篇构思奥妙、文风清新自然的幽美散文不仅表示出欧阳修积极有为、乐不雅观旷达的精神,也为后人留下了为之千年传唱的精神宝贝,更为滁州深厚的文化秘闻添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说到欧阳修的滁州之旅,丰乐亭更多地承载了他对滁州的影象,欧阳修不止一次来到这里,寄情山水的同时,也留下了一首首幽美诗歌。
透过这诗情画意的笔墨,我们可以看到欧阳修对滁州的喜好与赞颂。正由于这样,他在离开这片地皮的时候,才会如此的不舍,才会如此的留恋。
冬去春来,又到了游春踏青的时节了,事情之余的欧阳修又一次来到了丰乐亭,这真是一个好去处,俏丽的风光不仅缓解了墨客怠倦的身心,也荡涤了墨客的心灵。
春光妖冶,东风和煦,暖风吹拂着欧阳修的衣袂,墨客惬意十足,当他来到丰乐亭向远处眺望,滁州城尽收眼底。这不禁让他诗兴大发,于是欧阳修持续写下了三首《丰乐亭游春》。
第一首的是墨客寄情山水时的惜春之意,原诗如下:
绿树交加山鸟啼,晴风荡漾落花飞。鸟歌花舞太守醉,嫡酒醒春已归。
绿影婆娑的树木,枝叶连成一片,这茂密的林木,成了鸟儿们的乐园,它们在林间愉快地歌唱。和煦的东风轻轻吹拂着树枝,有一些即将凋零的花瓣,在微风的吹拂下离开花萼,随风飞舞。这宛如图画的幽美风景,墨客徜徉在这撩人的春景中,愉悦的心情溢于言表。
妖冶春光,令民气醉。墨客呢?原来墨客饱览了迷人的春光后,带着无比的惬意,来了一次高兴的丰乐亭宴会,不觉间就进入了醉乡。
诗句流露着墨客寄情山水的乐趣,滁州山川秀美,民风淳厚,欧阳修在这里可以尽享自然之美,欧阳修在《丰乐亭记》中也说:“人生行乐在勉强,有酒莫负琉璃锺。”
越日酒醒,墨客与丰乐亭的春光告别后,悄然踏上了回去的道路。这首诗的末了一句“嫡酒醒春已归”,字面意思是说自己醉了一天,而弦外之音是说自己醉了整整一个春天,墨客用夸年夜的措辞反衬春景的迷人和春日短暂,带有浓厚的惋惜之意。
欧阳修在写给朋友的诗中曾感慨地说到:“滁山不通车,滁水不载舟。舟车路所穷,嗟谁肯来游。”滁州虽然不是繁华的都邑,但由于独特的地理位置,自古有“金陵锁钥、江淮保障”、“形兼吴楚、气越淮扬”的美誉。
这里多情的山水,淳厚的民风,足以抚慰了欧阳修仕途沉浮的心灵,滁州的山水也给欧阳修的创作注入了新的灵感和素材。欧阳修来到滁州的第二年,小麦喜获丰收。在对滁州管理初见成效之后,欧阳修也很欣慰,以是他寄情滁州山水的足迹也多了一份踏实与自傲。
以是第二首诗,写的便是墨客在丰乐亭饮宴的场景,原诗如下:
春云淡淡日辉辉,草惹行襟絮拂衣。行到亭西逢太守,篮舆酩酊插花归。
这首诗的前两句大意是说:天上是淡云朝阳,晴空万里;地上则是春草茂盛,发达成长,碰到了游人的衣襟;而飞舞着的杨花、柳絮悄无声息地洒落在游人的春衣上,这是多么浪漫、多么富于诗意的情景啊。
一个“惹”字写出了春草欣欣向荣之势,春草主动来“惹”人,又表现了春意的撩人;配上一个“拂”字,更真切地描述出了漫无边际的春色。
第三四句写游人兴之所至,来到丰乐亭,在亭西碰上了欧阳太守。太守在干什么呢?他双鬓和衣襟上插满了花卉,坐在竹轿上大醉而归。
篮舆,是竹轿。太守,是欧阳修的自称,汉代时一郡主座被称为太守,唐代称为刺史,宋朝称知州。欧阳修将自己称为太守,是借用汉代的称谓。
他不乘坐官轿,而选择乘坐悠悠晃动、吱嘎作响的竹轿,显示出洒脱不羁的性情。由于坐的是敞篷的竹轿,故而人们得以一睹文章太守的风采。
第三首是一首幽美的抒怀小诗,写的是墨客对春天的眷恋之情,原诗如下:
红树青山日欲斜,长郊草色绿无涯。游人不管春将老,来往亭前踏落花。
正像墨客在《丰乐亭小饮》中写的那样:“造化无情不择物,春色亦到深山中。”青山红树,白日西沉,萋萋碧草,一望无际。天已暮,春将归,然而多情的游客却不管这些,依旧踏着落花,来往于丰乐亭前,欣赏这暮春的美景。
此时的墨客是愉快的,由于他看到自己亲手建造的丰乐亭,成为游人登临丰山远眺滁州风景的立足点,也成为游人栖息的空想场所。
尤其是,每到了春暖花开的时节,前来此处的游人更是相继而来,这很让墨客有造诣感。当然,在春游、踏青的人群中,还有墨客的身影。
丰乐亭周围景致四季皆美,但这三首诗都是剪取了丰乐亭春天的美景加以勾勒、点染、描述的。每首诗的末了一句都因此景抒怀,读来情致缠绵,余音袅袅。
如果结合欧阳修在滁州创作的姊妹篇《醉翁亭记》和《丰乐亭记》的话,再读《丰乐亭游春》的话,那一唱三叹的韵致就更加光鲜了。
无论是欧阳修的《丰乐亭记》、《醉翁亭记》,还是《丰乐亭游春》,都是对滁州山水的赞颂和讴歌,这幽美的诗文早已铭刻在滁州的一山一水中,也成为的滁州山水的人文印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