拐过一个弯,就看到了祠堂。在这个村落里,挂着“刘氏宗祠”牌匾的祠堂,是该地规模最大、用材最讲求、装饰最华美的建筑,但实际上,却由于人工、材料的缺少,更没有手艺博识的匠人锦上添花,此处建筑比其它刘氏族人的房屋,也就只好上那么一点罢了。
此时,在这处隆重庄严的祠堂之内,一名老者正拿着本书摇头晃脑的念着:“。。。。。。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怖乎其所不闻。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
刘悌廉在旁轻声道:“这是为父请来的师长西席,专门教孩童六礼三仪及四经五书。此位张师长西席可敬,去年云游至此,只求有弟子可教,分绝不取。听为父道,张师长西席乃大懦也!
”
穷山恶水的地方,会涌现大懦?李芗泉半信半疑,只是一愣:“何以见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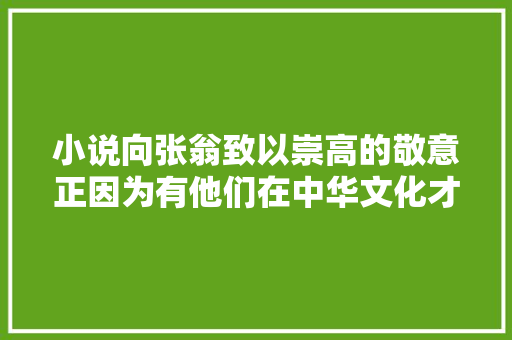
刘悌廉回答:“吾亦不知,听闻张师长西席博览群书,凡事剖析入理颇有见地!
”
李芗泉心中很是迷惑,竟然还有不求钱财、只求教授弟子的师长西席,当现代上,果真有如此人物?放在物欲横流的后世,这是不可思议的,要么被人疑惑此人故意外之心,要么便是小时候发高烧烧坏了脑袋,会被各种喷子的口水淹去世。
那位张师长西席教了几遍后,把稳到李芗泉与刘悌廉二人站在祠堂之外聆听,便交待四五名孩童连续朗诵刚才教过的贤人之章。然后才向李刘二人作揖施礼:“原来是刘少族长来了,这位可是昨晚的那位来客?”
李芗泉尴尬一笑,算是认了,不过昨晚围不雅观自己的村落民中,却未见到此人。在刘悌廉引见之后,他也学着对方的样子容貌向这位师长西席拱手鞠躬:“方才听到书声朗朗,被吸引过来,却打扰先生长西席了。”
那张师长西席戴束发冠、内穿襦裙,外罩对襟衫,约摸五六十岁的年纪,饱经风霜的脸上,写满了忧闷,个中模糊还有诸般无奈的神色,他高下打量一番李芗泉,然后道:“既是贵客,请赐步吃茶。”
李芗泉对这位张师长西席有种一见如故的觉得,也不推辞,跟在张师长西席身后,步入与祠堂一起相隔的住所。刘悌廉告了声罪,没有跟过来,正有模有样的抽查那些孩童的朗诵情形,许是对二人的闲谈不感兴趣。
住所颇为简陋,就堂屋、书房两间房罢了。先生长西席带李芗泉入了个中的书房,说是书房,实在也是这位师长西席的寝室,室内陈设只能用大略二字形容。一张桌子上工工致整的码放着几束书,还有砚台笔墨,两张椅子也规规矩矩的摆在桌前桌后,靠墙处有一张老床,床边的踏板上,放着张师长西席的一双木屐,这一床一桌两把椅子,险些便是室内家具的全部。
张师长西席为李芗泉倒上茶汤:“吾不雅观足下印堂发亮,脸颊红润,气宇轩昂,眉宇间英气逼人,绝非一样平常凡夫俗子!
吾与足下萍水相逢,算是有缘!
”
李芗泉呵呵一声:“师长西席过誉了,不才不过在草莽之中搪塞塞责罢了,区区下里巴人,不敷为道!
敢问师长西席尊讳?”
“山村落野夫罢了,何来尊讳一说,足下称吾山翁便是。山翁今年五十有六,阅尽人间悲欢离合,走遍大好河山,如今老矣,甘为一学堂师长西席,教授二三子,聊以丁宁时日。然足下正当年,当有一番作为,方无悔世间一遭。”
李芗泉只道这位张师长西席称自己是“山翁”,不过是谦逊,他作为晚辈,当然不可能称对方山翁,于是他接话道:“张老,这世间。。。。。。不才却不敢有一番作为。。。。。。”
张山翁哈哈一笑:“时势造英雄也,当是时,须激流勇进!
”
李芗泉无语,初次见面,这位先生长西席就鞭策自己要有一番作为,不知是存了什么心思,难道他逢人如此,要知这神州大地,皆会是蒙元的天下,谁当那出头鸟,只怕是嫌自己活得不耐烦了。
李芗泉岔开话题聊及其它,未料,这位张老,真个博学多才,无论天文地理、农业水利、甚或医术药材、拳理兵法,都通一二,当然,其对孔孟之道、儒家学说更有一番研究。
随着与这位张老聊得越久,两人的话题竟然加倍多了起来,这张老许是很多时日未曾碰着说话如此投契的工具,也是打开了话匣子般滔滔不绝。
他的年事有两个李芗泉不止,但竟也是个脾气中人,譬如其每每吟诵到名家经典的诗词时,每每拍掌而赞,有时念到悲哀处,还会绝不掩饰笼罩的落泪,言语之中,无不流露出对汉家文明的怀念,也让李芗泉无端生出一种亲切的觉得。
过了不知多久,外间的刘悌廉轻轻踱了进来:“特使,时辰不早了。”
这一老一少的二人,才发觉他们这一聊,已过去近两个时辰。那张山翁也有些过意不去,要留二人吃午饭,刘悌廉赶紧一壁向张老告罪改日再来,一壁不由分辨扯着李芗泉便跑。
直到李芗泉被其“拖”出祠堂几十步,刘悌廉这才道歉:“请特使恕岚清无礼,而是张师长西席口粮不多,平日连吃个饱饭都难,但他为人刚直,来刘家村落经年,从未哀求家父多给哪怕半斗米粮,更不多收,且这位张师长西席还会从自己不多的口粮中匀出给孩童,自己或是挖些野菜或下水捕些鱼虾度日,张师长西席,大儒也!
”
李芗泉不由得对张老更高看一层,然后才问:“这里缺粮吗?”
刘慊廉深深叹了口气,但语气武断的道:“很缺,皆是那些鞑子祸害的。。。。。。”
李芗泉彷佛溘然记起什么,返身就往十二姐家跑去。
一脸茫脸的刘悌廉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以为哪里出了岔子,他忽地想起刚才自己在这位特使大人面前表现出的对鞑子的愤慨,贰心里一紧,难道是这的问题?他?不会是鞑子的细作罢,忙三步并作两步跟上。
此时的刘十二姐的院子里,村落里唯一的半吊子木匠挥汗如雨,但他丝毫没顾得上擦上一把,心神专注于架子上的一根木材卯上已有一段韶光了,非得将其刨得方方正正不可。族长说了,要给特使大人做一张好床,平时哪有机会为相公们做木工活,现在这件能让门庭大出异彩的事轮到了自己,木匠自然是放在了心上,全身心都投入到了这项意义非凡的事情当中。
还有几个帮衬的小伙小娘忙里忙外,替李芗泉整顿房间。
内屋,刘十二姐已经换上了另一身蓝布衣裳,此刻的她,正与陈二娘支配特使大人的卧室,三件家具就有两件是族长家搬来的。
“大师付、十二姐、二娘,各位你们好,辛劳你们了!
”李芗泉大步流星的走进来,看着众人都在替他劳碌,心里更有些过意不去,必须好好的偿还他们的美意。
在房里打扫、整理的刘十二姐与陈二娘见李芗泉进来,忙起身道个万福,十二姐更是满脸的羞涩,她低着头手指不断的绞着衣角,彷佛与衣角结下了梁子。
李芗泉的把稳力却不在她们身上,他匆匆拱了拱手,然后奔向自己的背包
他有一袋子的宝贝,当然不是作战的装备,而是红薯,如果没有记错的话,直到明万历年间闽人陈振龙在吕宋进行贸易时,偷运薯藤及栽种之法后传入中国,因红薯对环境的哀求比稻谷低得多,随意马虎栽培。当时正值闽中旱饥,当地试种大有收成,抵谷食之半。
而吕宋的红薯,而是西班牙人从南美带来的。也便是说,在这个西班牙人还没有涌如今东南亚一带的年代,亚洲是没有红薯这个东西的,如要给予时日,自己从苏拉威西岛带来的红薯,一旦大量栽培,足以改进刘家村落村落民粮食紧张的局势。
李芗泉对着上气不接下气的刘悌廉匆匆道:“少族长,请将刘老族长请来,我有要事相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