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过遥长的时空,漫漫黄沙,大水浩荡,蝗虫蔽日,荆榛遍野,虎狼横行,薄弱的先民东躲西藏……这画面颇有灾害片的味道。美国有一部名为《后天》的电影,里面楼坍桥塌,海啸地震,一副天下末日情景;如果上述镜头搬上银幕,大约可以叫《前天》了。《前天》并不比《后天》好过,天下各地遗落的传说里,都能寻到大大水的痕迹,至于其他灾害,想来该当也不会少,不然,在我们的文籍里就不会有这样一首诗了——
土反其宅。
水归其壑。
昆虫勿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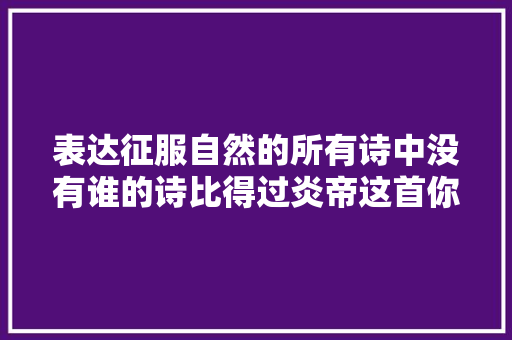
草木归其泽。
初读此诗,我们看到的彷佛是威严的命令,可细细品味,却是无可奈何的乞求。
这首诗名叫《蜡辞》,载于《礼记》,注释说乃伊耆氏所作。伊耆氏即炎帝,又称神农氏。作为炎黄子孙的我们,不知道炎帝那是不可体谅的。神农氏尝遍百草,日中七十二毒,方才有了本日的我们。伟大的炎帝生平都在为其子民驱疠除害,他的这首《蜡辞》也不例外。
劳碌了一年,各种磨难虽然都已过去,但新的一年又会有怎么的命运等着我们呢?于是敬拜成为古人岁末最主要的事情——敬拜百神,感谢他们一年来对农作物的福佑并为来年的丰收祈福。《蜡辞》便是在这种场合下念的祷词。
土,返回到你们原来所在的地方吧(不要流失落)。水,流向你们该去的低洼之地吧(不要泛滥成灾)。昆虫,你们少产点卵,最好不生(你们吃掉了我们多少植物啊)。稗草、荆榛,滚回到沼泽里去吧(不再危害庄稼)。
土、水、昆虫、草木四物,与农业生产至关主要。如果四物泛滥,那先民遭受的灾害便是不可承受的了。他们希望有一种力量能达成自己的心愿,也祈祷众神能因他们的敬拜而帮他们完成这一欲望。
据考证,炎帝之时人类尚处于新器时期,生产力极为低下,面对各种自然磨难,渴望征服的欲念可想而知,可自然力量在当时对付人类险些处于碾压状态,人除了祈祷,能做的真的不多。
关于蜡祭,东汉末年经学大师郑玄在注释《蜡释》时说,“天子大蜡八:先啬一也;司啬二也;农三也;邮表畷四也;猫虎五也;坊六也;水庸七也;昆虫八也。”在这里,除了神农、后稷、地皮之外,路上的标记要祭(邮表畷),连猫和虎也要祭——猫吃老鼠,虎吃野猪,由此推测,当时鼠患、猪患专横獗到了何种程度。“万物有灵”的定命不雅观在那个时候是先民们对天下的一种普遍认识。
在这里,蜡即是腊。当下的我们,进入尾月之后,最主要的一个节日是腊八节。这个腊八节跟上面所说的蜡祭有没有关系呢?该当说我们现在欢度的腊八节,正是上古蜡祭大典的副产品。
据郑玄称,夏代称蜡祭为“嘉平”,商代为“清祀”,周代为“大蜡”。因在十仲春举行,故称该月为尾月,称腊祭这一天为腊日。先秦的腊日定在冬至后的第三个戌日,南北朝时则固定在了尾月初八。
现在的腊八节,在民间敬拜险些已看不到,我们唯一能看到的彷佛只有吃了。
驰名五湖四海的腊八粥,当然是为腊八节量身定做的。最初登场韶光已推延至宋代。到了腊八这天,不论朝廷、官府、寺院还是庶民百姓家都要做腊八粥。到了清朝,喝腊八粥的风尚在民间更是盛行,宫廷里,天子、皇后、皇子等都要向文武大臣、侍从宫女赐腊八粥,并向各个寺院发放米、果等供僧侣食用。
关于腊八粥的做法,不同地区腊八粥的用料虽有不同,但基本上都包括大米、小米、糯米、高粱米、紫米、薏米等谷类,黄豆、红豆、绿豆、芸豆、豇豆等豆类,红枣、花生、莲子、枸杞子、栗子、核桃仁、杏仁、桂圆、葡萄干、白果等干果。腊八粥不仅是季候美食,更是养生佳品,尤其适宜在寒冷的景象里保养脾胃。
网上说还有一个习俗是吃冰。说是腊八前一天,用盆装水让其结冰,等到了腊八节那天,把盆里的冰敲成碎块。说这天的冰很神奇,吃了它在往后一年里不会肚子疼。
南方显然是吃不到这个玩意的,北方到了腊八早冻得瑟瑟颤动,还须要专门冻冰来吃?这显然与上面说的保养脾胃完备不在同一个频道了!
对付这一习俗,本人只能用匪夷所思四字形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