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很早以前的孩子们,常常在一起玩耍。他们唱的童谣都是多少年乃至几代人传唱过的。只管有些粗陋,但我觉得很真实,贴近生活、接地气。
如:
喔喔,觉觉。
小孩睡着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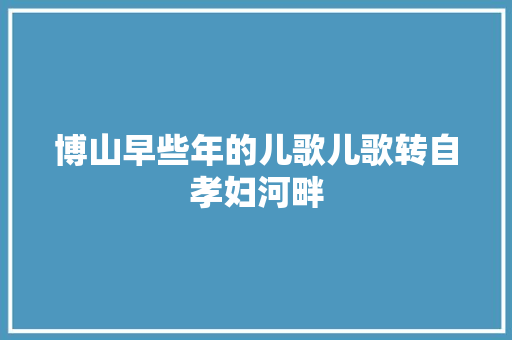
大人利索唠。
小孩醒唠,
大人跳唠井唠。
这是一首大人哄孩子睡觉的摧眠曲,大人一边用手轻轻地拍打着孩子,一边逐步地唱。很老土,但很真实。小孩子便逐步地闭上眼睛,甜甜地睡去。
再如:
小巴狗,戴铃铛,
刚啷刚啷到集上,
买菠菜,买白菜,
刚啷刚啷再回来。
小板橙,巴轱辘,
开开油门看媳妇。
谁来唠,小姑夫,
挎的啥,小马虎。
咬人啊不,不咬人啊,
我看看着来,
___啊呜。
小老鼠,爬灯台。
偷油吃,下不来。
奶奶奶奶抱下来,
猫来唠,
___啊呜。
以上三首,很有想象力,很形象,又顺口,随意马虎记。同时寓教于乐,让孩子们通过传唱,懂得了一些生活的知识,如买菜要到集上、马虎咬人、猫逮老鼠等等。
又如:
南瓜种,嘎蹦蹦,
俺娘不几俺买油灯。
买唠个油灯经薄薄,
俺娘不几俺找婆家。
找唠个婆婆经歪歪,
缒着那辨子打悠千。
小狗汪汪咬,
亲家来要瓢。
今年雨水大,
冲唠葫芦架。
你说俺待几你啥?
泔水瓮里有个瓢碴碴,
刷把刷把几你罢。
鸡勾勾,打鸣唠,
爷爷起来喂牛唠。
奶奶起来缝衣上,
一缝缝唠那牛比上。
以上三首恢谐、诙谐、给人以想象力。同时又顺口、好记,随意马虎传唱,启示孩子们的学习兴趣。
2、还在操持生养以前的时候,屯子人家孩子多,一家五六个孩子很正常,多的兄弟姊妹八九个、十几个的也有。大人们忙不过来,就大的看小的。一个大孩子领着几个小孩子再抱着一个更小的孩子的比比皆是。但那时的孩子们很康健,光着露着土里水里长年累月很少有人感冒发热。一点也没有现在孩子们那么娇气。当然由于性情不同,有的孩子天生爱哭,又粘,哭起来成半天不住声。于是大人们又教了新的童谣:
叫喊将,啃屎棒。
人家不叫啃,
扒下就打滾。
打唠一后晌,
挣唠碗豆汤。
又待喝又待养活。
端到门士欠(门坎),
桶唠一多数。(桶:泼洒的意思)
端到天井,
桶唠个干净。
孩子们唱着跳着,哭者也破啼为笑,流出的鼻涕立时吹起了一个大泡泡,于是大家都来看吹铃铛,便笑得更欢了。
其余一首哄孩子的童谣,大人或是大一点的孩子,面对面地拉着小一点孩子的双手,前后摇着,一边摇一边唱:
罗罗,面面,
请唠小孩来用饭饭。
啥饭?炒杂面,
谁赶嗯,老红眼。
谁烧火,秃老婆,
咋着烧,不拉着。
谁推磨,豆虫,
咋着走,顾拥。
谁打水,蚂蚱,
咋着走,跳哒,
打唠罐噢吊杀。
这首童谣极具戏剧性,把赶面、烧火、推磨、打水这些屯子家庭中的活路淋漓至尽地用老红眼、秃老婆、豆虫、蚂炸等非常形象地表现出来,给人以热火朝天地忙着而又快乐着的想象,如临其境。活脱脱便是一个童话剧本,让孩子们一边唱着一边增加着生活的知识。
还有一首是大一点的孩子们唱的,这时候的孩子们心眼多起来,知道调皮了。人们说:七岁八岁狗也嫌,一点不假。
童谣是:
xxx,不大高,
一屁呲到柳树稍。
柳树稍上一领席,
一屁呲到八陡集。
八陡集上放爆丈,
一屁此到南庙上。
南庙上,吹喇叭,
一屁呲到老马家。
老马家,出豆腐,
一屁呲到锅背面。
锅背面,冒点烟,
一屁呲到场院边。
场院边上一口井,
一屁呲木唠影。
……
这首童谣稍显粗俗,具有一定的调侃性、故事性,也有一定的寻衅性。由于前边的xxx可以随便冠以一个人名,那么就唱谁是谁了。那时候街上孩子们多,成群结队,一旦有一个领头唱起来,一呼百应一哄而起,不管是赤着脚的光着腚的都_会拥过来使动地唱,大有不可阻挡之势。有时候也唱大人,跟在大人后边唱,直到唱的大人沉不住气了,回过分来跑几步,伪装要打人,孩子们才哄地一下跑散开来。
3、那个年代的童谣,基本没有政治色彩,只有浓厚的生活气息。
如:
小家雀,过河崖,
淹唠衬噢淹劳鞋。
过去河崖一口屋,
一个小孩在那哭。
小孩小孩你哭啥?
俺娘不给俺找媳妇。
邦邦邦,卖豆腐,
一卖卖到山背面。
山背面,有块谷,
两个斑鸠咕咕咕。
金银花,一古查,
俺娘生唠俺姊妹仨。
大姐待家出豆腐,
二姐出来去卖渣。
便是三姐不会干,
撵唠坡一逮蚂蚱。
逮唠仨,蹦唠俩,
剩下一个扔唠它,
你说气煞不气煞。
当然,童谣中也有神往美好生活,憧景美好未来的。
咣咣嚓,砰砰嚓,
打小俺随着佬外家。
佬娘给俺好饭吃,
妗由给俺好粉搽。
等到俺长到十七八,
俺舅给俺找婆家。
大车拉庄稼,
小车轧棉花。
恣的俺心里乐开唠花。
花椒树,探连枝,
树底下一个大闺女。
大闺女,俊又巧,
两把剪子一起绞。
左手铰出了牡丹花,
右手铰的是灵芝草。
当然,也有戳穿丑恶征象,勾引儿童向孝、向善、向真、向美。从幼小的心灵就善恶有辨、爱憎分明的潜移默化教诲。
长衣巴狼,衣巴长,
娶唠媳妇忘唠娘。
把他娘来背唠山坡哎,
把他媳妇背唠炕头上。
赶油饼,烧辣汤,
不吃不吃烧上喷鼻香。
看你饿不饿的慌。
4、大部分在民间传唱的童谣每每带有故事性,启示性,相对长一点,大都在四句以上。也有的童谣很短,也就一两句话,但它能合营上一些大略的演出动作。比如春天挖苗子的时候,妈妈们每每带上小鸡上坡,孩子们是少不了的。一下子老鹰飞来了,孩子们便把小鸡拿得手里,高兴地仰着头唱:
老雕老雕你转转,
给你个小鸡你看看。
……
春天到山上挖梨梨嘴,也是一边唱一边挖:
梨梨嘴,跑山腿,
你不跟我你跟谁?
……
有时候在草毯里,路边上见了示示虫,是绝不能让它跑掉的,用手轻轻地按住唱道:
示示虫,示示虫,
你不拉屎害腚疼。
……
果真示示虫就拉屎了,这时轻轻地放开手,示示虫便悠哉悠哉地爬走了。挖丁当也有唱:
丁当丁当开门,
大一领着个小人。
……
一边唱一边挖,一下子丁当果真就出来了。然后把它放掉,让它重新钻进沙里,于是再唱再挖……
找一堆湿乎乎的土或沙,把一只手埋到里边,另一只手在上边瓜打,一边瓜打一边唱:
瓜打瓜打燕噢窝,
我给燕噢打唠砂锅,
燕噢来家不愿意我,
我给燕噢对起来,
燕噢来家夸把我。
然后逐步地抽出埋在里边的那只手,一个俊秀的燕窝就造出来了。其余如藏猫猫歌:
指、星、过、月,
点、点、捏、捏。
不朝南,不朝北,
逮住小狗捂到黑。
藏好唠姆?
藏好兰!
山麦仁:
山,山,山麦仁,
麦仁着花结石榴。
石榴皮,我吃唠,
石榴籽,我卖唠,
丁当丁当花盖噢。
你要胭脂我要粉,
咱俩打个琉璃滚。
这样的童谣是带演出的,就有了一些艺术性了。这里不旦旦是唱,同时也让孩子们动了起来。
有的童谣,每每好几个版本,一个地的人和另一地的人唱出来就不一样。如两个版本的嘎啦秧:
(一)
东嘎啦秧,西嘎啦秧,
谁家那小狗喝了俺那喂狗汤。
老狗老狗你别咬,
再咬我给你一担杖。
……
(二)
东嘎啦秧,西嘎啦秧,
一布袋米,一布袋糠,
一撒撒到那王家庄。
大娘哎,俺来抱小狗啊,
小狗待那干草垛上晒洋洋。
你去选办
噢
选花一,选绿一,
一选选唠个放屁一。
5、在那个年代里,孩子们虽然没有现在这么多当代化的玩意儿,却总是满满的幸福感。高枕而卧无拘无束,天性的开释和快乐的纯洁便是孩子们幸福的童年。虽然物质生活无法和现在比较,但他们走一走跳三跳,歌不离口,幸福着快乐着。
忽然想起做了这样一个专题,引起了许多朋友们的关注,有的写评论,有的发感慨,沉浸在那少年时期美好的回顾中,还有的和我回味、磋商那些早些年的童谣,在这里一并表示衷心地感谢。同时还要深深地感谢郑贵尧老师,由于文中部分童谣是由他搜集整理供应的。
想想那时候的孩子们,不但童谣多的唱不完,便是上学往后课外活动也非常丰富。比如男孩子们打蛋(玻璃球)、打住(线团行头)、打瓦、打王八、滚铁环、打
后来,那些过去的童谣逐渐没有人唱了,新的童谣又盛行不起来,于是盛行的童谣彷佛有点断档。有一首童谣在我的影象中,孩子们彷佛唱了几十年,大概现在还有喝的:
大苹果,圆又圆,
姨妈带我上公园。
我不哭,我不闹,
姨妈夸我妈宝宝。
能盛行那么多年,该当便是好童谣了。但我每当听到孩子们唱这首童谣,心中总会有一种压抑感、强制感,有点透不过气来。我不哭我不闹是为了得到姨妈的称颂?那么受了委曲呢?也不哭吗?如果哭了是不是就要得到姨妈的批评?以是不敢哭?哭和闹是孩子的天性,也可以说是他们对付大人的一种拿手和武器,不敢哭不敢闹的孩子,心里会承受多少委曲,乃至很多大人(包括家长和老师)有时候都不会理解。
就到这里了,末了以几首童谣作为结束吧:
老南瓜,面墩墎,
俺上佬外家住一春。
佬娘给俺好饭吃,
妗由给俺白不眼(瞅人)。
妗由妗由你白瞅,
麦由黄稍俺就走。
宝谷宝谷,找找小姑,
小姑来唠,麦由熟唠。
宝谷宝谷,你待哪屋,
我待山后,住唠瓦屋。
山后吃啥?
黄瓜炒肉。
刮大风,搂豆叶,
一搂搂唠个花大姐。
花大姐,拾棉花,
一拾拾唠个大甜瓜。
俺娘就说割著吃,
俺爹就说到年下,
馋的俺小嘴直吧嗒。
青青菜,嘎哒油,
小两口睡觉待一头。
枕着花斗枕,
摸着光油头,
你说恣悠不恣悠
恣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