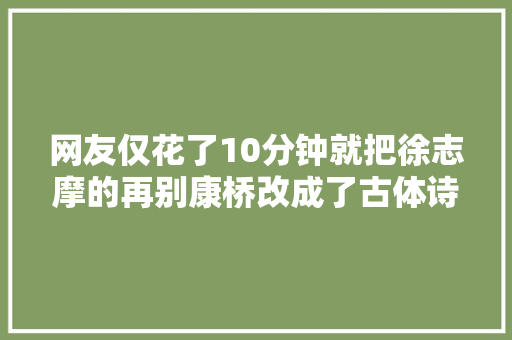笔者还记得当年上小学时,最爱跟同学们改写孟浩然的《春晓》。那时候,语文老师看着“春眠不觉晓,处处蚊子咬”时,硬是不知说什么好。
后来上初中了,就开始改写刘禹锡的《陋室铭》,苏轼的《水调歌头》等更高等的作品了。到这个年纪时,改写的水平自然要稍高一些了,虽然紧张还是图一乐,但总归是说出了自己的真情实感。比如下面这首学生版的《水调歌头》,当年就曾让很多同学捧腹:
《水调歌头.假日几时有》(学生版)
假日几时有,把笔问上苍。不知假日当中,作文有几篇。我欲偷工减料,又恐老师白眼,作业不胜烦。起早贪黑写,好似在研讨。背英语,做数学,夜难眠。不应有偏,为何总是感到难?人有高矮胖瘦,学有高低深浅,此事两难全。但愿假日多,作业能锐减。
毕业后,笔者才创造,原来还有大量和我们一样爱改写名作的诗迷朋友。对他们来说,改写并非不尊重原作者,而是一种致敬,抒写的是对诗歌的热爱。最开始,这些“改写爱好者”是改一改唐诗、宋词,当这些也改写得差不多后,他们开始改写当代诗,也终于对《再别康桥》“下手”了。
咱们都知道,《再别康桥》是徐志摩最经典的作品,属于如今的当代墨客难以企及的。虽然“轻轻的我走了,正如我轻轻的来”,字面上看起来很大略,但不得不说这些字组合在一起,确实很美。
不过有诗迷却表示:“我花10分钟就能把它改写一首古体诗”。说实话,最开始看到有人这样说,笔者还真不敢信。但后来看了看他的大作,却又不得不感叹:够牛。我们来鉴赏一二:
康桥一去是经年,难忘清音榆下谭。
艳影金波聆旧梦,软泥青荇唤新颜。
达摩纸上无笔墨,海谷诗中有彩笺。
寂寞笙箫何处诉,星船满载是斑斓。
正直直正的56字古体诗。虽然从格律上来说,算不上是十分工致的七律,但这位诗迷的整体水平却不容小觑。
首句“康桥一去是经年”下笔就非凡,一股浓浓的文艺青年气质迎面而来,还真有点儿徐志摩的调调。第二句引入榆树的意象,“清音”二字用得淡雅、清丽。这样的开头是有一定水平的,看得出来这位诗迷是懂古体诗的。
第三句和第四句,为了追求字句对偶上的工致,刻意用“聆旧梦”对“唤新颜”,用“艳影金波”对“软泥青荇”。这几个意象,都是原诗里用到了的,他只是把构造和诗风改了一下。遗憾的是这种对偶仅限于字面,并没有完备考虑到意境的布局,失落了一些些美感。
第五句和第六句,是诗迷自己加入的意象。把原诗淡淡的忧伤,写得更为直白了。末了的落笔,“星船满载”该当是全诗最美的意象了,这一句改的是徐志摩的原句“在星辉斑斓里放歌”。实在徐志摩这句诗之以是能这么美,本身便是化用了元末墨客唐珙的“满船清梦压星河”,可见古体诗和当代诗在意象上是能相通化用的,不同的只是措辞风格。
纵不雅观这首七言诗,显然是无法与原诗相媲美的。但它的创作过程毕竟只有10分钟而已,能即兴写到这个程度确实已经不随意马虎了。此诗的优点在于,保留了原诗的韵味,写出了古体诗的觉得。缺陷则在于,明显存在口语文和文言文杂糅的问题,读来无法做到如唐诗名作一样平常朗朗上口。
实在对《再别康桥》这首诗,还有很多诗迷改写过,七绝、五律、七律都有。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把这些作品找来读一读。大家认为此诗写得如何?欢迎谈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