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时候,相真切农氏尝百草时,创造漫山遍野成长着一种奇树,一棵棵枝杈旁逸斜出、怪刺丛生,结出一串串圆形的小果,红艳鲜亮,喷鼻香气四溢。他随手摘了一粒红果丢进嘴里,喷鼻香麻之味弥漫开来,向喉咙窜去,直达肺腑,顿觉脾胃发热,遍身轻惬。神农氏连连称道:“这确是难得的‘宝树’,还应是一种能医病的良药啊!
”随说出“宝树”独特之处,即为“叶青、花黄、果红、膜白、籽黑,禀五行之精”。
神农氏所赞的奇树、宝树便是花椒树,其成熟的红果便是花椒。农谚云:“立秋摘花椒,白露打核桃。”每到秋日,家乡漫山遍野的花椒成熟了,但见棘刺丛生的花椒树上,缀满了红艳艳的花椒果儿,远了望去分外刺目耀眼,成为故乡秋日一道亮丽的风景。
花椒是我国特有的喷鼻香料,自古就与茴喷鼻香、大料、桂皮、丁喷鼻香并列“五喷鼻香”,且居首位,亦位列现今的调料“十三喷鼻香”之首。它有浓郁的喷鼻香气,特殊的麻喷鼻香,是中富丽食烹饪中一个不可或缺而且很常见的调味剂,它存在于每个家庭的厨房里,是厨房里的神奇邪术师。它能除腥提鲜添喷鼻香,那缕缕浓喷鼻香、丝丝麻辣,令很多人迷恋,品之不尽。
花椒不仅被作为紧张的调味品食用,还是常用的中药材。它味辛、性热,归脾、胃、肾经,有芳香健胃、温中散寒、除湿止痛、杀虫解毒、止痒解腥之功效。早在汉代已有药用的记载,成都老官山汉墓医简《六十病方》中,有花椒入药治痛风的记载。最早的药物学专著《神农本草经》,也将花椒列为上品,言其“主风邪气、温中、除寒痹、坚齿、明目”。汉代名医张仲景在《金匮要略》中,就有用花椒治寒痛和饮食不振的记载,最具代表性的药方是“大建中汤”,其歌诀云:“大建中汤建中阳,蜀椒干姜参饴糖,阴盛阳虚腹冷痛,温补中焦止痛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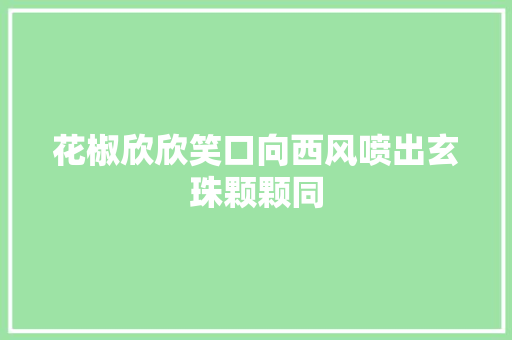
花椒不仅仅作为调味品和药用,它还代表古老的“椒文化”。《诗经》和《楚辞》多处提到“椒”,并授予它独特的文化内涵。《国风·陈风·东门之枌》有云:“视尔如荍,贻我握椒。”意思是:我看你像荞麦花一样俏丽,你就高兴地送我一把花椒。这首诗表达的是青年男女相互慕悦,选择良辰吉日,载歌载舞,赠予礼物的情景。花椒多子,喷鼻香气浓郁,先秦时男女青年选择花椒作为定情物,表达婚后“多子多福”的美好欲望。
这种以“花椒多子”为比兴的手腕,在《唐风·椒聊》中表现得更为详确:
椒聊之实,蕃衍盈升。彼其之子,硕大无朋。
椒聊且,远条且。椒聊之实,蕃衍盈匊。
彼其之子,硕大且笃。椒聊且,远条且。
这是一首女子采椒之歌,赞颂花椒枝繁叶茂,硕果累累,喷鼻香气远播,以椒喻人,赞颂那个高大健壮的心仪之人,人丁茂盛,子子孙孙像花椒树上结满的果实,繁盛累累。
在《楚辞》里,花椒被看做名贵的薰身喷鼻香料,作为“忠贞良善”的化身。屈原在《离骚》中吟唱:
昔三后之纯粹兮,固众芳之所在。
杂申椒与菌桂兮,岂维纫夫蕙茝!
意思是说:当初禹、汤和文王的品行多么完美,所有的芳香都簇拥在他们周围。特殊是花椒与桂树杂陈其间,怎能只有兰蕙与芷草结伴相随?
户服艾以盈要兮,谓幽兰其不可佩。
览察草木其犹未得兮,岂珵美之能当?
苏粪壤以充帏兮,谓申椒其不芳。
那些辨不出善恶的人把艾蒿挂满腰间,却要说幽兰不能佩在身边。他们连喷鼻香花恶草都不会鉴别,更何况在真正的美玉面前?他们用粪土充当帷幕上的流苏,却要说花椒的味道不足喷鼻香艳!
在《九歌·湘夫人》里,“椒”更是独特的美物:
筑室兮水中,葺之兮荷盖。
荪壁兮紫坛,掬芳椒兮成堂。
意思是说:在水中修建一座宫室,用荷叶来覆盖装潢,用紫贝做坛喷鼻香荪涂墙,还要捧一把椒粉撒满厅堂。可见,花椒以暗喻、借喻等手腕,被授予了多么美好的形象啊!
在古代宫廷,还有用花椒掺入涂料装饰的屋子,称为椒房、椒宫,是给皇后嫔妃居住的。如班固《西都赋》有“后宫则有掖庭椒房,后妃之室”的句子;白居易《长恨歌》也写到“椒房阿监青娥老”;最著名的则是汉未央宫椒房,为汉代皇后居住的宫殿。古代帝王认为,后妃居住在这样的屋子里,一来可以辟邪除崇,二来是除湿驱寒保温,而紧张的意义在于,花椒籽粒繁多且生命顽强,以其寓意帝王之家人丁茂盛、生生不息。
花椒涂抹成“椒房”,也仅是王公大臣、豪绅富贵之家,平民百姓是用不起的。唐末墨客张孜耽酒如狂,诗风随意率性不羁,《全唐诗》仅存其《雪诗》,个中有句:
长安大雪天,鸟雀难相觅。
个中豪贵家,捣椒泥四壁。
饱含讥讽之意。
宋代理学家刘子翚写有一首《花椒》,写出了花椒的美艳喷鼻香馥和实用之妙,诗云:
欣欣笑口向西风,喷出玄珠颗颗同。
采处倒含秋露白,晒时娇映夕阳红。
调浆美著骚经上,涂壁喷鼻香凝汉殿中。
鼎餗也应加此味,奠教姜桂独成功。
上半首描述花椒的娇艳玲珑之态,采收晾晒时红艳映日之景;下半首是赞颂花椒的实用代价,既可涂在皇室后宫的壁上作为暖房,又能祛荤腥、调百味,堪与生姜、肉桂等调料媲美。
明代名臣于谦作有《拟吴侬曲》,个中一首是这样写的:
忆郎忆得骨如柴,夜夜望郎郎不来。
乍吃黄连心自苦,花椒麻住口难开。
这应是一首情诗,那种相思之状如黄连之苦、似花椒之麻,没有切身之感是体会不出的。不过,我倒是喜好花椒那种麻喷鼻香之味的,那芳香那酥麻,在舌尖上萦绕,在齿颊间荡漾,使得五味调和得法,相得益彰,美哉妙哉!
-作者-
刘琪瑞,男,山东郯城人,一位资深文学爱好者,出版散文集《那年的歌声》《乡愁是弯蓝玉轮》和小小说集《河东河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