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一
白日不到处,青春恰自来。
苔花如米小,也学牡丹开。
其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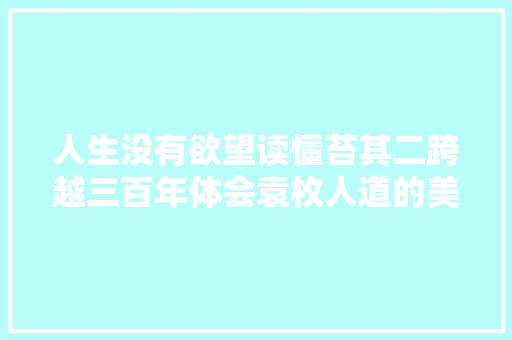
各有心情在,随渠爱暖凉。
青苔问红叶,何物是斜阳。
白日不到处,青春恰自来。 苔花如米小,也学牡丹开。
如果其一是表达的是对平凡人生的歌颂和赞颂,那么其二便是对平凡人生的理解和对环境的无可奈何的感慨。
各有心情在各有各的环境和在各种环境下的心情。
一个人生下来,或富有或贫穷,这个不是由自己决定的,因此,人生下来的出发点就不一样。有的人还在山脚下,而有的人却早已经爬到了半山坡或到了山顶。那么,山脚下和半山坡以及山顶上的人的心情是不一样的。
山脚下的人,如果没有梦想,大概一辈子都会在山脚下,能够上半山坡或是山顶上的人也是寥寥可数。半山坡的人,同样如此,如果他足够努力,那么他爬到山顶的可能性比较大。当然,这些每每由于压力不大,掉到山脚下的可能性则是非常大。还有比较少的便是那些山顶上的人,这些出生即是大富大贵,这类人对生存根本没有什么观点。
那么这三类人,由于生活的条件不一样,心情怎么会一样呢?而苔便是属于在山脚下的那类人,袁枚便是怜悯那些一出生就处于山脚下的那些人。
不满石头的苔藓,可见苔藓的生命力之顽强
随渠爱暖凉喜好温暖还是风凉,该当随他自由选择。
第二句话锋一转,喜好温暖还是风凉,该当由他自己选择,可是,当时的社会环境怎么可能许可你有自己的选择的权利呢,自由选择的想法只不过是他一厢宁愿的想法罢了。这也表明了袁枚想对命运抗争却又无能为力。无法改变就选择躲避,我想这便是他为何34岁就隐退随园的根本缘故原由吧。
“谈山林之乐者,未必真得山林之趣。厌名利之谈者,未必尽忘名利之情。”那些好评论辩论山居生活之乐的人,未必真的领悟到了山林生活的乐趣;嘴上说讨厌名利的人,未必真的忘得了名利。
经历了十年的官场,袁枚彻底明白了这个道理,话不多说,直接放弃统统,这些袁枚做到了,成了一名真正意义上的隐士。
成长在树木上的苔藓,与树木争夺营养
青苔问红叶,何物是夕阳青苔问询红叶,夕阳是什么样子的呢。
有些青苔从来没有领略过夕阳的艳丽,因此问从高处跌落到惨淡的地方的红叶,夕阳到底是个什么样子的呢?
此时,联系前面两句再来看一遍,由于阳光的偏爱,青苔红叶各有暖凉不同的境遇,在不同的位置,青苔和红叶各有自己不同的心情。于是青苔卑微地向红叶发出了什么是“斜阳”啊的疑问?
袁枚直接表达出阳光不能做到“普照万物”的责怪,更多的是对当时社会的不满与无奈。诗中青苔那怯怯而又执着神往的神色跃然纸上,读后让令人悯然。
在那个专制的封建专制的时期,袁枚笔下的青苔,它有对付阳光的期待,有对冷暖的自知,也有向红叶打听作甚阳光的勇气。它越是执着、越是努力地绽放自己的青春,证明自己的存在,实际上就反衬出它周围环境的恶劣。
在当时的社会环境,无论周围的环境多么的恶劣,袁枚都无法很直白的控诉社会的阴郁,因此,他通过一种成长在惨淡角落里最卑微的植物--苔,来表现自己内心的对付人生下来就不公正的训斥。就像曹雪芹的《红楼梦》一样,只能通过一个神话传说女娲补天落入世间的一块石头说事,并且取名《石头记》一样,他无法摆脱环境的束缚,但是也无计可施,退隐山林就成了袁枚的唯一选择。
深山老林里,成长在树上的苔藓
我的青春我能否做主?袁枚的《苔》,大概把其一和其二如果放在一起成诗会更有味道,更能显示出袁枚归隐前后内心的挣扎的无奈。
其一可以理解成早期的虽然成长在不被人把稳的地方,但是我的青春我做主,虽然自己的能力有限,但是依然会不遗余力,那时候的他是有梦想的;
其二是为官一段韶光,终于明白环境对一个人的影响有多大,他想要见到阳光,须要一个平等的天下,于是用了一个反问句,由于他知道这个问题没有答案,这时候他的梦想随之破灭了。
梦想破灭了往后,他直到他的青春他自己做不了主,于是趁着父丧养母的机会,归隐于随园!
南京师范大学随园校区,便是基于随园改建而成
后记袁枚对付这个发奋图强的小小生命的尊敬,实际上便是为了更好地表达对付社会环境不公的训斥,这种不雅观念或许是源于他主见诗文审美创作该当抒写性灵,要写出墨客的个性,表现其个人生活遭际中的真情实感。他通过对顽强成长的苔的同情和怜悯,向众人展示出了人性中最美好的一壁!
生活不快意?读读袁枚的这首诗,《苔》见告你怎么才能沉着地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