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海内现存最长木拱廊桥——福建万安桥突发大火,毁于一旦,令人不禁扼腕嗟叹。作为水路和陆路的主要交通办法,桥自从被创造以来,便一贯发挥着此岸到彼岸、此山到他山的实际功效。而在情怀浪漫且富有创造力的古代文人眼中,桥却有着更深层次的意义——连接民气,沟通古今。在一个清风摇翠的夏日,笔者翻开尘封的书页,踏上了古人走过的桥。
长安灞桥:
灞桥烟柳知何限,谁念行人寄一枝
自古东出长安,过了灞桥便是中原的地界了。千百年来,经由此地的贩夫走卒、客路之人、戍边将士不计其数,在或太平或离乱的时期中不断奔忙,他们在灞水波澜不惊中告别,在灞桥之上伫立回望。与此同时,深奥深厚的离愁别绪也在酝酿,在发酵,终极从人类精神的高地喷薄而出,于是,一首首光耀千古的名篇出身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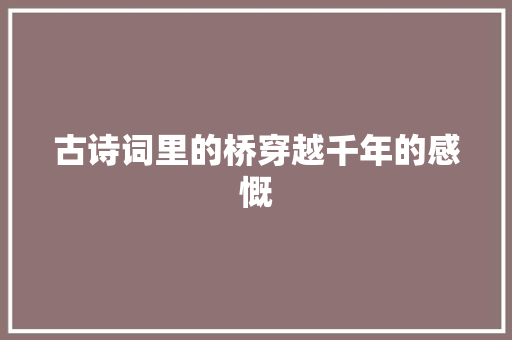
据《三辅黄图》记载:“灞桥在长安东,跨水作桥。汉人送客至此桥,折柳赠别。”纵然洒脱如李白,在听闻洞箫呜咽之后,笔墨也不免感伤,于是写下了“年年柳色,灞陵伤别”的诗句。还有被后人称作“诗豪”的刘禹锡,在面对灞桥的时候,彷佛也失落了几离开朗之气,他笔端流淌的“征徒出灞涘,回顾伤如何”,乃至比李白更哀婉伤情,远行之人不忍卒读,却已潸然泪下。
“杨柳含烟灞岸春,年年攀折为行人”。灞陵桥和灞桥柳,这两个意象共存共生,相依相偎,极大地丰富了国人表情达意的情绪载体,折柳相送由此变成了诉说挽留之情和祝福之意最浪漫最诗意的办法。而灞桥也在文人的不雅观照下,打破了物质与时空,终极演化成文学天下里一座生生不息的“情尽桥”和“断肠桥”。
扬州二十四桥:
天涯回顾一销魂,二十四桥歌舞地
淮左名都是扬州,竹西佳处亦是扬州。孟浩然在烟花三月的残酷时节,一边吟咏着“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一边荡漾扁舟,顺长江而下。唐人张祜初到扬州,便已斟酌好了身后之事,竟发出了“人生只合扬州去世,禅智山光好墓田”的感慨,其实让人凄恻动容。
二十四桥在扬州。关于二十四桥到底是一座桥还是二十四座桥的浪漫辩论,至今未休。数不清的学者、道不尽的缘由,实在并不妨碍一代又一代的文人们在此地挥毫泼墨。在扬州浩瀚拥趸之中,俊彦者当为唐人杜牧。杜牧家世显赫,加之少年景名,故而颇好结交游宴,时常放浪形骸。某个月明星稀的夜晚,他借着几分醉意,把心绪糅进月光,写下了“二十四桥明月夜,美男何处教吹箫”。从此往后,二十四桥便走进了文学的地界,文人雅士纷纭留下墨宝,贺铸吟道,“二十四桥游冶处,留连”;王奕带着仇恨与不甘写下了相见恨晚的落寞——“二十四桥明月好,晚年方到扬州”。
遥想当年,白石老人姜夔途经扬州,看到曾经被杜牧深情以歌的好山水,如今却因频年战乱而冷落凋敝,不觉心生凄凉,化而为词,个中有言曰:“杜郎俊赏,算而今重到须惊。纵豆蔻词工,青楼梦好,难赋深情。二十四桥仍在,波心荡,冷月无声。念桥边红药,年年知为谁生?”
成都万里桥:
雕鞍送客双流驿,银烛看花万里桥
三国期间,诸葛亮饯别即将出使东吴的费祎,费祎感叹,“万里之行,始于此桥”,万里桥由此出身。可以说,正是由于天府之国的富庶与周遭景致的美好,使得历代文民气神往之,故而反复吟咏玩味,作品不可尽数。
安史之乱后,诗圣杜甫拖着“百年多病”的身体,扶老携幼,一起流寓西南,至成都,便在万里桥西、浣花溪边搭建茅屋。少焉的安逸宁静,使杜甫一改“沉郁抑扬”的诗风,深情款款地写下了“万里桥西一草堂,百花潭水即沧浪”“西山白雪三城戍,南浦清江万里桥”等清新明快的诗歌。正所谓“国家不幸诗家幸”,生平流落、了无所依的墨客,在山明水秀的锦官城得到了人生中屈指可数的安宁与抚慰。
唐人王建一首《寄蜀中薛涛校书》,“万里桥边女校书,琵琶花里闭门居。扫眉才子知多少,管领东风总不如”,让薛涛名噪一时,赢得了“扫眉才子”的美誉,却未曾想到,这也给她孤独终老的后半生埋下了伏笔。深居浣花溪、手制小彩笺的薛涛直到生命的末了一刻,终是没有等来那个对她说过“别后相思隔烟水,菖蒲花发五云高”的游荡公子元稹。万里桥究竟成了薛涛生命中的伤心地和离恨天。诚如元杂剧所言:“三十三层天,离恨天最高;四百四十病,相思病最苦。”
南京朱雀桥:
我欲去寻朱雀桥,淡烟落日风萧萧
光阴流转,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依然未改旧时波;风吹雨打,静默不语的朱雀桥早已洞悉世事沧桑。那些波诡云谲的风云,金戈铁马的岁月,以及悼感怀伤时的愁思,被定格在秦淮河和朱雀桥不悲不喜的光阴里。
刘禹锡在历经人间波折、遭受政敌排挤的愤慨中,悲愤写下了流传千古的诗句:“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平凡百姓家”,字里行间满含忧国忧民的大情怀、大格调。宋室南渡后,词人朱敦儒在登临凭吊时,但见“朱雀桥边晚市,石头城下新秋”,忽觉心内模糊作痛,只一瞬便化为“前人何在,凄凉故国,寂寞潮头”的感喟与哀思。“元曲四大家”之一的白朴,在金陵城下、朱雀桥边,忽然忆起六朝繁华旧梦,感叹道:“朱雀桥边野草,白鹭洲边江水,遗恨几时终”;清人纪昀在《阅微草堂条记》中写下的“六朝燕子年年来,朱雀桥圮花不开。未须惆怅问王谢,刘郎一去何曾回?”更将那种“物是人非事事休”的落寞表达得淋漓尽致、哀婉久绝。
当然,曾经在文学的天空中别离过、悲戚过的桥,远远不止于此。还有在一千多年前某个“月落乌啼霜满天”的夜晚,张继夜泊后,方才闪耀在文学国度里的枫桥。因轰轰烈烈的爱情而被人们熟知的断桥、鹊桥和蓝桥,以及晏几道笔下那座只存在于精神层面的谢桥,它们共同支撑着、扶持着,托举起了古代文学的一座又一座高峰。
就在这个烽烟散尽的夏日,我随着古人行色匆匆的脚步,与他们一道读了桥,也读懂了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