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星陪伴(xinghuivip)
是周代在齐国京都地区(今山东省淄博市临淄)广为流传的一首民歌,它描写了在奴隶主的残酷剥削和压榨下,奴隶们被强礼服苦役的痛楚生活,戳穿了当时社会的阶级抵牾和统治阶级的残暴,诉说了奴隶们受压榨的痛楚,反响了奴隶阶级的怨恨和反抗心声。
《齐风》,《诗经》十五国风之一。为先秦时期齐国地方民歌,共十一篇。半数以上是关于婚娶和爱情的诗,别的几首或是反响公民对沉重劳役的不满;或是戳穿齐襄公与其妹文姜通奸的丑行;或是描写野猎和射技等。“齐风”除少数讽刺齐襄公的诗可知作于公元前六九七——前六八三年之间,别的的诗年代多不可考。《诗经》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部诗歌总集。对后代诗歌发展有深远的影响,成为中国古典文学现实主义传统的源头。
齐,本是西周初姜尚的封国,后又吞并些小国,是春秋期间的一等大国,其领土大致包括今山东的昌潍、临沂、惠民,德州、泰安等地区以及河北沧州地区的南部。“齐风”便是这个区域的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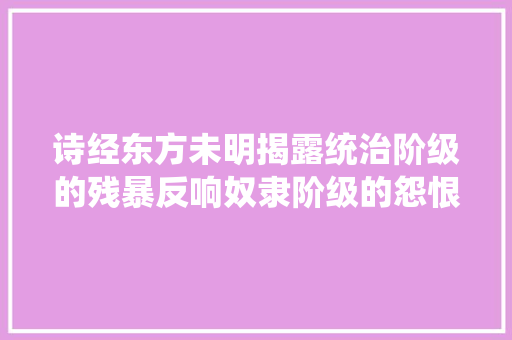
齐国地大物博,盛产鱼、盐,纺织、刺绣等手工业很发达,人口分布也较他国稠密。自太公姜尚历十五世,至齐桓公时(前六八五年登基),称霸于天下。其后再传十四世,政权落入新贵田氏手里,仍号为齐国。
在“齐风”中半数以上也是关于婚娶和爱情的诗,别的几首或是反响公民对沉重劳役的不满;或是戳穿齐襄公与其妹文姜通奸的丑行;或是描写野猎和射技等。
“齐风”除少数讽刺齐襄公的诗可知作于公元前六九七——前六八三年之间,别的的诗年代多不可考。
言及“齐风”,一样平常与齐俗并提,称为“齐风齐俗”。单提“齐风”每每令人不知以是然,乃至会发生歧义。由于《诗经》中也有《齐风》。齐风和《齐风》是两个不同的观点。《诗经·国风》中的《齐风》是齐国的民歌。宋代学者朱熹在《诗经传·国风序》中说:“风者,民俗歌谣之诗也。”《诗经》中的“风”,又称“国风”,即指当时诸侯国所辖各地域的乐曲,实际上也便是指相对付当时周天子的京都而言的遍地所的土乐,犹如我们现今所说的地方俗曲,各地的地方小调。《诗经》中共有十五国风,《齐风》是个中之一,共有十一篇。
当代汉语词典,对“风”字的阐明有多种意义,个中之一义,“风”即指风尚,风气。唐人孔颖达疏“《汉书》地理志云:‘凡民涵五常之性,而其刚柔缓急,声音不同,系水土之风气,故谓之风;好恶取舍动静无常,随上之情欲,故谓之俗’。风与俗对则小别,散则义通。”孔颖达这段阐明的意思是说,由自然条件不同而形成的习尚叫“风”,由社会环境不同而形成的习尚叫“俗”,两者义近,联绵一处,即指风尚习气而言。
从内容上看,《诗经》中的《齐风》表现了以下几个内容:第一,爱情诗。《鸡鸣》、《著》、《东方之日》、《甫田》都是写男欢女爱的爱情诗。作为来自民间里巷的“国风”,描写风土人情,表现民间的悲欢离合,就更多爱情诗了。第二,佃猎诗。此类诗有《还》、《卢令》两首。佃猎,在春秋时期,不仅是统治者的一种娱乐,也是民众的一种劳动。佃猎诗不仅是一种劳动生活的反响,而且更多的是一种尚武精神的表示,《齐风》中反响尚武精神的还有一首《猗嗟》。第三,讽谏诗。《东方未明》反响了奴隶主对奴隶的残酷奴役以及奴隶对繁重劳役的强烈不满。《南山》、《敝笱》、《载驱》则是戳穿齐襄公荒淫无耻的生活的。这些诗歌表现了很强的思想性和艺术性。
《诗经》与乐舞是联系在一起的,《齐风》也不例外。虽然曲谱已经失落传,但它的欣赏代价和社会浸染,却能从史籍中看出。如公元前542年,吴国公子季札至鲁,叔孙穆子使乐工为之歌《齐》,季札听后,赞颂曰:“美哉,泱泱乎大风也哉,表东海者,其太公乎?国未可限量也。”(《左传·襄公二十九年》)。从这一记载中可见《齐风》曲调的壮美,并表现了姜太公首创的齐国的大国风范。
总之,“齐风”和《齐风》是两个不同的观点,切切不可将两者混为一谈。
这首诗在一定程度上真实反响了那个时期的现实生活,使读者犹如身临其境,感想熏染到奴隶们心底隐蔽着一种压抑已久而行将喷发的愤怒。正由于作者是从奴隶的出生遭际出发,抒发对付现实的愤懑,带有强烈的感情色彩,因此对统治阶级确实有一种活生生的鞭辟入里的戳穿和批驳浸染,使读者产生感情上的共鸣。
《诗经·东方未明》
东方未明,颠倒衣裳。
颠之倒之,自公召之。
东方未晞,颠倒裳衣。
颠之倒之,自公令之。
折柳樊圃,狂夫瞿瞿。
不能辰夜,不夙则莫。
衣裳:古时上衣叫“衣”,下衣叫“裳”。
公:公家。
晞(xī 希):“昕”的假借,清晨,天刚亮。
樊:即“藩”,竹篱。
圃:菜园。
狂夫:指督工。一说狂妄无知的人。
瞿瞿(jù):瞪视貌。
不能辰夜:指不能节制韶光。辰,借为“晨”,指白天。
夙:早。
莫(mù 暮):古“暮”字,晚。
大意:
东方还未露曙光,衣裤颠倒乱穿上。
衣作裤来裤作衣,公家召唤我忧急。
东方还未露晨曦,衣裤颠倒乱穿起。
裤作衣来衣作裤,公家号令我惊惧。
折下柳条围竹篱,狂汉瞪眼真强霸。
不分白天与黑夜,不早就晚真作孽。
前两章“东方未明,颠倒衣裳。颠之倒之,自公召之。东方未晞,颠倒裳衣。颠之倒之,自公令之。” 墨客并没有用很多笔墨去铺叙详细的劳动场面,或者诉说劳动如何艰辛,而是奥妙地捉住一瞬间涌现的尴尬而苦涩的场面来写:当一批劳累的人们正甜睡之际,溘然响起了公家督工的吆喝声,敦促着他们去上工。这时东方还没有一丝亮光,原来.寂静的夜空,一下子被这叫喊声冲破,劳工们一个个被惊醒过来,阴郁中东抓西摸,惊悸失措,有的抓着裤管套上胳膊,有的撑开衣袖伸进双腿。一韶光,乱作一堆,急成一团,真可谓洋相出尽。天还没亮,官差即来敦促起床,上工的命令就已经下达了,甚至可怜的役夫们在忙乱之中把两手伸进裤管,把两脚蹬进袖筒,竟然把高下衣裳颠倒穿了。
按理说,高下衣裳的差异是很大的,能够穿颠倒了,不只是由于入夜的缘故原由,恐怕更紧张的缘故原由在于役夫们并没从梦中醒来,他们可能头天夜里睡得很晚,疲倦的身子包括疲倦的大脑尚未缓过神来。这一情节极富戏剧性,十分诙谐可笑,却又饱含悲愤,笑中滴泪,生动弯曲地反响出了酷吏的凶恶以及役夫的悲惨。“颠倒衣裳”的细节描写,便利用得真实奥妙,写出了奴隶们在公爷的吆呼敦促下摸黑穿衣裳的不堪处境。前两章的“颠倒”二字,还会令人自然遐想到末一章“风”(早上与“莫”(即“幕”,晚上)的“颠倒”。衣裳的错乱,黑(夜)白(天)的颠倒,正解释了社会现实的不合理。既意在言中,又寓意言外,可谓一语双关。
末了一句\公众折柳樊圃,狂夫瞿瞿。不能辰夜,不夙则莫\公众解释:报时辰不是提前便是太晚。这诗是讽刺国君号令不准的诗,而国君的‘时时’,又在于司时的官吏不负任务。古时无准确的钟表,故而司时的官吏就显得十分主要了,如果司时的官吏每天搞错一点点,积年累月,经由一定韶光,就可能涌现巨大的偏差。司时官吏失落职,当然朝廷秩序也会一片混乱。
本诗在于讽刺司时官吏不准确报时,甚至群臣见国君的韶光混乱,官员惊悸失措,心中忐忑不定,唯恐误时,遭到国君责怪。“折柳樊圃”和“狂夫瞿瞿”,也是两个范例的细节描述,寥寥八个字,就把奴隶们艰辛的苦役和督工走狗的凶暴嘴脸和盘托出,一泻无余。这些描述都相符环境和人物身份,读来仿佛见其人,闻其声,神态态毕现,维妙维肖,颇有真实感。
全诗三章,皆为四句。每句两个音拍。前两章利用回环复沓的艺术手腕,渲染环境气氛,突出事物特点。且以工致的排列。朗朗上口的措辞形式,尽情抒发烦闷情绪,增强了音乐效果。第三章则转变风格,避免通篇同等的呆板感,显得起伏有致,使得诗作的另一突出特点是通篇明白晓畅,措辞普通易懂,未明颠倒狂夫不能等都是人们常用的日常措辞,以此为诗朴实自然,充满无限的生命。
这些词语历经了三千余年的风雨,仍旧葆有无限的生命力,至今保存在人们的口头与书面用语之中。此外,全诗以四言句为形式,每句两个音拍,二二的节奏。前两章排列工致,键行和押韵有规律;第三章则起伏有致,跌宕变革。这种不拘一格的韵律节奏,也表示了当时劳动人民口头歌谣创作的艺术特点。
名家点评
《毛诗序》说:“《东方未明》,刺无节也。朝廷兴居无节,号令时时,挈壶氏(掌计时的官员)不能掌其职焉。”古代学者见地不合不多。今人一样平常认为这首诗是反响劳动者对繁重劳役的怫郁。《郑筏》则说”挈壶氏失落漏刻之节,东方之未明而以为明,故群臣匆匆遽,颠倒衣裳”。
清牛运震《诗志》以为“颠倒衣裳”这一句“奇语着迷,写忽乱光景宛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