忽过新丰市,还归细柳营。回看射雕处,千里暮云平。
译文及注释
译文
角弓上箭射了出去,弦声和着强风一起呼啸!
将军和士兵的猎骑,飞驰在渭城的近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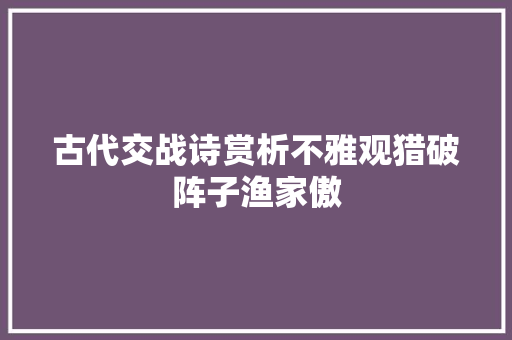
枯萎的野草,遮不住尖锐的鹰眼;积雪融化,飞驰的马蹄更像风追叶飘。
转眼间,猎骑穿过了新丰市,驻马时,已经回到细柳营。
凯旋时转头一望,那打猎的地方;千里无垠,暮云笼罩,原野悄悄静。
注释
诗题一作《猎骑》。《乐府诗集》、《万首唐人绝句》取此诗前四句作一首五绝,题作《戎浑》,《全唐诗》亦以《戎浑》录入卷五逐一张祜集中,皆误。
角弓:以牛角加强弓回弹强度的复合弓。
渭城:秦时咸阳城,汉改称渭城,在今西安市西北,渭水之北。
眼疾:目光敏锐。
新丰市:故址在今陕西省临潼县东北,是古代盛产美酒的地方。
细柳营:在今陕西省长安县,是汉代名将周亚夫屯军之地。《史记·绛侯周勃世家》:“亚夫为将军,军细柳以备胡。”借此指打猎将军所居军营。
射雕:北齐斛律光精通身手,曾命中一雕,人称“射雕手”,此引用其事以赞颂将军。
暮云平:傍晚的云层与大地相连。
雕:猛禽,飞得快,难以命中
鉴赏
诗题一作《不雅观猎》。从诗篇遒劲有力的风格看,当是王维前期作品。诗的内容不过是一次普通的佃猎活动,却写得激情洋溢,豪放有力。全诗共分两部分。前四句为第一部分,写射猎的过程;后四句写将军傍晚收猎回营的情景。至于其艺术手腕,几令清人沈德潜叹为不雅观止:“章法、句法、字法俱臻绝顶。盛唐诗中亦不多见。”(《唐诗别裁》)
诗开篇便是“风劲角弓鸣”,未及写人,先全力写其影响:风呼,弦鸣。风声与角弓(用角装饰的硬弓)声彼此相应:风之劲由弦的震响听出;弦鸣声则因风而益振。“角弓鸣”三字已带出“猎”意,能使人去想象那“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的射猎场面。劲风中射猎,该具备何等手眼!
这又唤起读者对猎手的悬念。待声势俱足,才推出射猎主角来:“将军猎渭城”。将军的涌现,恰合读者的期待。这发轫的一笔,胜人处全在突兀,能先声夺人,“如高山坠石,不知其来,令人惊绝”(方东树)。两句“若倒转便是凡笔”(沈德潜)。
渭城为秦时咸阳故城,在长安西北,渭水北岸,其时平原草枯,积雪已消,冬末的冷落中略带一丝儿春意。“草枯”“雪尽”四字如素描一样平常简洁、形象,颇具画意。“鹰眼”因“草枯”而特殊锐利,“马蹄”因“雪尽”而绝无滞碍,颔联体物极为风雅。三句不言鹰眼“锐”而言眼“疾”,意味猎物很快被创造,紧接以“马蹄轻”三字则见猎骑迅速追踪而至。“疾”“轻”下字俱妙。两句使人遐想到鲍照写猎名句:“兽肥春草短,飞鞚越平陆”,但这里创造猎物进而追击的意思是明写在纸上的,而王维却将同一层意思隐然句下,使人寻想,便觉诗味隽永。三四句初读似各表一意,对仗铢两悉称;细绎方觉意脉相承,实属“流水对”。如此精妙的对句,实不多见。
以上写出猎,只就“角弓鸣”、“鹰眼疾”、“马蹄轻”三个细节点染,不写猎获的场面。一则由于猎获之见地于言外;二则射猎之乐趣,远非实际功利所可计量,只就猎骑英姿与影响写来自佳。
颈联紧接“马蹄轻”而来,意思却迁移转变到罢猎还归。虽迁移转变而与上文意脉不断,自然流走。“新丰市”故址在今陕西临潼县,“细柳营”在今陕西长安县,两地相隔七十余里。此二地名俱见《汉书》,墨客兴会所至,一时搜集,典雅有味,原不必指实。言“忽过”,言“还归”,则见返营驰骋之疾速,真有瞬息“千里”之感。“细柳营”本是汉代周亚夫屯军之地,用来就多一重意味,似谓诗中佃猎的主人公亦具名将之风姿,与其前面射猎时斗志昂扬、飒爽英姿,形象正相吻合。这两句连上两句,既生动描写了猎骑情景,又真切表现了主人公的轻快觉得和喜悦心情。
写到猎归,诗意本尽。尾联却更以写景作结,但它所写非营地景致,而是遥遥“回看”向来行猎处之远景,已是“千里暮云平”。此景遥接篇首。首尾不但彼此呼应,而且适成对照:当初是风起云涌,与出猎紧张气氛相应;此时是风定云平,与猎归后犹豫容与的心境相称。写景俱是表情,于景的变革中见情的消长,堪称妙笔。七句语有出典,《北史·斛律光传》载北齐斛律光校猎时,于云表见一大鸟,命中其颈,形如车轮,旋转而下,乃是一雕,因被人称为“射雕手”。此言“射雕处”,有暗示将军的膂力强、箭法高之意。诗的这一结尾遥曳生姿,饶有余味。
这首诗很长于利用先声夺人、侧面陪衬和活用典故等艺术手段来刻画人物,从而使诗的形象光鲜生动、意境恢宏而蕴藉。诗写的虽这天常的佃猎活动,但却维妙维肖地刻画出将军的骁勇英姿,传染力。在这首诗中王维所要表达的思想感情却是渴望效命疆场,期盼建功立业。
综不雅观全诗,半写出猎,半写猎归,起得突兀,结得意远,中两联一气流走,承转自若,有格律束缚不住的气势,又能首尾回环映带,体合五律,这是章法之妙。诗中藏三地名而使人不觉,用典浑化无迹,写景俱能传情,三四句既穷极物理又见地于言外,这是句法之妙。“枯”、“尽”、“疾”、“轻”、“忽过”、“还归”,遣词用字准确熬炼,咸能照料,这是字法之妙。所有这些手腕,又都能奥妙表达诗中人生气远出的意态与豪情。以是,此诗完备当得起盛唐佳作的称誉。
十一月四日风雨大作僵卧孤村落不自哀,尚思为国戍轮台。
更阑卧听风吹雨,铁马冰河入梦来。
注释
僵卧:直挺挺躺着。这里形容自己穷居孤村落,无所作为。僵:僵硬,僵直。
孤村落:孤寂荒凉的村落落。不自哀:不为自己而感到悲哀,不为自己哀伤。
尚:副词,还,仍旧;表示事情的连续或残余状态。
思:想着,想到。为:介词,为,为了;表示动作行为的目的。
戍轮台:在新疆一带防守。戍(shù),守卫。轮台,现在的新疆轮台县,汉代曾在这里驻兵屯守。这里泛指北方的边防据点。
更阑:夜深。阑:残尽。
卧听:躺着听。
风吹雨:风雨交加,和题目中“风雨大作”相呼应;当时南宋王朝处于风雨飘摇之中,“风吹雨”也是时局写照,故墨客直到深夜尚难成眠。
铁马:披着铁甲的战马。
冰河:冰封的河流,指北方地区的河流。
翻译
我直挺挺躺在孤寂荒凉的村落庄里,没有为自己的处境而感到悲哀,心中还想着替国家守卫边陲。
深夜里,我躺在床上听到那风雨的声音,迷迷糊糊地梦见,自己骑着披着铁甲的战马跨过冰封的河流出征北方疆场。
渔家傲①· 秋思
塞②下秋来风景异,衡阳雁去③无留神。四面边声连角起。千嶂里,长烟落日孤城闭。
浊酒一杯家万里,燕然未勒归无计。羌管悠悠霜满地。人不寐 ,将军白发征夫泪。
作品注释
①渔家傲:别号《吴门柳》、《忍辱神仙》、《荆溪咏》、《游仙关》。
②塞:边界要塞之地,这里指西北边陲。
③衡阳雁去:传说秋日北雁南飞,至湖南衡阳回雁峰而止,不再南飞。
④边声:边塞特有的声音,如大风、号角、羌笛、马啸的声音。
⑤千嶂:绵延而峻峭的山峰;崇山峻岭。
⑥燕然未勒:指战事未平,功名未立。燕然:即燕然山,今名杭爱山,在今蒙古国境内。据《后汉书·窦宪传》记载,东汉窦宪率兵追击匈奴单于,去塞三千余里,登燕然山,刻石勒功而还。
⑦羌管:即羌笛,出自古代西部羌族的一种乐器。
⑧悠悠:形容声音飘忽不定。
⑨寐:睡,不寐便是睡不着。
作品译文
秋日到了,西北边塞的风光和江南不同。大雁又飞回衡阳了,一点也没有勾留之意。薄暮时,军中号角一吹,周围的边声也随之而起。层峦叠嶂里,暮霭沉沉,山衔落日,孤零零的城门紧闭。
饮一杯浊酒,不由得想起万里之外的家乡,未能像窦宪那样降服仇敌,刻石燕然,不能早作归计。悠扬的羌笛响起来了,景象寒冷,霜雪满地。夜深了,将士们都不能安睡:将军为操持军事,须发都变白了;战士们久戍边塞,也流下了伤时的眼泪。
创作背景
宋康定元年(1040年)至庆历三年(1043年)间,范仲淹任陕西经略副使兼延州知州。据史载,在他镇守西北边陲期间,既号令严明又爱抚士兵,并招徕诸羌推心收受接管,深为西夏所惮服,称他“腹中有数万甲兵”。这首词作于北宋与西夏战役对峙期间。宋仁宗年间,范仲淹被朝廷派往西北前哨,承担起北宋西北边陲防卫重任。
文学赏析
范仲淹是当时的著名的军事家、政治家,官至副宰相。他理解民间疾苦,深知宋王朝在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存在的问题,主见拔除积弊,但因统治集团内部守旧派的反对,没能实现。
他也是著名的文学家。这首《渔家傲》是他的代表作,反响的是他亲自经历的边塞生活。古代把汉族政权和少数民族政权之间的交界地方叫做“塞”或“塞上”、“塞下”。这首词所说的塞下,指的是北宋和西夏交界的陕北一带。
从词史上说,此词沉雄开阔的意境和苍凉悲壮的气概,对苏轼、辛弃疾等也有影响。
任何一首诗词的审美代价,是由多种艺术功能构成的。这首《渔家傲》并非以军事征战为题材,而是写边塞将士对家乡的怀念,因之不能生硬地用政治的尺度来衡量,而该当用艺术的尺度来衡量。它的艺术功能、艺术力量,在于抒怀写景,但纵然从政治上哀求,此词的意义也并不消极。“燕然未勒归无计”一句,正是这首词最实质的思想亮点。燕然山,即今之杭爱山。后汉时,将军窦宪追击匈奴,曾登上燕然山刻碑(勒石)纪功。词中霜雪满头的老将军,已擦干思乡之泪,在恋家与报国的抵牾中,他因此戍边军务为重。他效忠职守,不建功勋于边陲,虽有时思乡心切,也是不打算归去的。
词的上阕侧重写景。秋来风景异,雁去无留神,是借雁去衡阳回雁峰的典故,来反响人在塞外的思归之情。思归不是由于厌弃边塞生活,不顾国家安危。而是边防凄厉的号角声以及周遭的狼嗥风啸声,令民气寒。更奈何日落千嶂,长烟锁山,孤城紧闭,此情此景甚是令人怀念故乡的温馨。人非草木,孰能无情。一个长期戍边的老将,想念亲人和家乡也是很自然的。“千嶂里,长烟落日孤城闭”,此句写得最成功,仅10个字便勾勒出一派壮阔苍茫的边塞薄暮景致。
写景是为了抒怀。因此下阕一开头便是“浊酒一杯家万里,燕然未勒归无计”。浊酒,本是乳白色的米酒,这里也暗喻心情重浊。由于思归又不能归甚至心情重浊。“归无计”,是说没有两全其美的可能性。正在这抵牾的心绪下,远方羌笛悠悠,搅得征夫们难以入梦,不能不苦思着万里之遥的家乡,而家乡的亲人可能也在愿望白发人。“人不寐,将军白发征夫泪”,这10个字扣民气弦,写出了深奥深厚忧国爱国的繁芜感情。
这首《渔家傲》不是令人消沉斗志之词,它真实地表现了戍边将士思念故乡,而更热爱祖国,矢志保卫祖国的真情。范仲淹曾在《岳阳楼记》一文中,倡导“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崇高精神。词中的白发老将军,正是这种崇高精神的生动写照。黄蓼园说它“读之凛凛有生气”,倒是深得其旨趣。
“千嶂里,长烟落日孤城闭”。只此两句便抵得上那首有名的《敕勒歌》,虽然彼此取材不同。伟大的墨客杜甫曾写过“孤城早闭门”的佳句,但气势的雄浑似不及范词。那是人烟稀少的边塞,光秃的山峰重重叠叠,上空飘浮着一缕缕的青烟,悲壮的号角和着凌乱的边声在四野回荡。太阳还没有收起它金色的余晖,远了望去,山腰里一座孤零零的城池早已把城门关闭。这就像一幅中世纪边塞景象的艺术拍照。
一幅野性十足的边塞图画。“塞下秋来风景异,衡阳雁去无留神,四面边声连角起,千嶂里,长烟落日孤城闭。”这样的“边塞感情”,每每当人物置身特定场景之后,自然流露出来;此时才明白,长烟落日的边塞,对付生命个体而言,并不仅仅是“戍边苦”,还会产生极大的生理知足。
词是范仲淹守边欲望和繁芜心态的真实暴露。词中反响了边塞生活的艰巨和词人巩固边防的决心和意愿,同时还表现出外祸未除、功业未建、久戍边地、士兵思乡等繁芜抵牾的心情。在有着浓郁思乡感情的将士们的眼中,塞外之景致失落去了宽广的气概、欢愉的气氛,画面上笼罩着一种旷远雄浑、苍凉悲壮的气氛。在边塞熬白黑发,滴尽思乡泪,却又不能抛开国事不顾,将士们的生理是抵牾繁芜的。范仲淹虽然守边颇见成效,然而,当时在北宋与西夏的军事力量比拟上,北宋处于下风,只能保持守势。范仲淹守边的全部功绩都表示在“能够坚持住守势”这样一个局势上,时而还有疲于奔命之感。这对有远大政治志向的范仲淹来说肯定是不能知足的,但又是十分无奈的。以是,表示在词中的格调就不会是昂扬年夜方的。
此前,很少有人用词来写边塞生活。唐代韦应物的《谐谑》虽有“边草无穷日暮”之句,但没有展开,且短缺真实的生活根本。以是,这首词实际上是边塞词的创始。
上片描述边地的荒凉景象。首句指出“塞下”这一地域性的特点,并以“异”字领起全篇,为下片怀乡思归之情埋下了伏线。“衡阳雁去”是“塞下秋来”的客不雅观现实,“无留神”虽然是北雁南飞的详细表现,但更主要的是这三个字来自戍边将士的内心,它衬托出雁去而人却不得去的情绪。以下十七字通过“边声”“角起”“千嶂”“孤城”等具有特色性的事物,把边地的荒凉景象描述得有条有理。首句中的“异”字通过这十七个宇得到了详细的发挥。
下片写戍边战士厌战思归的心情。前两句含有三层意思:“浊酒一杯”扑不灭思乡情切;长期戍边而破敌无功;以是产生“归无计”的慨叹。接下去,“羌管悠悠霜满地”一句,再次用声色加以点染并略加抑扬,此时心情,较薄暮落日之时更加令工资难。“人不寐”三字绾上结下,个中既有白发“将军”,又有落泪“征夫”。“不寐”又紧密地把上景下情联系在一起。“羌管悠悠”是“不寐”时之所闻;“霜满地”是“不寐”时之所见。黑幕外景达到了水乳交融的艺术境界。
破阵子⑴·为陈同甫赋壮词以寄之⑵醉里挑灯看剑⑶,梦回吹角连营⑷。八百里分麾下炙⑸,五十弦翻塞外声⑹。疆场秋点兵⑺。
马作的卢飞快⑻,弓如霹雳弦惊⑼。了却君王天下事⑽,赢得生前身后名⑾。可怜白发生⑿!
词句注释
⑴破阵子:唐玄宗时教坊曲名,出自《破阵乐》,后用为词牌。
⑵陈同甫:陈亮(1143—1194),字同甫,南宋婺州永康(今浙江永康县)人。与辛弃疾志同道合,结为石友。其词风格与辛词相似。
⑶挑灯:把灯芯挑亮。看剑:抽出宝剑来细看。
⑷梦回:梦里遇见,解释下面描写的沙场场景,不过是作者旧梦重温。吹角连营:各个军营里接连不断地响起号角声。角:军中乐器,长五尺,形如竹筒,用竹、木、皮、铜制成,外加彩绘.名目画角。始仅直吹,后用以横吹。其声哀厉高亢,闻之使人振奋。
⑸八百里:牛名。《世说新语·汰侈》载,晋代王恺有一头宝贵的牛,叫八百里驳。分麾(huī)下炙(zhì):把烤牛肉分赏给部下。麾下:部下。麾:军中大旗。炙:切碎的熟肉
⑹五十弦:原指瑟,此处泛指各种乐器。翻:演奏。塞外声:指悲壮粗犷的战歌
⑺疆场:沙场。秋:古代点兵用武,多在秋日。点兵:校阅阅兵军队。
⑻马作的卢飞快:战马像的卢马那样跑得飞快。作:像……一样。的卢:良马名,一种烈性快马。相传刘备在荆州遇险,前临檀溪,后有追兵,幸亏骑的卢马,一跃三丈,而分开险境。见《三国志·蜀志·先主传》。
⑼霹雳:本是疾雷声,此处比喻弓弦响声之大。
⑽了却:了却,把事情做完。君王天下事:统一国家的大业,此特指规复中原事。
⑾赢得:博得。身后:去世后。
⑿可怜:可惜。
口语译文
醉里挑亮油灯不雅观看宝剑,梦入耳到军营的号角声响成一片。把牛肉分给部下享用,让乐器奏起雄壮的军乐鼓舞士气。这是秋日在沙场上阅兵。
战马像的卢马那样跑得飞快,弓箭像惊雷一样震耳离弦。齐心专心想完成替君收复国家失落地的大业,取得世代相传的隽誉。可惜壮志难酬,白发已生!
创作背景
这首词是作者失落意闲居信州(今江西上饶)时所作。辛弃疾21岁时,就在家乡历城(今山东济南)参加了抗金叛逆。叛逆失落败后,他回到南宋,当过许多地方的主座。他安定民生,演习军队,极力主见收复中原,却遭到排斥打击。后来,他长期不得任用,闲居近二十年。
公元1188年,辛弃疾与陈亮在铅山瓢泉会见,即第二次“鹅湖之会”。此词当作于这次会见又分别之后。
文学赏析
此词以两个二、二、二的对句开头,通过详细、生动的描述,表现了多层情意。第一句,只六个字,却用三个连续的、富有特色性的动作,塑造了一个壮士的形象,让读者从那些动作中去体会人物的内心活动,去想象人物所处的环境,意味无穷。为什么要吃酒,而且吃“醉”?既“醉”之后,为什么不去睡觉,而要“挑灯”?“挑”亮了“灯”,为什么不干别的,偏偏抽出宝剑,映着灯光看了又看?……这持续串问题,只要细读全词,就可能作出应有的回答,因而不必解释。“此时无声胜有声”。用什么样的“解释”也难以比这无言的动作更有力地展现人物的内心天下。
“挑灯”的动作又点出了夜景。那位壮士在夜深人静、万籁俱寂之时,思潮彭湃,无法入睡,只好独自吃酒。吃“醉”之后,仍旧不能沉着,便继之以“挑灯”,又继之以“看剑”。翻来覆去,总算睡着了。而刚一入睡,方才所想的统统,又幻为梦境。“梦”了些什么,也没有明说,却迅速地换上新的镜头:“梦回吹角连营。”壮士好梦初醒,天已清晨,一个军营连着一个军营,响起一片号角声。这号角声,富有催人勇往无前的力量。而那位壮士,也恰好是统领这些军营的将军。于是,他一跃而起,全副披挂,要把他“醉里”、“梦里”所想的统统统统变为现实。
三、四两句,可以不讲对仗,词人也用了偶句。偶句太多,随意马虎显得呆板;可是在这里正好相反。两个对仗极工、而又极其雄浑的句子,突出地表现了雄壮的军容,表现了将军及士兵们高昂的战斗感情。“八百里分麾下炙,五十弦翻塞外声”:兵士们欢欣鼓舞,饱餐将军分给的烤牛肉;军中奏起振奋民气的战斗乐曲。牛肉一吃完,就排成整洁的军队。将军神采奕奕,意气昂扬,“疆场秋点兵”。这个“秋”字下得好。正当“秋高马壮”的时候,“点兵”出征,预示了战无不胜的前景。
按谱式,《破阵子》是由句法、平仄、韵脚完备相同的两“片”构成的。后片的开始,叫做“过片”,一样平常的写法是:既要和前片有联系,又要“换意”,从而显示出这是另一段落,形成“岭断云连”的境界。辛弃疾却每每打破这种限定,《贺新郎·别茂嘉十二弟》如此,这首《破阵子》也是如此。“疆场秋点兵”之后,大气磅礴,直贯后片“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将军率领铁骑,快马加鞭,神速奔赴前哨,弓弦雷鸣,万箭齐发。虽没作更多的描写,但从“的卢马”的飞驰和“霹雳弦”的巨响中,仿佛看到多少连续涌现的画面:仇敌纷纭落马;残兵败将,狼狈溃退;将军身先士卒,乘胜追杀,一顷刻结束了战斗;凯歌交奏,欢天喜地,旌旗飘荡。
这是一场反击战。那将军是爱国的,但也是追求功名的。一战得胜,功成名就,既“了却君王天下事”,又“赢得生前身后名”,当为“壮”也。
如果到此为止,那真够得上“壮词”。然而在那个被屈膝降服佩服派把持朝政的时期,并没有产生真正“壮词”的条件,以上所写,不过是词人孜孜以求的空想而已。词人展开丰富的想象,化身为词里的将军,刚攀上空想的高峰,忽然一落千丈,跌回冷漠的现实,沉痛地慨叹道:“可怜白发生!
”白发已生,而收复失落地的空想成为泡影。想到自己徒有志薄云霄,而“报国欲去世无沙场”(借用陆游《陇头水》诗句),便只能在不眠之夜吃酒,只能在“醉里挑灯看剑”,只能在“梦”中驰逐疆场,快意一时。……这处境,的确是“悲哀”的。然而没有谁“可怜”他。于是,他写了这首“壮词”,寄给处境同样“可怜”的陈同甫。
同甫是陈亮的字。学者称为龙川师长西席。为人才华豪迈,议论纵横。自称能够“推倒一世之智勇,开拓万古之心胸”。他先后写了《复兴五论》和《上孝宗天子书》,积极主见抗战,因而遭到屈膝降服佩服派的打击。宋孝宗淳熙十五年冬天,他到上饶访辛弃疾,留旬日。别后辛弃疾写《贺新郎》词寄他,他和了一首;往后又用同一词牌反复唱和。这首《破阵子》大约也是这一期间写的。
全词从意义上看,前九句是一段,十分生动地描述出一位推诚相见,忠一不二,勇往直前的将军的形象,从而表现了词人的远大抱负。末一句是一段,以沉痛的慨叹,抒发了“壮志难酬”的悲愤。壮和悲,空想和现实,形成强烈的反差。从这反差中,可以想到当时南宋朝廷的腐败无能,想到公民的水深火热,想到所有爱国志士报国无门的苦闷。由此可见,极其豪放的词,同时也可以写得极其蕴藉,只不过柔顺约派的蕴藉不同罢了。
这首词在音调方面有一点值得把稳。《破阵子》高下两片各有两个六字句,都是平仄互对的,即上句为“仄仄平平仄仄”,下句为“平平仄仄平平”,这就构成了和谐的、舒缓的音节。高下片各有两个七字句,却不是平仄互对,而是仄仄平平平仄仄,仄仄平平仄仄平,这就构成了拗怒的、激越的音节。和谐与拗怒,舒缓与激越,形成了抵牾统一。作者很好地利用了这种抵牾统一的音调,恰当地表现了抒怀主人公繁芜的生理变革和梦想中的战斗准备、战斗进行、战斗胜利等许多场面的转换,收到了绘声绘色、声情并茂的艺术效果。
这首词在布局方面也有一点值得把稳。“醉里挑灯看剑”一句,溘然发轫,相继而来的是闻角梦回、连营分炙、疆场点兵、克敌制胜,有如鹰隼突起,凌空直上。而当翱翔天涯之时,陡然下跌,发出了“可怜白发生”的感叹,使读者不能不为作者的壮志难酬洒下惋惜怜悯之泪。这种陡然着落,同时也嘎然而止的写法,如果利用得好,每每因其出人意外而扣民气弦,产生强烈的艺术效果。这样的构造不但宋词中少有,在古代诗文中也很少见。这种艺术手腕也正表现了辛词的豪放风格和他的独创精神。但是辛弃疾利用这样的艺术手腕,不是故意虚假技巧、追求新奇,这种表达手腕正密切结合他的生活感情、政治遭遇。由于他的规复大志难以实现,心头百感喷薄而出,便自然冲破了形式上的常规,这绝不是一样平常只讲究文学形式的作家所能做到的。
李白有首叫《越中览古》的诗。诗中写道:“越王勾践破吴归,战士还家尽锦衣。宫女好花满春殿,只今惟有鹧鸪飞!
”这首七言诗中,有三句写到越王勾践的壮大,末了一句才点出越国的衰败景象,虽然表达的感情显然不同,但在谋篇布局方面又有相通之处,可以参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