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初酿
已而夕阳在山,人影散乱,太守归而来宾从也。
树林阴翳,鸣声高下,游人去而禽鸟乐也。
然而禽鸟知山林之乐,而不知人之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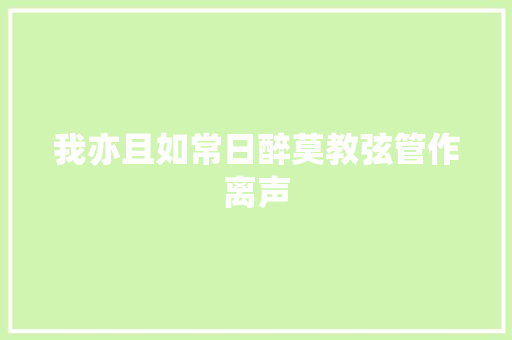
人知从太守游而乐,而不知太守之乐其乐也。
醉能同其乐,醒能述以文者,太守也。
太守谓谁?庐陵欧阳修也。
醉能同乐,醒能撰文,便是北宋大墨客欧阳修。他生平与酒为友,与文相伴,在浓浓酒喷鼻香中,一篇篇绝美诗文文字淋漓。
欧阳修并不是簪缨之家,父亲早逝,寡母以芦荻教他认字。他聪明勤奋,不负母望,在天圣八年得中进士,同时又被恩师胥偃选为乘龙快婿。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让这个穷小子一下子从人间步入天国,春风得意,激情飞扬。
青春何处风光好?帝里偏爱元夕。
万重缯彩,构一屏峰岭,半空金碧。
宝檠银钰,耀绛幕、龙虎腾掷。
沙堤远,雕轮绣毂,争走五王宅。
雍容熙熙昼,会乐府神姬,海洞仙客。
拽喷鼻香摇翠,称执手行歌,锦街天陌。
月淡寒轻,渐向晓、漏声寂寂。
当年少,狂心未己,不醉怎归得!
——《御带花》
年少本浮滑,更何况刚刚踏入仕途的风骚才子。此时的欧阳修才二十七八,正是人生中最好的年华,他来到帝都,走进繁华,又有一群诗朋酒友相伴。灯红酒绿,笙歌乐舞,让他有一丝迷离与梦幻。
元宵夜的汴京城是热闹的,彩灯结成高入云天的灯山,层层叠叠,残酷刺目耀眼;川流不息的车马,携着阵阵清香和欢声笑语,时时掠过身畔。恍然以为如入梦中瑶池,幻影桃园。
如此良辰美景,墨客怎可辜负,必是要一醉方休。
月色渐淡,晓露轻寒,天立时就要亮了,这群年轻人却还以为不尽兴。
有人说:“年轻,便是一首吟诵的诗,让每一个词句都有鲜花的绽放。年轻,便是一首欢畅的歌,让每一个音符都有激情的飞扬!
”年轻的欧阳修也正如绽放的鲜花,飞扬的音符,在这个充满了诱惑与梦想的帝都,将这诗酒年华尽情挥洒。
年轻人是快乐的,但他们也偶尔会有一些小忧闷,不过那些忧和愁,在别人眼里都算不得什么。就像辛弃疾诗中说的:“少年不识愁滋味,爱上层楼。爱上层楼,为赋新诗强说愁。”欧阳修也在诗中说着自己的少年愁。
把酒祝东风,且共从容。
垂杨紫陌洛城东。
总是当时携手处,游遍芳丛。
聚散苦匆匆,此恨无穷。
今年花胜去年红。
可惜明年花更好,知与谁同?
——《浪淘沙》
天圣九年,欧阳修来到洛阳,与梅尧臣等人结为好友,常常在一起饮酒谈天,诗文唱和。当时他们的上司是钱惟演,很是惯着这帮年轻人,不拘束他们,鼓励他们吃喝玩乐。或许是他后悔自己的青春过于惨淡,不肯望面前的这些年轻人也错过了青春浪漫。
欧阳修是幸运的,初入职场,就碰着了一位宽容的上司,让他可以自由发挥,充分展示自己的才华。于是在茶喷鼻香酒醇之余,他与诗友们一起研究古文创作,冲破了之前盛行的陈腐文风。他的词作也摒弃了前朝的浮华,开启了平实淡雅的词风。
生活的轻松愉快,让他依然如少年郎般无惧忧闷,就连离去在他的眼中也只是淡淡轻愁,如薄雾青烟,随风即散。
青春对付每个人都是平等的,不会为任何一个人稍作勾留,纵然大文豪亦不可豁免。欧阳修的青春岁月也在须臾间过去,世事沧桑,官场沉浮,他从繁华的帝都被贬偏远的边疆小城。他从众星捧月般的青年才俊,成为了一个无人问津的贬谪小吏,他有些许的茫然和失落落。
楚人自古登临恨,暂到愁肠已九回。
万树苍烟三峡暗,满川明月一猿哀。
殊乡况复惊残岁,慰客偏宜把羽觞。
行见江山且吟咏,不因迁谪岂能来。
——《黄溪夜泊》
岁末年终,贬谪千里,他无以释怀,只能用酒来抚慰,让那个寂冷的心暂时有一些温度。当然这杯酒再不同昔日,羽觞中不再有飞扬的激情与空想,只有孤寂与落寞。
然而,任何一个能够名垂千古的人,都不可能被一次挫折打败。如果就此沉沦,就没有了后来官至副宰相的大政治家,没有了首创一代文风的大文豪。拿破仑曾说过:“人生的荣光,不在永不失落败,而在于屡仆屡起。”
欧阳修不久就重新站了起来,不再自怨自艾。当然他也不再是从前的那个鲜衣怒马少年郎,风花雪月,诗酒华年已随风逝去,转而多了一份成熟和豪壮,他溘然间就终年夜了。
平山阑槛倚晴空,山色有无中。
手种堂前垂柳,别来几度东风?
文章太守,挥毫万字,一饮千钟。
行乐直须年少,尊前看取衰翁。
——《朝中措·送刘仲原甫出守维扬》
扬州城北的平山堂凌空矗立,犹如一飞冲天的大鹏,这是他建造的庭堂,也是贰心中的大鹏。挥毫万字,一饮千钟,他是气度豪迈、文采飞扬的“文章太守”。
在文字美酒的浸润中,欧阳修走入了不惑之年,鬓边已生华发,肩背也不再挺立。而此时他因参与庆历新政改革,再次被贬,远赴颍州。心中虽有不甘,但已不再沉郁,而且在狂放不羁中又多了一份洒脱和豁达。
堤上游人逐画船,拍堤春水四垂天。
绿杨楼外出秋千。
白发戴花君莫笑,六幺催拍盏频传。
人生何处似尊前!
——《浣溪沙》
在游船如织的西湖上,一位白发老翁头戴鲜花,随着婉转的“六幺”曲调,与朋侪们推杯换盏,看上去是那么惬意闲适,悠然自得。仿佛他不是贬谪到此,而仅仅只是沉着生活中的一次游山玩水,老友相聚。
大概这便是所谓的发展,“便是把悲哀调成静音模式,感情不动声色”。或许他真的放开了统统,也或许只是将所有情绪不动声色地埋在心底。
从少年时的“不醉怎归得”,到盛年的“一饮千钟”,再到晚年的“六幺催拍盏频传”,诗与酒生平都伴随着他。虽不是“李白斗酒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他也是十诗九酒,诗酒相伴。如果没有酒的生平相随,或许也就没有了那么多幽美的诗文相传。
花光浓烂柳轻明,酌酒花前送我行。
我亦且如平日醉,莫教弦管作离声。
——《别滁》
他亦不负“醉翁”的别号,酌酒花前,日日常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