诚然,魏源以学术著而不因此诗名并非自当代始,郭嵩焘在清同治九年(1870)写的《古微堂诗集序》中就曾经感叹:“默深师长西席喜经世之略,其为学淹博贯通,无所不窥,而务出己意,耻蹈袭古人。人知其以经济名世,不知其能诗,而师长西席之诗顾最夥。”不过当时造成这种“不知”的紧张缘故原由,还是由于刻印与传播之不易,他自己对此也不在乎,凡是能读到他作品的人,无不异口同声给予了极高的评价。郭嵩焘在惊叹之馀,直道其是“平视唐宋以来作者,负才以与之角,将以极古今笔墨之变,自发其嵚崎历落之气。每有所作,奇古峭厉,倏忽变革,不可端倪”。著有《射鹰楼诗话》和《海天琴思录》的林昌彝在所著中几次再三揄扬:“默深诗笔雄浩奔轶而复坚苍遒劲,直入唐贤之室……虽粗服乱头,不加润色,而气韵天然,非时髦所能蹑也。道州何子贞师谓默深诗如雷电倏忽,金石争鸣,包括时感,挥洒万有。少作已奇,壮更蹠实,诚为切论。”罗汝怀在晚年所作的《古微堂诗集叙》中盛赞其于诗“自行胸臆,达难显之情,状未道之景。古质如谣,明畅如策,栉比如赋,于是诗又别为一格。有谓自唐宋以来,诗家派别繁多而未有此体者,舍人不屑也。”徐世昌在《晚晴簃诗汇·诗话》中云:“默深为文发抒心得,不蹈故常,奥如衍如,自成一格,作诗亦然。其雕镌造化搥险凿幽之笔,能使山无遁形,水无匿响,凡难显之状,未道之景,一经摅写,如鼎铸象,如镜映影,自汉、魏、唐、宋以来,亦别为一体。盖其才大学博,不能以常格绳之也。”
以上只是选摘了几位与魏源同时期或稍后墨客兼诗论家对其作品的称道,对付他是一位精彩的墨客,已不须要我们再多饶舌了。
魏源自年少即有诗名。与他同被誉为“湘中三杰”的何绍基称其“少作已奇”,从集中可断定为十九岁之前所作的如七言古诗《送李希莲陈云心何积之归郴州》《大雪行》《夜雨行》和五言律诗《岳麓介景台夜作》《宿营岳麓寺》《湘江舟行》等等,确已皆可见不同流俗,远非但知俳体八韵以求应制者可比。十五岁经史兼优,为时任湖南学政李宗瀚所激赏,但正如他自己所咏叹的:“奇才与庸福,天地悭其兼”,科举入仕之途却十分不畅。何绍基于道光二年(1822)作《柬魏默深》诗云:“蕙抱兰怀只自怜,美人遥在碧云边。”相互以未造诣功名为憾!
魏源虽在这年秋日得中顺天乡试南元,按李元度在《国朝先正事略》中所说的“方师长西席之举京兆也,文誉飙起,典试者争欲吸取之”,但直到五十二岁时始中进士。不过,这反而更使他得以潜心学术与认清时局,造诣了生平的奇迹。他与龚自珍志同道合,但早已并非矢志要做墨客,一如罗汝怀在叙中所说的:“谓其为诗,非其所忻;谓其非诗,非其所惜,彼自道其学也。”正是这种既爱诗又不欲在诗坛争位的平常心,更使他造诣了自家的特色。
首先是只做诗而不是做诗,所作完备是出于内心自然流露。即其在《跋陈沆简学斋诗》中所言:“凡诗之作,必其情迫于不得已,景触于无心,而诗乃随之,则其机皆天也,非人也。”所谓“粗服乱头,不加润色”,并非是落笔成诗完备不加修正,而是谓倘无创作冲动不去刻意雕琢成篇,追求具有天然风采而不涂脂抹粉。同时,这种不刻意为诗亦非所谓创作全听凭灵感,而是如墨客自己在《诗比兴笺序》中所说的,不附和只求“专取翰藻”与“专诂名象”及“专揣于音节风调”,而“不问墨客所言何志”。魏源作为一位自觉肩负有历史义务感的墨客,在进行诗歌创作与学术论著时的认识是统一的。方濬师在《古微堂诗集序》中云:“作史三长,曰才、学、识而已,惟诗亦然……今读邵阳魏君默深诗,洵足擅三长之名矣!
”正由于“其才不可以斗计也,其识不可以蠡测也,其识不可以宇宙囿也”,故一有诗情使令,便能奇崛非常,令人击节讴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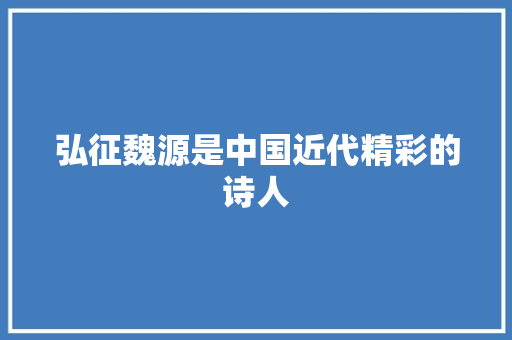
无人不道魏源才华纵横,不喜蹈袭故常。在进行诗歌创作时,所谓“粗服乱头”,亦涵括了从诗体、气韵、句式、修辞等各方面都富于独创,令人惊叹其是自汉魏唐宋以来,诗又别为一体,自成一格。为才华所发扬蹈厉的另一缘故原由,是墨客所面对的自有史以来未有的时局,包括海国强敌的环伺入侵,以及无数闻所未闻新事物的频频涌现,抒怀与达意已非固有的模式所能适应而必须别开生面。在这一点上,林昌彝有一首论魏源的诗云:“河山感喟写幽忧,利病苍生问九州。扫尽人间脂粉气,乱头粗服也风骚。”已道得颇为中肯。艺术贵在创新,诗体、诗格亦非一成不变,但只知墨守成规,专拿尺子去量是非是否合符古制者总是有的,魏源诗虽受到了普遍的、非常的称道,也不免随之有“诗非当行”“惟粗犷太甚”“失落粘失落对”之类的非议,这恐怕也正是为今日某些诗评家和选家所忽略的一个缘故原由。
古人紧张是陈衍在《石遗室诗话》中谓魏源诗属清苍幽峭一派,而才华所溢,时出入于他派。林昌彝在《海天琴思录》中谓“默深深得太白之高奇者也。钟嵘《诗品》以高奇为上品,余读默深《华岳》《太室》等篇,为之击节深赏”。罗汝怀则道是“为清幽,为闳肆,为淡冶,为秾丽,凡《诗品》所有者,莫不具焉”。仅就其某一部分作品而言,俱各有其是处,袁嘉穀在《卧雪诗话》中称“诗尤奇崛”更是许多作品的特色。然就其整体来看,我们能强烈感想熏染到的,是墨客正身处国势艰危之际,亟思善策以图救国拯民,因而,无论是他的时势诗、咏史诗或山水诗,皆是倾吐其胸中烦闷昂扬之气,表现出一种沉雄奇警的诗风,亦即他自己所推崇的“仁贤发奋之所作”。如《金陵怀古》八首之一:
一桁青山六代宫,沧桑都在水声中。
只今雨雪千帆北,自古云涛万马东。
千载江山风月我,百年出生去来鸿。
陆机别有兴亡辨,不与过秦监夏同。
又如《赠张虎头》绝句:
湖海元龙气不除,承平无处寄阴符。
江干饭饱浑无事,坐对寒潮捋虎须。
不独因《寰海十一章》《寰海后十章》等,感讽鸦片战役,痛数内忧外祸,才令人读之血脉贲张,遍及其他各种题材,亦能感想熏染到一股雄风激荡的时期强音。
龚自珍赠魏源联有云:“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综一代典,成一家言。”魏源平生足迹遍天下,所作山水诗极多,远至喷鼻香港、澳门,他都写有《喷鼻香港岛不雅观海市歌》和《澳门花园听夷女洋琴歌》,他自己亦谓“应笑十诗九山水”。遍游五岳而且都有组诗或长歌吟咏的,在中国历代墨客中只有他。在艺术上亦造诣极高,奔雷掣电,变革万端,异采奇情,极尽雄浑壮丽之美。前引罗汝怀、徐世昌诸人的评论都对其所作山水诗极为讴歌,郭嵩焘在序中亦特殊称道其“游山诗,山水草木之奇丽,云烟之变幻,滃然喷起于纸上,奇情诡趣,奔赴交会”。如《晒台石梁雨后不雅观瀑歌》的开篇:
雁湫之瀑烟苍苍,中条之瀑雷硠硠,匡庐之瀑浩浩如河江。惟有晒台之瀑不奇在瀑在石梁,如人侧卧一肱张。力能撑开八万四千丈,放出青霄九道银河霜。
从概括各地奇瀑的特色,以比拟突出此瀑的特异之奇,琅琅行云,急速就令人叫绝。又如《少室行》中有句云:
洛人多从侧背看,谁从汝颍道上瞻孱颜?天涯真人出云雾,凛然冠冕云霄寒。山灵扑我万重翠,少室磊磊真与少华参。无奈三面可望不可攀,安得羽翼飞上青云端。
不雅观察视角之极尽精微,感想熏染之非常奇特,造句之自然佳妙,堪称是继李白《庐山谣》《天姥吟》之后的第一人。毋怪清末至民国间的诗坛祭酒陈三立激赏之馀,要特地选录其游山诗为之出单行本。
晚清诗宗宋之风甚盛,但魏源不尚时流,毕生是导源于汉魏而直追李杜。和李白多是写古风相似,他也是五七言古风的造诣最高。近体中七律紧张是写时势和咏史,由于学博,典故信手拈来,颇让人目为“用典过多,艰深晦涩”。实在这也是多数律诗中习见,利害在设喻达意之奥妙自然与堆砌典故之味如嚼蜡,魏源诗正是属于前者。五律中佳制甚多,极具唐人风致。如十九岁前的少作《湘江舟行》四首之一:
亦欲愚溪去,其如山水重。
鸟鱼骄九曲,竹树醉千峰。
人入琅玕国,天围翡翠墉。
估帆贪利涉,不入壑丘胸。
又如《乌龙潭夜坐》之一:
晨兴寻古寺,径转翠成围。
客病花偏好,家贫草更肥。
鹿蹊群壑静,鱼国万泉归。
着我真图画,不嫌无钓矶。
大可置诸唐人集中,颔联尤具天趣。又如《江口晤林少穆制府》二首之一:
万感苍茫日,相逢一语无。
风雷憎蠖屈,岁月笑龙屠。
方术三年艾,河山两戒图。
乘槎天上事,商略到鸥凫。
这是道光二十一年林则徐于遣戍伊犁途中,在镇江与魏源相会,亲手将《四州志》的译稿交给他,两人对榻连宵,不胜感慨。末句原有自注云:“时林公嘱撰《海国图志》。”委婉深情,肝胆相照,记录了两位爱国者忧时图救的心声。
以上只是简论了魏源在诗歌创作方面的突出造诣。对今日的广大读者而言,恐怕除了研究者们之外,多数只知道有魏源其人而少有读过其《海国图志》诸书及所编纂的《皇朝经世文编》;而魏源的诗歌,不仅可以让我们理解他是一位精彩的墨客,也可以让我们认识他之以是成为一位改革思想家及其所处的时期。
(作者系湖南省文史研究馆馆员,本文选自《文史拾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