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益所作边塞诗中,最有名确当属《夜上受降城闻笛》:
回乐烽前沙似雪,受降城下月如霜。
不知何处吹芦管,一夜征人尽望乡。
诗中所云“回乐烽”,在常见的唐诗表明中,都指其为唐代灵州治所回乐县城东面的烽火台;而受降城则被视为灵州的别称——646年,唐太宗李世民亲临灵州接管突厥一部屈膝降服佩服,自此灵州被称作“受降城”,这一称呼乃至一贯沿袭到了宋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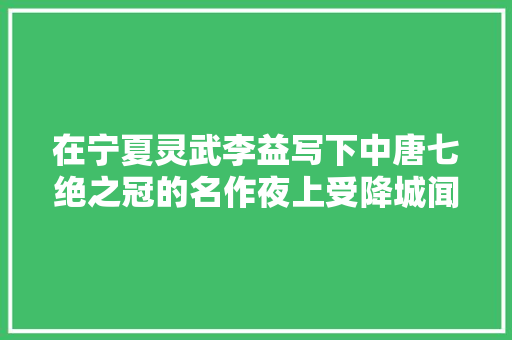
灵州即今日银川下辖的灵武市。在唐代,这里是防御突厥和吐蕃的前哨,具有极主要的计策地位。721年,唐玄宗李隆基在灵州设立朔方节度使,此地遂一跃而成为全国最为壮大之军镇,防区最大时,不仅包括今日宁夏全境,更涵盖内蒙古的河套地区,以及陕西富县、彬县以北广阔区域。
灵武水洞沟遗址,烽火台遗迹
李益大约生于天宝十年,即750年。出生之后大约五六年,安禄山在范阳起兵,“安史之乱”拉开大幕。这场历时七年多的内乱是唐朝由盛而衰的迁移转变点,也是李益人生中最主要的发展期间。经由这场大乱之后,唐朝再也不可能寻回盛唐气候,李益作为中唐墨客的代表,其作品也被认为染上了一层凄凉意味。
在李益之前和之后,到过灵州或以灵州为写作主题的墨客很多,个中就有著名墨客杜甫,他在《送灵州李判官》一诗中写道:
犬戎兴四海,回顾一茫茫。
决斗苦战乾坤赤,氛迷日月黄。
将军专策略,幕府盛材良。
近贺复兴主,神兵动朔方。
安史之乱发生后,唐玄宗李隆基仓惶逃往四川,太子李亨于756年在灵武为诸将所推,登基称帝,是为唐肃宗。李亨登基后,封郭子仪为朔方节度使,次年又封李光弼为河东节度使。这两位猛将日后在平定安史之乱时居功至伟。杜甫作此诗的韶光或在757年,他将李亨视为复兴主,对其寄予厚望,因而诗中充斥一股豪迈之气。
杜甫
杜甫该当没有到过灵州,在他的诗里,灵州并非一个纯挚的地名,它实际上已经成为一种意象,寄托着杜甫对付李亨这位“复兴主”的热切期盼和对国家动荡的深切忧虑。763年春,对唐朝造成极大毁坏的安史之乱终告结束,杜甫在一首名为《惜别行送向卿进奉端午御衣之上都》的诗里又一次写到灵州:“肃宗昔在灵武城,指挥猛将收咸京……”通过对灵武这个地名的强调,杜甫表达出了内心的喜悦。
出生于712年的杜甫是李益的前辈,而多数留下与灵州有关诗篇的墨客,比李益年事要小,当他们书写这座边地重镇时,不仅唐太宗受降的故事已经迢遥得犹如传说,乃至连“复兴主”李亨在灵州“再造大唐”的伟业也已渐被淡忘。唐朝无可挽回地走向衰落,灵州褪去光环,回答到首当其冲的边防要地角色,比如李频的《闻北虏入灵州二首》:
河冰一夜合,
虏骑入灵州。
岁岁征兵去,
难防塞草秋。
见说灵州战,
沙中血未干。
将军日告急,
走马向长安。
以及姚合的《送李琮归灵州觐省》:
饯席离人起,
贪程醉不眠。
风沙移道路,
仆马识山川。
塞树花开小,
关城雪下偏。
胡尘今已尽,
应便匆匆朝天。
还有贾岛堂弟无可的《送灵武李侍御》:
灵州天一涯,
幕客似还家。
地得江南壤,
程分碛里砂。
禁盐调上味,
麦穗结秋花。
前席因筹画,
清吟塞日斜。
这些诗的作者,很可能都没有去过灵州,最少这些诗并非在灵州写就。李益不同,他留下的一些边塞诗名篇,就写于灵州城内。李益初到灵州的韶光,可能是在777年,但无法确证。
780年深秋或者更晚一些,李益在朔方节度使崔宁部下任职,在灵州待了一段韶光,写下了《夜上受降城闻笛》《祝殇辞》《军次阳城烽舍北流泉》《从军北征》《盐州过胡儿饮马泉》《塞下曲三首》等著名诗歌。
在《祝殇辞》这首长诗中,李益把灵州风景的肃杀和自己内心的荒凉写得淋漓尽致:
我行空碛,见沙之磷磷,与草之幂幂,半没胡儿磨剑石。
当时洗剑血成川,至今草与沙皆赤。
我因扣石问以言,水流呜咽幽草根,君宁独不怪阴磷?
……
山石峥嵘的贺兰山
正如阎福玲在《汉唐边塞诗研究》中说的那样:盛唐边塞诗在描写边塞风光时,长于利用具有苦、寒、险冷色调特色的边景描写,来反衬战士唾弃困难、不可降服的英雄气概与豪情,以是盛唐边塞诗是一种主不雅观表现。而中晚唐的边塞诗在写景状物时,不仅写实,而且因边患日重而染上了一层凄凉惨淡乃至萧森胆怯的色彩。
在《祝殇辞》的末了,李益如此写道:
又闻招魂有美酒,为我浇酒祝东流。
殇为魂兮,可以归还故乡些;
疆场地无人兮,尔独不可以久留。
李益龟龄,活到了八十岁,在唐代墨客中属于罕见。他的诗歌在后世备受赞誉,尤其边塞诗,一曲《夜上受降城闻笛》,冠绝中晚唐,被誉为可与盛唐墨客比肩。他该当感激灵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