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句的出身
高咏楚辞酬午日,天涯节序匆匆。榴花不似舞裙红。无人知此意,歌罢满帘风。
万事一身伤老矣,戎葵1凝笔墙东。羽觞深浅去年同,试浇桥下水,今夕到湘中2。
——陈与义·临江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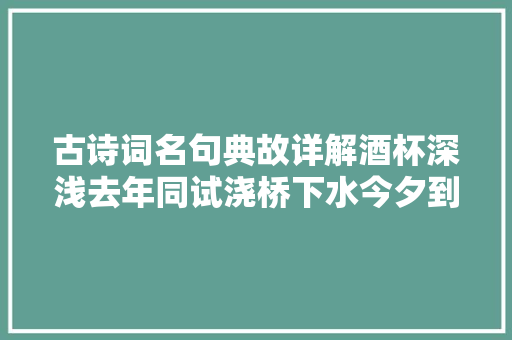
完备读懂名句
1﹒戎葵:即蜀葵,常日在夏日着花。2﹒湘中:指屈原去世处。试浇二句写酹酒江水,凭吊屈原。
年夜声歌咏楚辞,庆祝端午佳节,流徙天涯只觉时节过得匆匆。石榴花比不上舞女的裙裳鲜红。没有人能理解我此刻的心情,歌罢楚辞只觉满帘扑风。
如今,万事虽集于一身,但却老病伤神。墙东的蜀葵仿佛也在嘲笑我的悲惨。杯中之酒看起来与往年相似,我试着将它浇到桥下的江水,希望江水能带着它流到湘江去。
词人背景小知识
陈与义(公元1090—1139年),字去非,号简斋。他早期推崇苏轼、黄庭坚及陈师道的文风及写作办法,后期因经历、体会了“靖康之耻”,转而学习曾经历过“安史之乱”、与他有类似经历的杜甫。总体来说,他的作品题材广泛、感时伤事,是宋代学习杜甫最有造诣的墨客之一。
元代文学家方回曾将陈与义与黄庭坚、陈师道合推为“江西派”的“三宗”。所谓“江西派”是人们称呼以黄庭坚为首的江西文人所组成的一个社团。“江西派”的文人认为作诗为文该当“无一字无来处”,因此提倡所谓“点石成金”法,也便是指借用古人诗文中的词语、典故,加以熏陶点化,化陈为新,让自己的诗起到精妙的修辞浸染,以及“夺胎换骨”。
但实在陈与义并不是江西人,并且他的写作办法与黄庭坚的好用典、矜生硬也有所区隔。他虽喜好苏轼的风格,但却不以追效苏、黄为知足,而因此为应要通过他们,上溯到杜甫。他曾说过:“要必识苏、黄之所不为,然后可以涉老杜之涯涘。”意思便是要看到苏、黄不及杜甫的地方,才能学到杜甫的真谛。他也常常提及作诗的两个要点:一是“忌俗”,一是“不可故意于用事”,此外,他更看重意境,也善于白描的写作办法,因此实在不应该列入“江西诗派”。
名句的故事
这首《临江仙》是陈与义在高宗绍兴五年或六年避居青墩镇僧舍时的某个端午节所作,写作时的年纪约是46、47岁。由于当时金兵攻入汴京,宗室南迁,他在亡命之际又恰逢端午,因此便填了此词凭吊屈原,也借以抒发个人胸臆,以及忧国忧民的情思。
词人在作品中以“羽觞深浅去年同。试浇桥下水,今夕到湘中”来表达一种“马齿徒长”但却“物是人非”的感慨。实在中国自古有以“羽觞深浅”论交情的说法,也便是看杯中酒的多寡来衡量感情的深浅以及对方的“诚意”度,并且还发明了一种测试“羽觞深浅”的办法,以在最恰当的机遇为对方斟酒。
曾有人就中国古代留存下来的“竹林七贤”图,研究出古人在测试“羽觞深浅”时,是在羽觞之中做文章。由于在此幅图中,竹林七贤之一的阮籍,羽觞里装有一只木雕小鸭子,在古时,人们称这种木雕小鸭子为“浮”,宴饮时若想知道对方究竟饮了多少酒,便可直接看羽觞中小鸭子浮沉的程度。小鸭子若沉潜下去,则表示饮酒者相称尽兴,若小鸭子一贯浮在羽觞上,便表示饮酒者只是虚应一应故事。
饮酒能饮至让羽觞都符合“物理学”事理的办法,想必也只有中国古代这些好风雅的绅士们才想得出来了。
经久弥新说名句
陈与义的这阕《临江仙》不仅思念屈原,更在个中融入自己的人生感想熏染,无怪元好问在感同身受之余,也激起他的共鸣,夸奖陈与义的词不仅像诗歌一样“隽永有味”,并也具有“不传之妙”、“愈嚼而味愈出”,确实是读出了个中滋味。
农历五月初五是中国传统的端午节,又称“端阳”、“重五”、“端午节”。实在早在周朝,民间便有“五月五日,蓄兰而沐”的习俗,同时,端午节也是自古相传的“卫生节”,人们在这一天总要打扫庭院,挂艾草、悬菖蒲,洒雄黄水、饮雄黄酒,以袪除不洁之物。不过到了本日,一提起“端午节”,人们首先想到的便是中国伟大的政治家与文学家——屈原。
屈原是一个正派的忠贞爱国之士,生平忧国忧民,但却屡遭奸佞猜忌、陷害,终不见用于君王,甚至末了,他宁肯自沉于江中,也不愿连续在那“众人皆醉我独醒”的人间间苟活。如此破釜沉舟的忠烈情怀,自然引起许多文人的共鸣,因此自古以来歌颂屈原的诗篇可说是数不胜数,例如汤显祖的《午日处州禁竞渡》、钱琦的《台湾竹枝词》、梅尧臣的《五月五日》等,都是个中的名篇。
有趣的是,2004年,韩国政府文化财厅决定将“江陵端午祭”推向天下,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报告2005年度“人类口传和无形文化遗产”。虽说韩国与中国自古渊源颇深,但相信听到这个后,没有多少中国人会乐意将这个原属中国且纪念意义深刻的节日拱手让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