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做的那个扶额礼,觉得虽然有点中二,但被他演绎出来却变得特殊帅,让人移不开眼。
"羽族的皇,拽的二五八万的扶额礼",那时候我在朋友圈这么写道。那段韶光,我被张若昀饰演的这个角色迷得无法自拔。每次剧里涌现这个镜头,我就会不由自主地模拟,乃至在朋友面前炫耀:"你们看,这才是王者的气度!
"我的闺蜜们一开始还笑我花痴,但逐渐地,她们也被张若昀的这个角色圈粉了。
例如有人表示:“起初我以为这动作挺傻的,但当他开始做时,我立马被征服了!
”此外,也有其他网友留言道:“当时他饰演的角色一出场,真是惊为天人,我全体人都瞬间被他迷住了!
”。
这段回顾让我开始反思当下古装偶像剧的一个奇怪征象:为什么编剧们总是要费尽脑汁地设计这些繁芜的见礼手势?难道他们之间也有“查重”的压力,恐怕一个动作重复就会被不雅观众骂“抄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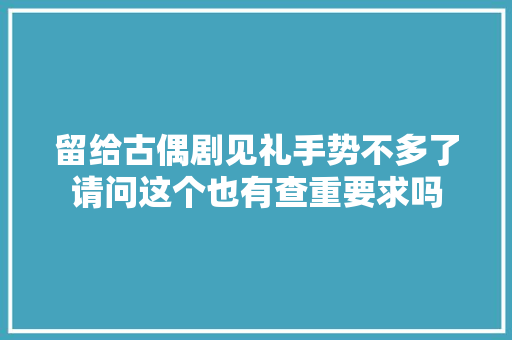
如今的古装剧中,见礼的办法已经不再拘泥于传统的拱手礼,而开始猖獗"创新"。有的开始在武打戏高下功夫,有的则专注于手势的创新,形式愈发的新颖,乃至有些奇葩。
看着这些千奇百怪的见礼办法,不禁让我感叹:照这个趋势下去,留给古装剧的首饰恐怕逐渐沦为稀缺物种。
那条关于张若昀见礼的推送,溘然让我回顾起了以前的光阴。我好奇地在网上搜索起其他古装剧的见礼镜头,结果创造这些镜头让我笑得前仰后合,也让我对这些剧的创作理念有了新的认识。
首先映入眼帘的是《玉骨遥》。肖战在这部剧中饰演的角色,有一幕和其他四个人同时见礼,却用了三种不同的姿势。我不禁感叹,这剧组对礼仪的讲求也太透彻了吧?仿佛恐怕不雅观众说他们敷衍,硬是要把手势研究得明明白白。
"肖战的玉骨遥,哈哈哈,五个人见礼,三种姿势,真的绝了",我在朋友圈里这样写道,"见礼都研究的很透彻了"。真正让我破防的是当我看到《苍兰诀》中大黑龙这个角色的片段时。每次出场,饰演大黑龙的演员都会高喊一声"尊上威武",然后"邦"的一下,猛地伸出拳头,在自己胸口狠狠一锤。
第一次看到这个镜头,我被这突如其来的动作吓了一跳,但紧接着就被逗得眼泪都笑出来了。
我记得当时在弹幕上看到他们评论说:“最牛的还是苍兰诀大黑龙那个锤子,每次出来我都会爆笑,尊上威武!
(邦!
)”紧接着另一条弹幕说:哗啦一下拳头伸出来邦邦锤自己,每次都邦的一下给小兰花吓一抖动,哈哈哈哈哈哈哈。
这个"锤子礼"真的太搞笑了,可是在笑过之后,我溘然担忧起大黑龙哥哥。他每次都捶得那么用力,他的手会不会痛呢?这种看起来很威武,但实际上有点儿自虐的动作,真的得当吗?。
就在我在心疼大黑龙的手时,另一部剧的片段吸引了我的把稳力。那是《从前有座灵剑山》,里面有个角色的见礼办法让我哭笑不得。
他竟然对着对方比了两个爱心!
"这是从前有座灵剑山里的手势,对方为你比了两个爱心,哈哈哈哈哈哈哈哈,"我在社交媒体上写道,"这个也太可笑了吧!
不过这个剧本来便是笑剧,巨搞笑剧情也挺好,便是这手势有点花里胡哨了"。
这条动态引发了很多人的共鸣。有人回答道:“剧好看的话是有加成的,不好看的话便是多此一举!
”确实,在笑剧中,这种略显夸年夜的手势反而为剧情增色不少。
从张若昀那个令民气动的扶额礼,到大黑龙那个令人捧腹的"锤子礼",再到《玉骨遥》中那些令人眼花缭乱的三种礼仪,乃至是《从前有座灵剑山》中那个让人忍俊不禁的双爱心手势,这些设计就像一壁多棱镜,映射出编剧们天马行空的想象力。
但是,这些花里胡哨的动作到底是为了丰富角色个性和剧情效果,还是纯挚为了标新创新、避免被说没创意呢?这场古偶手势的狂欢中,欢快与质疑并存,让我不禁感慨:这些手势竟然承载了如此丰富的喜怒哀乐。
就在我为这些稀奇古怪的手势感到哭笑不得时,一部剧的片段却让我面前一亮。那部剧叫《阿诗勒隼》,主角的见礼姿势虽然大略,却散发着一种难以言喻的帅气。
"怎么能没有我们阿诗勒隼,"我在社交媒体上写道,"虽然姿势大略但真的帅!
"。
让我更为惊异的是,朋友们的回答见告我,这个看似大略的手势竟然源自于某个真实存在的民族传统。一个历史系的朋友评论说,"这个手势在以前的某一民族中确实是存在的,以是它并不会显得突兀!
"。
我被这个创造所震荡,《阿诗勒隼》在这场古偶手势的创新狂欢中,如同一股清流般脱颖而出。这部作品的手势并不是为了求新创新而生搬硬套,而是从历史长河中汲取灵感,这让我想起那些流传千年的礼仪,它们不须要任何刻意的装饰,就足以让人肃然起敬。
反不雅观那些为了分歧凡响而生硬创造的手势,反而显得有些多此一举。
正当我对《阿诗勒隼》中的几个细节特殊讴歌的时候,有个采访的时候让我大吃一惊,对方说古装剧中的一些问候的手势都是演员们自己想出来的。
我原以为这些手势都是编剧或者导演想出来的,没想到演员们也有这么大的创意。我记得一个采访说,很多古装剧的问候手势都是让演员自己创作的。朋友们的反应很有趣。有人佩服演员的创造力,但也有人调侃说:“真的,我都佩服能想出这些手势的人,有些真的看起来便是,纯粹为了形式而仪式,没有美感也没故意义!
觉得在研究十根手指的排列组合了。
这让我想到《长月烬明》中的一些手势,那些动作看起来确实很美,但做起来却随意马虎抽筋。我笑着想象剧中人物见礼后,还在那里惊悸失措地摆正姿势的样子容貌。
在朋友圈写道:"长月烬明里面有几个手势倒是非常好看,便是做了随意马虎抽筋那种!
礼都行完了整顿还没摆好"。
转头不雅观望那些演员们自创的手势,个中不乏富有创意的表现形式,但也有一些是为了新颖却无实际效果而做出的。于是我开始明了,为什么有些剧迷们会以为这些手势显得有些"出戏"。
当一个动作过于繁芜或刻意,它就不再是剧情的点缀,反而成了喧宾夺主的滋扰。
在传统与创新的拉锯战中,《阿诗勒隼》向我们展示了一种启迪:真正的创新,不是完备抛弃传统,而是在传统的根本上授予新的生命力。
就像那个大略却帅气的手势,它既尊重了历史,又完美地融入了当代审美。
大概,未来的古装剧中会有更多的例子涌现,它们不但是为了创新而创新,而是能在传统的肥沃土壤上开出新的花朵。
正当我为这些手势的利弊辩论不休时,《从前有座灵剑山》的一个场景溘然跃入脑海。那是一个让我至今难忘的镜头:一个角色向另一个见礼,竟然是双手比出两个爱心!
"这是从前有座灵剑山里的手势,"我在社交媒体上愉快地写道,"对方为你比了两个爱心,哈哈哈哈哈哈哈哈,这个也太可笑了吧!
"。
第一次看到这个镜头,我笑得前仰后合,以为这个设计非常有创意。但笑过之后,我溘然意识到,这部剧本来便是一部笑剧。在这样的语境下,这个略显花哨的手势反而为剧情增色不少。
我以为这个剧本来便是笑剧,巨搞笑剧情也挺好,便是这手势有点花里胡哨了。这个不雅观点引发了广泛的共鸣。有朋友回答:“如果剧好看,手势自然会增色不少;但如果不好看,那就犹如多此一举。”这让我认识到,评判一个手势的好坏,不能分开剧情背景。
在笑剧中,适当的夸年夜手势有时乃至能为角色增长魅力;但在一部严明的历史剧里,这样的手势可能就显得不伦不类了。
谈起笑剧效果,我又想到了《沉喷鼻香如屑》里的一个有趣手势。"沉喷鼻香如屑笑去世我了。"我在群聊中说道,并讯问这个手势的含义,"莫挨老子???达咩?"朋友们的回答也十分有趣。
有人表示:"双手胸前交叉可能是表示祝福,但如果不比兰花指就会变成你xx了"。
这个模糊的寓意在剧中引发了很多笑料,但笑过之后,我开始思考:这种为了博君一笑而设计的手势,是否会影响不雅观众对剧情的投入?就像我一个资深剧迷的朋友常说的:有时候,这些标新创新的自创手势,真的会让人出戏。
她一贯坚信在大多数情形下,只须要大略的拱手礼就足够了。她在一次谈论中说,“我个人以为拱手礼就够了,大家都懂。有时候标新创新自创手势真的出戏!
”我不得不承认,她的不雅观点很有道理。
拱手礼简洁大方,超过时空,不须要过多阐明。
我不能完备否定创新手势的代价。例如,在《从前有座灵剑山》和《沉喷鼻香如屑》这两部剧中,虽然有些手势看起来有点出格,但在笑剧的语境下,这些手势却为剧情增长了许多欢快色彩。
因此,我认识到,手势设计并不仅仅是好坏的问题,更主要的是它如何与剧情和角色相互呼应。
就在我被这些思绪缠绕时,一个大胆的想法溘然闪烁在我的脑海中:如果古偶剧真的用尽了手势创意,为什么不向其他领域借鉴呢?"往后假如不足了建议去借鉴隔壁rapper的手势,"我在朋友圈调侃道,"他们还剩很多。
但是嘘小声一点,我怕被diss"。
一想到这个,我就忍不住笑了,把《长月烬明》里做起来随意马虎抽筋、却又很优雅的手势,换成某个说唱歌手标志性的动作,画面想想就很有趣。
"《长月烬明》里有些手势真的很好看,"我曾经写道,"便是做了随意马虎抽筋那种!
礼都行完了整顿还没摆好"。
我想起了之前看过的《与凤行》,赵丽颖饰演的角色在灵族,他们的见礼办法是比一个爱心。
"我之前看过赵丽颖的那个剧与凤行,"我在群聊里说,"灵族的见礼办法是比一个爱心。"
乍一看,这个设计彷佛有些俗气。但仔细想想,在一个讲述爱情的剧中,这个手势倒也不算突兀。
当所有人都在绞尽脑汁地设计新手势时,我不禁产生疑虑,这是不是陷入了形式主义的陷阱?就像我朋友常说的,"觉得在研究十根手指的排列组合了。"我们是不是过于追求形式而忽略了内容?
还有鞠婧祎在那部剧的角色,让我想起了童年的游戏,便是她见礼的样子。"鞠婧祎这个飞飞的见礼挺有羽族的特色",我在评论里这样写,"我们童年便是用这个模拟老鹰投影在墙壁上的。
"这个设计虽然大略,但奥妙地呼应了角色特点不过,有个调皮的朋友说:"不把稳看会以为是比中指"这让我意识到,纵然是大略的手势,也须要谨慎设计,以免产生误解。
回忆起所有这些手势,从繁芜到大略,从优雅到搞笑,我不禁感叹:在这场创新的狂欢中,我们彷佛已经到了一个临界点。如果再这么下去,真的要去借鉴rapper的手势了吗?但转念一想,大概这并不是坏事。
毕竟,艺术从来便是相互借鉴、领悟的产物主要的是,无论借鉴自何处,都要做事于剧情,做事于角色。
经由一番思考后,我再次回到最初的问题:古偶剧中留给见礼的手势还有多少?从张若昀在《九州天空城》中的扶额礼,到大黑龙的“锤子礼”,再到《阿诗勒隼》中的帅气礼仪,以及《玉骨遥》中令人眼花缭乱的三种礼仪,乃至那些让人捧腹大笑的爱心手势,彷佛都在见告我们一个事实:这个舞台上,创新的空间已经所剩无几。
现在,我开始理解编剧和演员们为什么会如此绞尽脑汁。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期,纵然是一个小小的见礼动作,都仿佛要经受"查重"的磨练。
大家都在担心,如果不推陈出新,就会被不雅观众责怪为"套路"或"抄袭"然而,在这种压力下出身的创新,究竟是真的为剧情增色,还是仅仅是为了创新而创新?
我终极认同了剧迷朋友的不雅观点:大多数情形下,一个大略的拱手礼就足够了。它不须要花哨的装饰或繁芜的动作,但却能传达出一种超过时空的礼遇和尊重。
正如一位网友所说:“剧好的话拱手礼就有加成,不好看的话就成了多此一举!
”。
或许,古偶剧中剩下的见礼手势确实不多了,但这未必是坏事。相反,它可能在提醒我们:在创新的道路上,有时候,最大略的办法反而最打动人。
就像《阿诗勒隼》中的那个源自传统的手势,它并非为了标新创新,而是在传统的根本上注入了新的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