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我轻轻的来;
我轻轻的招手,
作别西天的云彩”
以上节选自入选教材多年的《再别康桥》,大家该当都很熟习。它是徐志摩的代表作,由于这首诗让康桥变得很有名气,去英国旅行时,很多朋友都把它当成打卡地。这首诗写于1928年11月,当时徐志摩在归国途中,想起了康桥,有感而发写了这首诗,而“康桥情节”也伴随了徐志摩的生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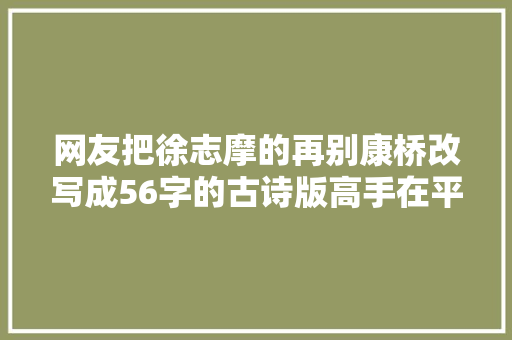
毫无疑问,这首诗曾是月牙派、乃至是新诗最经典的作品。但近些年来,也有不少网友表示,每天听别人说“轻轻的我走了”,也没以为哪里好啊,这首诗是不是被高估了?乃至有网友表示:这种诗我也会写,于是网上涌现了各种不同的版本:
悄悄的我醒了
正如我悄悄的睡;
我悄悄的抬手,
拭去眼角的泪水。
对付这一类的仿作,且不说意境不如徐志摩原诗幽美,而且人家玩剩下的写诗办法,你直接套用,写得再好也注定成不了经典。在浩瀚仿作里要说最牛的,笔者认为还是一位不有名网友写的古诗版。这位网友把《再别康桥》改写成56字古体诗,写得很有水平,让我们来读一读:
康桥落日淡余晖,金柳依依拂翠微。
青荇悠摇波不定,长篙漫搠梦同飞。
放歌何以笙箫默,高咏那堪衣袖挥。
明月自随楼影去,微风长送白云归。
大家看这首诗,虽然平仄格律上不算很完美,算不得十分工致的律诗,但整体上是按照古诗的写法写就的。它用56个字,就把徐志摩原诗里要表达的意象基本上包括进来的。原诗里涌现了云彩、金柳、风、流水、长篙、夕阳等意象,这首改写诗里基本上一个不落,但字数用得就少多了,这也是当代诗和古体诗的不同。
前两句,一开篇便是一幅大的水墨画。落日、桥、柳先构图,这是桥上的美景。三、四两句,写的是桥下的船和微波,这是桥下的美景。四、五两句,则是写景和抒怀的领悟,这一点和徐志摩原诗的立意是差不多的。
末了两句是笔者最喜好的部分。徐志摩原诗的落笔是“不带走一片云彩”,但古诗不会这么直接,微风送走白云,明月随楼影而去,更加婉约。至此全诗戛然而出,诗里面有韶光的变换,也有空间的转换,整体上读来是一气呵成的。
当然这首诗也存在一定的瑕疵,除了格律对仗之外,有些字眼用得还是浅白了一些,比如“衣袖挥”这一句。但作为一个当代人,能写到这个程度已经相称不随意马虎了,只能说高手在民间。
通过这首诗,我们也能看出古体诗在写作办法,意境的渲染上与当代诗是完备不同的。古体诗强调的是对偶,以是写出来的东西一定是有一个框架的。这种框架对普通人来说,可能是一种笔墨上的束缚;但对付高手来说,它是一种更高的艺术追求,网友这首诗基本上做到了。而当代诗,看起来很随意马虎,但要写出水平,就要在形散中做到神不散,这不是随便凑几句话能达到的,徐志摩这首诗做到了。
像这种模拟版,网上还有不少,彷佛网友们很喜好用古体诗的办法来改写这首经典诗作。从某个角度来说,作为徐志摩的代表作,这首《再别康桥》之以是还是会有人认为写得不足好,便是由于他们从心底就不太接管当代诗,无法认可这种诗的形式。
“当代诗根本不能叫诗”、“再好的当代诗,都不过是把散文多分几行而已”,这类不雅观点根深蒂固,就连韩寒当年就曾说过类似的话。对付这种不雅观点,笔者是不敢苟同的。
是的,当代诗整体来说当然无法和古体诗相提并论,但这并不能否定它存在的代价。以网友的这首古体诗为例,“高咏那堪衣袖挥”确实不如“我挥一挥衣袖”,它们是两种不同的表达办法,写出来的诗性是不一样的。
诗歌是须要传承的,口语文涌现后,与之相对应的当代诗自然出身,至于它将来能发展到哪一步,我们谁都无法预见。但正如王国维所说“一代人有一代人之文学”,古体诗我们显然已经回不去了,诗歌不能就此断了,以是不管喜好或者不喜好,它一定会往前走。大家读完这首网友写的古体诗版,以为水平如何呢?欢迎谈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