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从近年网络诗词大赛征稿启迪提及,有禁用平水韵的,有许可用平水韵的,有仅限《词林正韵》的,还有不少点名说“用新韵者请注明”、“新旧韵不可混用″如斯。不才虽自幼好诗,但不善研究诗论,总以为让作品说话就行了。家父乃民间说唱艺人,常常在家演习训练,家人便耳濡目染,不才写浸染韵,只受家父些许点拨,绝算不上系统。乍闻新韵旧韵平水韵,还不让混用,还需注明,这军将大了,赶紧学理论。这一学才知道,原来,古代这诗理论还真得理论理论。
诗韵之于当今,再大略不过的事了,想想蛟龙探海,嫦娥登月,太空建站,这诗韵之事,不乃后宫小菜一碟吗?韵押音,不押意。而今字典拼音,天下一统,农人工有的大字不识几个,上北京,下江南,普通话互换,那真是钢钢的。押韵那点事,街头巷尾讨饭喊好要喜糖的都懂,人家编的一套一套的,朗朗上口,比某些获奖新诗都好,不信?往后带你来听。现在说韵,不便是汉语拼音的一个韵母吗?比如说“天仙韵″(江湖艺人所称),也便是第二句尾字,是用了拼音韵母an与其他声母拼出字来用便是了,如:天、仙、年、间、寒、连等。“红军不怕远征难″这篇便是an韵。令不才不解的是:古韵书和巜诗韵新编》基本都是十三元、十四寒、十五删。把这些"an″韵字分为三家或多家何来?哪地方言能比普通话更有威信?更有美感?大路不走,拐弯抹角为哪般?本是一个"an″韵下来,却硬生生分成三家近韵,还谓近韵可通押,谁能说出以是然来,不才急迫想听,以便解惑提高。还有一东、二冬,一会还有八冬!
都是由“ong″韵母拼出,又非多音字,连平仄都一样,何来一二?"二″在哪儿?总得说出个来由吧。还有网上查到的巜词林正韵》,也让我开了眼,请看:一东枫疯丰风……。二冬峰丰蜂封……。明明一个ong拼出东冬,双胞似的同韵,天下少找,硬分成两路近韵,孰远孰近不是一拼便知吗?而eng拼出的枫与ong拼成的东却混成了一家,即是一家人说了两家话,而两家人说了一家话,这不是要把诗友们弄疯了吗?恕不才愚见:东与冬才是正宗ong韵的一母同胞,为何要分出两个首领、各领一起人马呢?而Ing、eng拼出的字与ong拼出的字,才是近韵可通押。
“韵″者,音匀也。韵既然押音,就依汉语拼音。拼音何来新旧?汉语拼音没在全国一统天下之前,哀求这韵那韵都可以,之后,所有方言在文化领域都应归顺于普通话!
所有韵音在文化领域都应归顺汉语拼音!
评委是专家,作品到了手里,押的是何韵,质量有几成,那还不一目了然?还用作者注明押的何韵,岂不多此一举、多此一举?如"留取赤心照汗青″,还要作者注明押ing韵或某韵吗?
事实上,关于诗韵之哀求,正如清者自清,浊者自浊一样,韵者自韵,不韵者自不韵,无论你征诗方如何哀求,那种“墨客”压根就不理韵为何物。曾经的“百诗百联大赛”,就将不韵之新"诗″拒之门外,其获奖作品也很具质量,不输唐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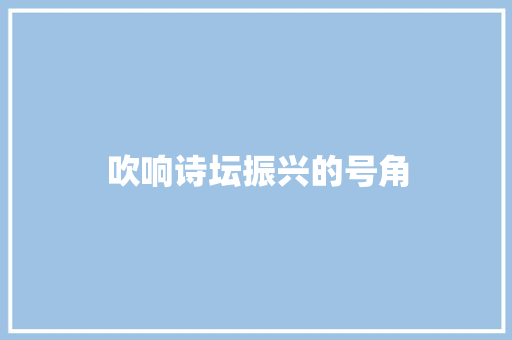
再说平仄。所谓平仄,不才理解为汉语拼音之四个音调,仄声或去声为腔调之第四声。只管字典上云:仄二三四声之总称,但我还是以为去、仄二字本身皆四声。就实用而言,同一韵母拼出的字,只有四声与前三声相去甚远,读起来略感别扭。同一篇中,最好多用一声,如不足用,二三声也可以上,只管即便别与或少与四声混用。不过,名人大家也偶有用之,效果还不算差。如毛诗“重上井岗山”:久有凌云志,重上井岗山。……过了黄洋界,险处不须看。“山”为平声,“看”为仄声,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又如不才为“祁连玉杯”试作了一首咏玉七律:中原寻宝何处去,祁连山藏祁连玉。珍稀琳琅堪为绝,岁月雕琢鬼神锯。肃南大地锦绣添,裕固儿女金银聚。直教游人看花眼,赤橙黄紫青蓝绿。由于第二句尾用玉(仄声)以是都用了仄声韵字,这样读来舒畅点,不绕口,力度均匀。这里只论平仄,不论质量。若有前三声混入,即便按拼音押韵了,读来会有深一脚浅一脚的觉得。平仄之分,实用之中,仅此而已。
诸位诗兄弟、诗姐妹们:咱不用去背那“平仄平仄平平仄,仄平仄平仄仄平”,啥意思?圈套!
偶句尾字押韵就够了,诗作也不能太过用去世公式去套,咱钻那迷宫干吗?李杜毛诗要钻了套子,能写成那样?蒙谁?诗的意境和措辞艺术性也尤为主要。按拼音押韵写作,奥妙理解与利用,不必太过去世板,泱泱洒洒为诗,说不定能出千里马。如果诗兄弟诗姐妹们还没听懂我的话,非要我把那同韵字挑出来,按平仄分成一堆一堆的,不才愿效犬马之劳。有些人带着眼镜查字典,生平未著一名篇,耻辱也!
小儿科把戏,谁奇异?只管即便不想祸害你们,按拼音写吧,简约不大略。
时期在发展,诗坛要革命。诗韵要随着普通话的遍及而规范。任何方言在普通话面前都苍白无力,拼音韵母才是全国最统一、最威信、最规范的韵书!
作者:姜爱民
((请看第四篇:诗坛振兴路在何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