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传播、弘扬济南特立于世的泉水文化,《风喷鼻香历下》连续推出《济南名泉考》系列作品,先容、挖掘济南名泉罕为人知的历史故事,内容包括:济南名泉的考证与索隐、绅士与名泉的风雅往事、名泉史话等等。欢迎关注。
中秋节前夕,接到好友、泰安文化学者周郢师长西席自诸城县博物馆发来的一幅石刻照——“允素草书”石刻的照片。想不到,竟然由此弄清楚了趵突泉上一处“仙迹”——《来鹤亭诗》的来龙去脉及其原形。
旧时趵突泉上吕祖阁
趵突泉上有吕祖阁,泉上有不少关于吕祖“仙迹”的传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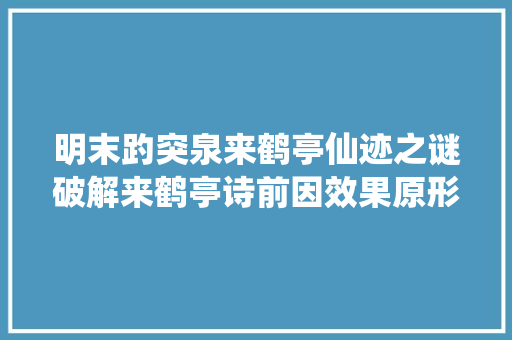
据清任远大《趵突泉志》之《传闻志》:
“来日诰日启丁卯,来鹤亭壁上,一夕忽题云:
大仙何处黄鹤舞,来鹤桥通白雪楼。
胜地自逢人作主,好风飘桂我惊秋。
千家松菊山山月,十里芰荷叶叶舟。
书罢新墨客不见,涌轮亭上望悠悠。
群以为‘仙笔’。一时属和者甚众。长吏多罗拜其下云。”
任远大在《传闻志》中称:“传闻,以其事不见之文籍,相传于父老之口也”,因而他“取父老之相传,为游人之解颐。”
书影:任远大《趵突泉志》《传闻志》
实在不然。笔者创造,《趵突泉志》上的记载,非止“相传于父老之口”,实源于明崇祯《历城县志》卷十六《杂志·传疑》“来鹤亭诗”:
“来鹤桥北有来鹤亭,天启丁卯,有人以瓜壳濡墨题壁上云:
大仙何处黄鹤舞,来鹤桥通白雪楼。
胜地自逢人作主,好风飘桂我惊秋。
千家松菊山山月,十里芰荷叶叶舟。
书罢新墨客不见,涌轮亭上望悠悠。
时亭壁新成,羽士恐得罪,乃诧以为‘仙笔’,四方临者携手挥汗,长吏多罗拜其下。已而察之酤廛野刹多此字迹,乃青州狂生戏墨云。”
书影:明崇祯《历城县志》:“来鹤亭诗”
原形大白,此诗为“青州狂生戏墨”。不过,作者即“青州狂生”究竟为何人?依然是一头雾水。
而周郢师长西席所供应“允素草书”石刻,却办理了这一悬疑。石刻正面正是崇祯《历城县志》所谓“来鹤亭诗”也,不过,个中个别字句却有不同,且石刻并有署名与跋。详下。
其一:诗作:(《百度》收有“允素草书”条,而未收诗作,大约不易辨认之故),经笔者与书法里手一番辨认,诗如下:
大仙何处黄鹤舞,来鹤桥通白雪楼。
胜地自逢人作主,好风飘桂我惊秋。
千岩松菊山山月,十里芰荷叶叶舟。
旧蹟几行云海渺,涌轮亭上望悠悠。
其二:署名:允素。
其三:跋:五山张师长西席趵突泉上诗,伊时名流拜为“仙笔”,明崇祯间手书于放鹤园。清康熙年用勒之石。
石刻背面则为卧象山龙湫重新光明藏碑记。张侗撰文,楷书体。与此诗关系不大。
书影:允素草书
石刻中涌现的“允素”“放鹤园”等,参照《诸城县志》,详情如下:
放鹤园在诸城西潍水之滨放鹤村落(今为普庆社区普庆村落),为明代正德年间张氏开山祖师张泰所建。据清乾隆《诸城县志》,张泰脾气豪迈,喜好野猎,在潍河捕获一只鹤,翅膀吊颈挂一个银牌,上面写到:“(元)至正二年再放”。张泰很是伤感,于是,为鹤改换一牌,上写:“明正德十二年三放”,将鹤放生,并且,焚毁猎具,同时建起放鹤亭(园),让子弟读书习礼,风雨不辍。(“张泰,性豪迈,好剑术。尝从诸少年结网潍滨获一鹤,翅间悬银牌镌曰:‘元至正二年再放’。泰为易一牌云:‘明正德十二年三放’。遂焚网解剑,举酒谢少年曰:“鹤今可谓冥冥矣,愿与诸君无复陷入网罗也。”乃立石为碣、筑亭,颜放鹤。日与子弟诵读,风雨不辍者六十年。无病而终。” 见清乾隆《诸城县志》卷四十二《列传十四·隐逸》)
书影:清乾隆《诸城县志》卷四十二“张泰传”
此后,此地遂为放鹤村落,而张氏虽非进士之家,亦本钱地名门王谢。称放鹤张,别号普庆张。
再后,至明末清初,“放鹤张”氏又一次声名大震。原来是,张泰后人有张衍、张侗、张佳、张傃,不事清室,以山水友朋为乐,居于放鹤园中,饮酒赋诗。称“张氏四逸”,名声颇大。(清乾隆《诸城县志》卷三十六《列传八·文苑》)
书影:清乾隆《诸城县志》卷三十六“张衍传”
“允素草书”石刻,可与明崇祯《历城县志》、清《趵突泉志》互为订正,且有《历城县志》未录之详情在焉。
一是,石刻供应了《来鹤亭诗》的又一版本,且有不同之处,如“千家”为“千层”,“书罢新墨客不见”为“旧蹟几行云海渺”等,此足以互为参照。
二是,作者为张允素,号五山,为诸城“放鹤张”氏之后人。此石刻成于清初康熙年间。
至此,“仙迹”《来鹤亭诗》的来龙去脉业已基本清楚。明崇祯《历城县志》所谓“青州狂生”者,为诸城“放鹤张”氏之后人张允素张五山师长西席。
细审之,明崇祯《历城县志》仍与“允素草书”石刻有不同乃至抵牾之处。
紧张是,《来鹤亭诗》书写地点,《历城县志》认定在趵突泉上来鹤亭壁,而石刻则称张允泰“手书于放鹤园”,这种抵牾征象,该如何理解呢?对此,笔者再加详考之。
首先,张允素书诗于趵突泉来鹤亭壁是一个铁定的事实。此当以《历城县志》记载为是。
情由:当时书写过后,闻是“仙迹”,文士称道,四面八方前来临摹者成群结队,挥汗如雨,浩瀚官员前来,罗拜其下,编纂者郑重其事编入《历城县志》,韶光(天启丁卯)、地点一应俱全,此乃当时轰轰烈烈、尽人皆知的大事,必不能为虚构也。
而且,由字迹看,不惟率意、随性,且笔划干挺如弯枝,亦不似正常羊毫所写,而颇似“以瓜壳濡墨”所致。
趵突泉旧照
其次,石刻称张允泰“明崇祯间手书于放鹤园”,有没有这样一种可能,即张允素自济南趵突泉返回老家后,又用“瓜壳濡墨”重新写了一遍呢?“复制”甚难,况且,此时在省城已是议论纷繁,照一样平常情形理解,这种可能性彷佛不大。
然而,我们却不能完备打消它的存在。这是由于:
其一,《来鹤亭诗》有两个不同版本,且差异较大,笔者以为,个中,初版本为张允素书于来鹤亭壁之诗,亦即现存于崇祯《历城县志》之诗,惜乎原稿无存。而今所见诸城县博物馆所存“允素草书”石刻,即为张允泰“明崇祯间手书于放鹤园”之诗。
其二,况且,“允素草书”石刻,有“允素”署名,经书家辨认,其字迹与诗作相同等,当出自一人之手。
在学术研究中,否定或抹杀任何一种可能性,都是武断的、不科学的。
由“允素草书”石刻笔墨可知,立石在清康熙年(“清康熙年用勒之石”),为“张氏四逸”所为,这间隔张允素手书至少三十年之后的事情了(张允素手书为来日诰日启七年即1627年,康熙元年1662年)。“四逸”年事附近,均生于明末(多为崇祯年),而张允素此时已然成年,他们大约隔了一代人。
感谢文史学者周郢师长西席寄来石刻图片资料,感谢祖籍济南的书法家王绍垿师长西席帮助辨认草书笔墨。